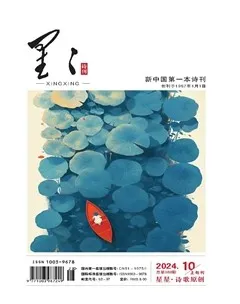现代诗和城市
现代诗或者说新诗与旧体诗区分开来,首先是挣脱了格律的镣铐,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形式,同时现代诗的语言活动范围,也理所当然不再局限于山水和乡村,语言的视野里理应更多出现城市的身影。当代诗人似乎依然存续着一种强烈的乡土眷恋,总是有意无意把目光投向乡村或故土——这当然和大部分诗人的农村出身和童年记忆有关,乡愁、亲情、童年记忆,它们在时间里沉淀更久也当然更容易得到美学的认领。而乡土恰恰是中国古诗传统反复书写的,有着深厚的美学积淀,现代诗人痴情于此,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传统美学的泥淖。许多诗人对乡村的田园牧歌式书写,大多来自一种公共美学经验,他们书写的乡村,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修辞化的乡村,真正的乡村已经不是那个审美经验里的乡村了。而城市的日常对于现代诗人,却是一个全新的语言活动场所。由于它的陌生、庞杂、纷繁和丰富,它当然挑战诗人的个人才能。
面对城市,当代诗人不应在语言上绕道而行。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进程,除了工业化以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使更多的人口——远不限从乡村通过求学进入城市的“侨居者”,——涌入城市,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商人,他们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经营者,而通过大学之门进入城市的农村孩子,大多成为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这种快速生成的社会样态可能以林立高楼和宽敞大街、CBD和别墅区作为显著标志,但是城市在现代诗歌中作为崭新的语言形象,却远未显示它的新颖性和陌生性。中国许多现代诗人师承于象征主义,但是其笔下却没有出现b6aa303b68336241cbf8c9bdf208c5cbc0bb40567f001510541ca3e0566ca434《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那样显示对一座城市的深刻理解和真切感应的作品。不是说现代诗没有书写城市的作品,而是说现代诗的呼吸里很少出现城市的脉搏跃动的诗歌,更多是一种对象化的书写,缺乏一种深深的本体沉浸。
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作为当下的存在,理应是现代诗关注的焦点。而城市作为人文荟萃之地,它可能比乡村更容易建立过去和未来汇聚的视点。一座古城比历史教科书更容易让你建立感性的历史意识,而未来的可能性之发生地,当然也是城市。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大量人群,无不面临一种悬空的处境:故乡回不去,回去不是故乡;而在城市始终是一个异乡人。移居城市的乔木和灌木比人更快地扎根,它们很快恢复了剪枝后的树冠和从前的葱郁。而人类的精神根须的生长和新芽的冒出,才意味着现代性的真正生成。现代诗可能比其他任何艺术样式,理应表现出对城市的敏感,更具有催生人和城市和谐共生的力量。
现代城市的高速运转需要在一首诗中偶尔停顿。喧闹的集市需要一首诗去过滤它的噪声。每个人都需要一首诗去建立至少一面映照存在的镜子,使得现代人不再是城市里的一个“幽灵”(庞德《在地铁站》),而是让城市变成一个自由和自在的场所,犹如一对老友重逢,在某个临窗的地方坐下喝咖啡,那样,他们就从大街的喧嚣中完全脱身出来,而进入回忆和情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