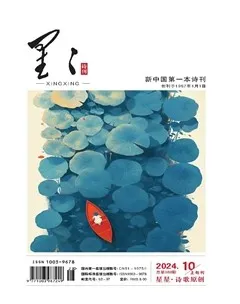那些被照亮的刹那
今年春天多雨,我时常会在某一个瞬间听见一种鸟叫声,苍凉的一声两声,若有似无,从小镇的某处遥遥而来,它的咕咕声,穿过绵绵细雨。我能听见它却看不见它。那声音总是忽然出现又快速消失,如同幻觉。直到有一天,它飞到窗前,当我凝视它时,发现它也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一个遗世独立的小小的黑点,尖锐,忧伤。带着淅沥雨声进入到我的诗里来。我想我感知到了那种随万物生长的疼痛和力量。
三月初,北方朋友说那里正在下雪,视频中,一场春雪,纷纷扬扬,覆盖着平原、城市。藏着一条通向春天的路。而我所在的南方,油菜花已席卷河流两岸。蓬勃着跳跃着的时间,生息循环。我相信那之中必有令一首诗热泪盈眶的部分。五一节假日,途经浙江兰溪,路遇麦地。一大片亚麻黄茫茫奔涌在大地上。我触摸到麦子成熟的重和麦芒之刺。这期间,我还去过阿炳故居,听见灰白院墙下,一株芭蕉,把二胡声引到了命运曲折处。而在溆浦,夜逢屈原,唯有他才能抱得动那块传世之石。潕水之畔,一座芙蓉楼,王昌龄在此设下人世所有离别的小径。在惠安,净峰寺,弘一法师将“以戒为师”留给了后来人。很长一段时间,我辗转在不同的地方。领取各种际遇带来真切的生命体验。并从山水,树木,野鸭,湖等自然事物中去发现和感受。一边游历一边记录。我愿意把自己推至空无一人的从容和安宁中去。置身在旷野、旅途,年轻时我时常会有孤独感,现在,我喜欢这种状态。沉默一会,像晚风推动落日。它时常提示我删掉诗句里的喋喋不休。
“一匹马站在春天”。我写这句诗,是因为看到一幅画:《春日黄昏》。画中的春天原野里,一匹马站在河岸边,把头伸向芦苇丛里几个红色的野果。那马嗅向红果的神情和动作,柔情极了,却又是那种处变不惊的淡泊。好似不舍,无限留恋,痴迷。看到它的瞬间,人世变得明亮深情。这里有时光的速度,事物本身散发出的生命力,弥漫着孤绝感。画面的灰白类似枯草的色泽,质地很厚,它令整个画面中的原野、河流、马、野果透出冲破边界的自由快意。在有限的画布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生命气息。随时可以带着春天飞翔。“画面上的东西越多,留下的东西越少”。这句话用在写诗或活着的方式上,也是有效的。
昨天,朋友谈自己的遭遇,“人生就是这样,仅用了八年的时间,我们就耗尽了一生的缘分,真的很残酷啊。”是的,常常都是如此,走着走着,你身边的人就散了,那些纠缠你的物事也会不辞而别。我们常抱怨世事无常,饱经沧桑。不尽人意。缺失敬畏。那是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发生了什么,天空都是满盈的。
不要将词语或发现一直停留在个体的苦难和艰难中。诗的探索之路很短,生命本质的局促和困境,譬如朝露。应尽可能去传递美、善。诗的探索之路也很长,每一行都企图建造新的世界,以此获得温情与勇气。我在不停地怀疑否定中反思,诗的“新”,应该是如何在普遍、普通的生活泥沙、生命经验里捕捉到让自己也吃惊的意外。所以,我又乐此不疲地眷恋着变化多端的人间。耐心沉潜于此,打造、磨砺它。邀请一道光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