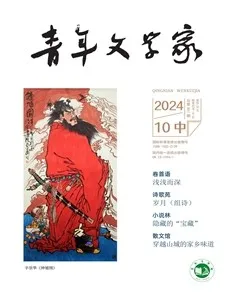自由与天道


《庄子》一书常借助各种动物来进行说理,马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象征。历代注家对于马的研究多集中在《逍遥游》开篇中的“野马”:卢国龙在《“野马”之喻与庄子的哲学悖论》中认为“野马”所喻的是一个蕴含着原始和谐的理念世界;鲁立智在《〈逍遥游〉中“野马”“尘埃”考辨》中从佛经翻译的角度出发认为“野马”即是海市蜃楼,但这种解释放在庄子哲学中略显单薄;马启俊在《〈庄子·逍遥游〉“野马”注释商兑》中也认为根据佛典来解释《庄子》有待商榷;张家成在《试析〈庄子〉中的“马”的意象》中则提出一个新观点,认为“野马”就是马,纵观全文,尽管这种说法富有浪漫,但在情理和哲学逻辑上有些不通。在《庄子》一书中,“马”这个意象出现多次,有些仅仅作为马这种动物本身出现,而有些背后则有着丰富而深刻的隐义。通过发掘“马”这一意象的内涵,结合象数思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庄子哲学的核心,体悟庄子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一、“国马”和“天下马”的区别
在《马蹄》篇中,庄子对作为动物本身的马进行了论述,在一开篇就写到了它们的习性即蹄践风霜,毛御风寒,食草饮水,喜怒自如,庄子将这些特征概括为马的“真性”。《徐无鬼》篇讲述了魏之隐士徐无鬼相马的标准:“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马也。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恤若失,若丧其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由此可以将作为动物的马分为“国马”和“天下马”两类。
“国马”是世俗意义上的好马,体质健壮,合乎规矩,听从驾驭。但与此相对,“国马”也受到了规训,性情被人为改变了,并非马原本处于自然环境中的样子。徐无鬼相马认为“国马”不若“天下马”,“天下马”的关键在于“超轶绝尘,不知其所”,它有与生俱来的禀赋,完全按照自由精神所跑动,不被外物所累,是真正地处在自然环境中的马,无论做出什么举动都是符合动物习性的,这也就对应了《马蹄》篇的“马之真性”,成疏谓之“逸豫适性”。
“国马”和“天下马”的区别在于是否受到人为的改变,其中有两种人即“伯乐”和“爱马者”,他们对马的态度也是马被驯服的两个阶段。自称善于驯马的伯乐用一系列暴力手段削减马身体上的自如,这时原本与天地自然相适的马在受到人为的禁锢和破坏后死亡过半,伯乐还要让马合乎规矩,泯灭“马知”,这时的马已经丧失了许多原本所拥有的自然性情。当马被彻底驯服后就来到了“爱马者”对待马的阶段。同伯乐采取暴力手段进行规训不同,《人间世》对于“爱马者”的描述是这样的:“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以俗世的眼光来看,“爱马者”对马的爱到了极致,从其用珍贵的器具来盛放马粪就可见一斑。但值得玩味的是这样珍惜马的人却将马养死了,这固然有时机不对,触犯其性的缘故,但也和“天下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叔岷在《庄子校诠》中将“马”注释为“案马,易驯者也”。“天下马”长于天地之间,精神丰沛、乘物游心,受尽风霜却体魄强健;受到精心照顾后的马丧失了本身的天性,已被驯化,人为干预导致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使它惊惧乃至死亡。马的“真性”让它不需“义台路寝”,但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对马进行了改变,无论是以暴力手段还是精心喂养,所给予的都是马本身所不需要的东西,都破坏了马的自身平衡,在剥削掉马的“真性”后致使马死亡。
二、“马”是自由精神的象征
《大宗师》篇中,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为好友,子舆有病,子祀前往探之。当子祀询问子舆是否厌恶自己的病态时,子舆的回答中有一句是:“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子舆在形体上虽然受到束缚,但在精神上却有着绝对的自由。以马来比,正是因其本身性情特征是对人驰骋天地间的自由精神的模仿和把握。
自由是庄子的重要思想之一,获得自由的方法即是“心斋”“坐忘”,虚而待物,表现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这样的身体状态在《齐物论》中被称为“丧其耦”。庄子认为“天下马”的一个特征即是“若丧其一”,陆德明对此解释为“言丧其耦也”(王叔岷《庄子校诠》),司马彪解释为“耦,身也,身与神为耦”(王叔岷《庄子校诠》),两者都是精神超越了物质存在达到了独立自由的高妙境界。“丧其耦”是“吾丧我”在形体上的表述,在这种状态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马所喜爱的是原野,高台大殿并不会吸引到马。庄子反复强调“马知已此矣”,正是说明马停留在其“真性”不为万物所动的情态。南郭子綦在隐机而坐,仰天而嘘后达到了和“天下马”一样的境界,“天下马”已然忘己身,这是其与生俱来的天赋。“吾丧我”这种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庄子称之为“游”,“游”是“无为”,是“不知所求”“不知所往”。“马”这个意象本身的特征即是迅捷,良马日驰千里。这种奔驰是在旷野上的,是无目的无拘束的,这同人的精神运动的“游”何其相似。
《应帝王》篇提到“泰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成疏对此解释为:“忘物我,遗是非,或牛或马,随人呼召。”(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马氏引李威曰:“呼我为马,应之曰马;呼我为牛,应之曰牛,此非玩世不恭也,心无我相,已解脱形骸之外也。”(王叔岷《庄子校诠》)陈鼓应先生在《庄子今注今译》中解释为:“任人把自己称为马,任人把自己称为牛。”这里的牛和马并没有贬低的色彩,而是一种接近于自然的神性。“一以己为马”的前提条件是泰式已经达到了卧时安闲舒缓,醒时逍遥自得的精神自由状态,这不就是“离形去知”吗?这种似马的状态正是人达到精神上的真正自由的表现。
三、“马”是天地之道的体现
《秋水》开篇述秋时水至,隔水相望,牛马分辨不清,因此让河伯误以为自己广大。河伯的洋洋自得正是因为其见识短浅,周围的环境让他在认知上没有达到“体道”的程度,才会“见笑于大方之家”,“大方”据司马彪说即“大道”。“不辩牛马”也即是“不辩道”,不辩道所以对自身没有深刻的认知,这里的牛马即是道的隐喻。
在《庄子》中,道作为宇宙的本源,其特点是无所不在,浑融一体,体现的是事物变化的规律。庄子认为道贯穿于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宋代王雱《南华真经拾遗》曰:“万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无有不在,故在大则未尝有所过,而在细则未尝有所遗,是以万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庄周之为书,而言及鲲鹏蜩莺鸠斥鹦鹩蚁羊鱼蝶马牛山木之类也。”庄子对于马之类的动物的不断提及正是其自然论的一个体现,小至虫蚁,大至鲲鹏,广而无极又细于纤毫,正是道的普遍性的显现。道生发了天地,天地生发了万物,“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在《齐物论》中有:“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成疏曰“万物虽多,一马可以理尽”(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崔撰对马的解释为“万物之一物”,王叔岷在《庄子校诠》中对马的解释为“等万物于一马”。这里的马所指代的是一个万物一体的形象化概念,象征的是宇宙万物同质,马是庄子对道的本体论的形象化表述。
在《则阳》篇中,大公调讲述“马”怎么样才能成为马:“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N87GrhBuILN0kkfXwtnVZg==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只有马的一个部分是不能被称为马的,但将这些“百体”组合起来便成了马。在《秋水》篇中,河伯问天人区别,北海若认为牛马天生就有四足,不是人为所赋予的。天即是道,是不受任何人为破坏浑然天成、遵循自然的样子。这种浑融一体的观念即是天地自然的“合则成体,散则成始”。
由此观之,庄子将马作为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一个象。在这之后,少知问道,大公调的回答是:“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读之则可也,已有之矣,乃将得比哉!则若以斯辩,譬犹狗马,其不及远矣。”
大公调将丘里比作狗,明确地将道比作马。道是统揽了天地、阴阳之气、万事万物的,正同《齐物论》所说的“万物一马也”相符。
在《至乐》篇中,庄子讲述了一个生物转生衍化的过程,一个自然造化生生不息的系统,而其中有“马生人”一说。以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马生人”是荒诞不经的,且时间久远,其真实性也已难考辨。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故事中的程看作具体的程,马看作具体的马,只将其视为万物循环中的“气”的一个形态似乎一切就又可解了。庄子妻死,他鼓盆而歌,是因为他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气聚而生,气散则死,气遵循着道的规律在整个宇宙万物中循环往复。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马生人”也即是“气生人”,“通天下一气耳”是事物的运行规律,正是道的体现。
在《庄子》开篇《逍遥游》中,有“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历代注家对于“野马”的解释有“游气”和“尘埃”两种。郭象明确指出,“野马者,游气也”(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成玄英疏,“此言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司马彪认为,这是春天山泽中的游气;崔撰也认为,“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王叔岷《庄子校诠》);陈鼓应也认为,“野马,谓空中游气”(《庄子今注今译》)。以上几例都认为“野马”是天地之间阳气蒸腾滚动的样子,这正是天地之道运行之时的状态和显现。
四、马是通达道的媒介
马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动物。河图的来源传说就是“龙马负图”,龙马所扮演的是“天命”的使者。《周易》中的马,虽然有重“象”与重“数”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向,但无不以马代表天地。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人眼中,马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庄子》中的马成了通达道的媒介。在《至乐》篇中,庄子在楚国见到道旁枯槁的髑髅便用马捶敲打以问道,然后髑髅便在梦中向庄子讲述了以天地为春秋的自得之乐。“马捶”即是马鞭,以马鞭击打髑髅,庄子知晓“死生之理均齐”(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马捶”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与髑髅的沟通之门,庄子的问道之路。《田子方》篇讲述文王为了请姜子牙出山便假托于梦,在他形容的梦中指明道路的良人的装扮是“黑色而髯,乘驳马而偏朱蹄”,这位指明了方向的神使骑了一匹杂色且一蹄偏赤的马。尽管这个故事为文王虚构,但从他所虚构的这个人物形象可以看出人们认为带来“天命”的人是骑马之人。
同样一个驱赶马的人出现在《徐无鬼》篇。黄帝同七圣为了见大槐迷路在具茨之山,成疏曰:“大槐,大道广大而隗然空寂也。亦言:大槐古之至人也。”(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后世也多秉持这两种看法,将其视作大道或神人,所以可知黄帝此行是为了访道。就在迷路之际出现了一位“牧马童子”,成疏直接点明“牧马童子”即是得道之人。结合上文对于马作为自由精神的代表、道的象征,我们可以推测“牧马童子”是具备了自由精神,驾驭了道的人。在黄帝问他可知大槐之所存时,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进一步验证了他是体察了道的高人。黄帝在之后的对话中又两问天下,牧马童子也给予其答复,且以牧马作比:“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治理天下不过和牧马一样,“害马者”在这里指的是分外之事,即是不守己之人。
无论是“马捶”还是“驳马”,抑或“牧马童子”,都可以发现马是具有某种神性的,是传播道的信使。当人们陷入迷惘而不知所处的时候,马可以作为通达道的媒介来为人们指明方向。
《庄子》之文所表述的哲理往往幽微精妙,常常采用艺术形象来对其中内容进行阐发,是中国取象思维的一种延伸,需要用精神的目光去观看。《庄子》中的各类“马”的意象含义丰富,但其背后依赖的是庄子“齐物论”的思想,表现的是庄子对于“道”和自由人生的不懈追逐。通过对马的动物特点的进一步生发,庄子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形象化,借动物以明道,让人们能够有一个具体的物象去体悟道的存在和形式。奔腾的“野马”也正如庄子那颗向往“道”的心驰骋在自由的原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