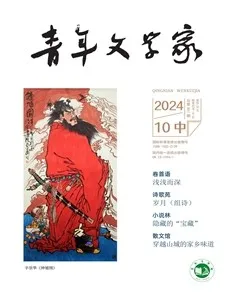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骆驼祥子》与《悲惨世界》中女性悲剧的异同比较

老舍的《骆驼祥子》创作于战火纷飞的1936年,描绘了战乱之中北平的众生相,许许多多的小人物构成了这一人间悲剧。祥子在追求个人事业的路途中被病态的社会摧残与吞噬,而一众女性更是在男权社会当中“失语”。虎妞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由自由洒脱变得脆弱;小福子为养家糊口失去贞洁,在世人唾弃中走向死亡;夏太太在压抑中沦为封建夫权制度的祭祀品。男性霸权统治成了她们悲惨人生的导火索。雨果的《悲惨世界》同《骆驼祥子》一样,以冉·阿让的经历为线索,描绘了黑暗社会当中底层人民的穷苦生活,其中的女性形象也都难逃悲惨的命运与社会的压迫。本文着重分析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解读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异同,探究造成悲剧的缘由,“从一个人的故事,读懂一类人的命运,窥见一个时代的缩影”(郑若丽《从小人物看老舍小说的叙事艺术—〈骆驼祥子〉名著专题复习教学设计》),并由此进一步探析两位作者的女性观。
一、《骆驼祥子》中的女性悲剧
(一)男性霸权的挑战者—虎妞
虎妞同传统小说当中的女性形象都不相同,与老舍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也大相径庭。老舍曾说“要娶,就娶个能作贤妻良母的”(老舍《婆婆话》)。因此,在老舍女性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虎妞这一形象注定是以悲剧结束生命。在外貌方面,虎妞人如其名,虎头虎脑,其貌不扬;在性格方面,也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温婉端庄,她聪明而且善于理财,把父亲的人和车厂打理得井井有条,是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在那个压迫女性的时代,有着现代职场女性的风范。除此之外,虎妞对待爱情义无反顾,即使祥子一无所有,而自己是富甲一方的车厂女老板,也无所畏惧地放弃所有、大胆求爱,嫁给祥子。
在如今的社会看来,虎妞雷厉风行的管理才能,对祥子的觅爱追欢,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在她的身上甚至有许多优秀品质,但她在当时的社会却遭人白眼与唾弃。在这样的社会中,虎妞是尝试过挣扎的,她不断对抗自己的父亲,争夺车场的控制权,并且和祥子结婚来试图挣脱父亲带来的枷锁。但在与祥子结婚之后,虎妞又跳进了另一层囚笼,最终难产而死。
(二)男权压迫下沉默的反抗者—小福子
比起虎妞,小福子是完全不同的。她美丽善良温柔,是祥子真正喜欢的人。但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创伤是巨大的,她在十九岁被卖给了军官。卖了女儿之后,她的父亲却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做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不仅自己的亲生父亲将自己当作物件,文中的军官也将女性物化,打仗打到哪儿,军官就在哪里买女人,而后安家;等军队撤走了,就把姑娘抛弃了。他们高兴时给几个铜板,不高兴就把女人晾在家里,女性在男权主义社会当中成为可有可无的小玩意儿。
小福子被军官抛弃后,她的人生却再一次陷入低谷。一是被父亲逼迫,二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弟弟,不得已出去“卖肉”,成了人人唾弃的“娼妓”。自己的尊严被人践踏,她想过逃避、想过自杀,但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自己的弟弟,选择继续忍受,坚强地在这“吃人”的社会当中活了下来。但最终她还是被卖去了窑子,带着控诉自杀了。这是对男权压迫的无声反抗。
小福子和虎妞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和她们有着相同境遇的千千万万女性的缩影,两人在外貌、性格等方面大相径庭,但最终的结局都是凄惨的。在家庭层面,虎妞有一个强势的爹,掌管着人和车厂。虎妞的成长环境当中少有女性的出现,逐渐滋养了她变态的心理;而小福子的父亲脾气暴躁,酗酒成狂,将自己的女儿当作物件随意变卖。在社会层面,虎妞拥有着不被社会认可的管理能力,父亲也只把她当成维持车厂秩序的工具;而小福子在与军官的不良关系当中选择承受,在父亲的压迫中也选择妥协。这都是因为在男性霸权的社会当中,受压迫的她逆来顺受、软弱妥协,缺乏独立,没有反抗意识。
二、《悲惨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一)一生的苦难—芳汀
在小说开篇,芳汀是极为美好的。雨果不遗余力地用大量笔墨塑造芳汀,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那脸蛋儿光艳照人,倩影娉婷,眼珠呈深蓝色,眼皮儿如凝脂,双足娇小而翘起,手腕和脚腕都珠联璧合,肌肤白皙,隐约显现天蓝色的脉络,面颊稚嫩而鲜艳。”除了美貌,她纯真且贞洁。雨果甚至说芳汀就是快乐,就是贞操。但纵观芳汀的一生,她一开始就是可怜的弃婴,之后是被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玩弄感情的“残花败柳”,最后为了自己的女儿饱受摧残。从一开始的美丽动人到最终面目可憎,芳汀一生的经历与前后容貌的对比突出了这一女性人物的悲剧性,也印证了雨果“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这一句话。
(二)历经波折后见光明—珂赛特
同她的母亲一样,珂赛特也有着惊为天人的美貌,雨果将珂赛特描述为“能把整个小路尽头都洒满了蓝色的光辉”。珂赛特出生后就被芳汀寄养在德纳第先生家中,受尽折磨,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幸运的是,珂赛特后来遇到了冉·阿让,被他收养,接受了来自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无微不至的爱。但不论是与冉·阿让的相处,抑或在与马吕斯的恋情当中,都可窥见珂赛特性格当中的软弱与妥协。在一段看似平等的恋情当中,珂赛特却是毫无主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吕斯言听计从,仿佛马吕斯是她的上司,甚至冉·阿让只是让珂赛特在家中放一把椅子,珂赛特都战战兢兢,想先问过马吕斯的意见。尽管珂赛特拥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但她的精神依然是贫瘠的,在珂赛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见在男性霸权的社会当中的女性的卑微。
这一对母女存在许多共同点。首先,二人都拥有国色天香的容貌,这是贫穷也无法掩盖的。其次,二人都饱经风霜。芳汀在成为弃妇后,独自生下孩子,并被德纳第先生一直压榨,最终沦为娼妓,走向死亡。珂赛特在儿童时期遭受德纳第一家的虐待,被当作奴隶使唤。第三,二人性格都比较软弱,无法独立,始终依附着男人。芳汀年轻时始终都想着靠自己的美貌寻找良人,攀附上有钱的公子哥,成为有钱人的太太,但最终成了弃妇;而珂赛特在与马吕斯的婚姻当中,就如菟丝花,需要人精心照料,且毫无主见。这足以体现在当时社会中女性的软弱与温顺。二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芳汀结局悲惨,而珂赛特有一个好的结局。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仅只体现在《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的身上,也体现在他对自己笔下无数女性形象的怜悯当中,珂赛特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女性悲剧成因探析
尽管身处的国家以及时代都不相同,但老舍与雨果笔下的女性形象却有着相似之处。例如,本文提到的四位女性角色都希望通过男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是在经济上依附着男人。虎妞希望通过与祥子成婚摆脱刘四爷的掌控,小福子在虎妞死后无数次地暗示祥子自己对他的爱慕,希望通过祥子扭转自己沦为暗娼的命运。芳汀将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成为阔太太的命运,寄希望于男子能够看中自己的美貌;珂赛特在与马吕斯成婚后,彻底沦为了菟丝花。除了珂赛特,其他三位女性的结局都是悲惨的:虎妞难产而死;小福子忍受不了自己的尊严被践踏在地上,上吊自杀;芳汀容貌尽毁,香消玉殒。而珂赛特的结局看似美满,但她在精神上依然是贫瘠的,往后余生,都只能在马吕斯的鼻息之下讨日子。
造成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四位女性都生活在男权社会之下,受男性的压迫。尽管虎妞的性格较为泼辣,与其他三位女性温顺的性格有些许不同,但也难逃男性霸权的压迫。
(一)父权压迫—虎妞、小福子
虎妞变态心理的养成,大多归因于他的父亲。因为父亲的自私,虎妞一直到四十岁了还没嫁人,养成了自私、泼辣、精于算计的性子。刘四爷先是将虎妞当成免费的车场管家,而后极力阻止虎妞和“臭拉车的”祥子厮混在一起,阻止不成,就狠心和自己的亲生女儿断绝了一切关系。之所以能对自己的女儿下如此狠心,就是因为刘四爷认为自己的权威地位竟然被一个女人挑战了,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应该任由自己摆布的女儿。由此可见,导致虎妞悲剧人生的原因之一便是父权的压迫。
小福子的悲惨结局缘由之一来自嗜酒成狂、好吃懒做的父权打压。她先是被自己的父亲卖给了军官,成了军官的掌中之物;而后又在父亲的压迫之下成了暗娼,讽刺的是小福子为了养活全家去“卖肉”,而懒惰的父亲却还看不起自己的女儿;0Kecz5DVUuZgf91S67hvpOQkOjB9tr/iBx5QsRuRUw4=最后父亲又为了臭铜板,把亲生女儿卖到了白房子做妓女。小福子的人生完全不属于自己,而是被自己的父亲随意买卖。
(二)夫权压迫—芳汀、虎妞、珂赛特
在表面上看来,祥子与虎妞的婚姻中,祥子是受害者,其实虎妞也是这一段婚姻的受害者。在婚后,虎妞一心一意地想和祥子过好日子,但祥子对虎妞已经恨之入骨,面对虎妞时,只剩下了冷暴力,甚至心中有不快,也只会跟外人吐露,绝不会跟自己的结发妻子说真心话。在故事接近尾声时,祥子碰上了刘四爷,他像是在报复一般把虎妞难产而死的消息告诉了刘四爷,且半点儿都不愿透露虎妞的墓在哪里。尽管这样确实达到了报复的目的,但虎妞唯一的亲人都无法去祭拜自己的坟墓,为死后的虎妞更添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芳汀对男人的恭顺且将自己成为阔太太的美梦寄托在男人的身上,本身就是在男权压迫之下的产物。甚至芳汀在被多罗米埃抛弃之后,她的反应并不是反抗,而是妥协与接受。芳汀的女儿珂赛特与她如出一辙,在潜意识当中就将自己当成男人的附属品。《悲惨世界》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德纳第太太,对德纳第先生已经不是用“顺从”二字可以形容的了,而是完全服从于丈夫的命令,对自己的丈夫恭敬而虔诚。
四、老舍与雨果的女性观比较
经过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老舍与雨果在女性观上存在相似之处:
首先,以男性视角看待女性。在中国大多数男性的心中,贤妻良母有着固定的形象,如美丽善良、温柔恭顺、勤俭持家等,老舍自然也不例外,《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老舍对虎妞这类有悖传统妇女形象的女性总体上是持批判的态度。
在《悲惨世界》中,也不难看出雨果始终以男性的视角出发去定义女性,比如他将芳汀、珂赛特等正面人物写得年轻漂亮,且极尽渲染她们玉骨冰肌;而一些反面人物,比如德纳第太太,便是其貌不扬。再比如本书中大多数女性的性格都是温柔恭顺的,如他精心打造的女主人公—珂赛特,也是凭借美貌与对丈夫百依百顺的性格,才摆脱苦难,拥有了美满的结局,但不论是在经济上、心理上都始终依附在男人的身上。此外,还有雨果对女性贞洁的重视,他在第一卷中反复强调芳汀是贞洁的,这是芳汀区别于其他三位女性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难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带着男权意识去凝视与定义女性的,他们用自己心目当中喜爱的、向往的女性形象去描绘书中的正面与反面女性形象。且女性的社会地位由男性决定,女性的命运由男性摆布,如芳汀试图用自己的美貌吸引男性提高自己的地位,牺牲了自己的光阴,可依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许的;而后她为了养活女儿,每天承担着超负荷的劳动,却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由此可见,在两位作家的笔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由男性决定的。
其次,对女性的悲剧怀有怜悯之心。两位作家都是以男性的视角去定义自己心目当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十分怜悯在黑暗社会当中底层女性所遭受的苦难。正如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提到的:“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骆驼祥子》谱写了底层女性生命的悲歌,老舍是希望中国社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当封建社会的阴霾散尽,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迎来崭新公平的社会,女性能够自立自主。《悲惨世界》亦是如此。芳汀的一生都凄苦无比,但雨果将希望延续到了她的女儿珂赛特的身上,尽管珂赛特的精神世界依然是贫瘠的,但已是为数不多拥有一个美好结局的女性形象。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对当时女性处境的深切怜悯,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由此可见,造成女性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男性霸权社会的压迫,从中可窥见老舍和雨果两位作家对女性悲苦命运的怜悯。
综上所述,老舍的《骆驼祥子》展现了封建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而雨果的《悲惨世界》则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光辉。这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表现手法也影响了两部作品中女性悲剧的呈现方式。《骆驼祥子》与《悲惨世界》虽然都深刻描绘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但二者在女性悲剧的描绘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这些异同点不仅反映了两部作品在文学风格、主题思想等方面的差异,也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命运的普遍性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