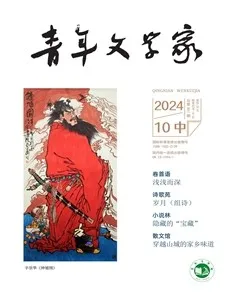历史真实与叙事策略:孔尚任《桃花扇》编撰考论

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诸家赞之不已。其实,除了叙事笔法、排场布局等艺术层面的因素之外,其主题意蕴,尤其是以征实为主的写作方式,更是在故明遗老中间取得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其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该剧的征实性。具体来说,孔尚任在创作该剧时,尤为关注其历史真实性,这与洪昇的《长生殿》等剧作,在史料来源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从史源学的角度系统剖析《桃花扇》的征实特色,可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该剧经典性的形成,提供新的参照。
孔尚任自称《桃花扇》之“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桃花扇〉小引》)。显然,在创作过程中,孔尚任既秉持了《诗经》的教化传统,又借鉴了“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更在戏剧叙事中,继承了《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的“征实”“实录”原则,由此带有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为了最大限度地在戏剧艺术中呈现历史真实与思想真实,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的过程中,确实颇费苦心。
一、口述史料与传世典籍的多重印证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得益于其舅翁秦光仪等亲属的口述。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道:“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由此可见,崇祯末年,孔尚则在南京部曹任职,算是明末清初历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明亡之后,秦光仪投奔孔尚则避乱三年,朝夕相处。孔尚则便将其亲身经历见闻,如数转述给秦光仪。后来,秦光仪归里之后,又将其在孔尚则处听闻的弘光遗事,口述给孔尚任。其中最能打动孔尚任的,当数李香君“面血溅扇”,而杨龙友又依其血迹,巧妙地点画为桃花的故事。因此,“《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桃花扇本末》)。这也是该剧得名的原因。这样一来,也就使得该剧演述的故事,并非史书记载呈现出来的冷冰冰的文字,更非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带有浓郁的历史温情。
从学理上讲,口述史确实具有贴近历史真实的一面,同时也有其缺憾,就是容易夹杂口述者的个人情感色彩,甚至不排除虚构、误记乃至张冠李戴的情况,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需要进一步核验。孔尚任作为杰出的剧作家,对此亦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了避免盲从盲信而带来的历史失实,他又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桃花扇本末》)。与一般传奇戏剧不同的是,孔尚任在剧末非常用心地编撰了附录,并详细标明了其所参照的史籍。比如,该剧取自无名氏《樵史》二十四段、侯朝宗《壮悔堂集》十三首、贾静子《四忆堂诗集》注十二条、钱谦益《有学集》十一首、吴伟业《梅村集》七首、龚鼎孳《定山堂集》二十一首等,采集范围既包括史部,也包括子部和集部。尤其是那些文人别集,可视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口述史料,其历史真实性似无可疑虑。通过口述史和历史记载、笔记、诗文的多重印证,孔尚任发现,当事人口述与史籍所载,是可以互相印证的。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而且,这种富有质疑考证的精神也为当下的人文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是经过孔尚则、秦光仪双重转述的历史,为何还能保证其真实性呢?再者,孔尚任仅为南京的部曹,对于南明朝廷的核心事件,并不一定有机会亲身参与。而且,史书记载的往往都是朝廷重大事件,对于诸如儿女私情之事,恐怕很难入其法眼,也就难以载录史册。为此,我们通过进一步追溯发现,在孔尚则口述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面的口述史。比如,堪称《桃花扇》创作核心的李香君“面血溅扇”一事,就是来自该事件亲历者的讲述。孔尚任说:“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桃花扇本末》)所谓“小史”,就是杨龙友身边的书童,自然也就是“面血溅扇”的在场者。尽管此事“不见诸别籍”,并无相关载籍可以印证,然而通过前面经过口述历史和历史典籍双得印证的结果来看,孔尚任认为,该事不仅“亲奇可传”,也是足以采信。其实这些经过“中转”的口述史实,从史源学的角度说,顶多算是“二手”材料。孔尚任自称:“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尚秘之枕中。”(《桃花扇本末》)易言之,他对这些听闻的“二手”材料,依然保持着谨慎、警惕的态度。那么,如何才能真正使之成为“信史”呢?为此,孔尚任又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的工作。
二、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的完美结合
除了史述史料与传统史籍的双重印证,孔尚任还借仕宦机会充分进行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这就是他说的“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桃花扇·凡例》)。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南下淮扬,疏浚下河海口,前后凡四年。淮扬素来就是故明遗老的重要聚居地。孔尚任初至,就主动拜访遗民高隐。比如,“屡辞聘召,益肆力于诗歌,东南持风雅者必宗焉”(《道光泰州志》卷二十六)的黄云,就回忆道:“先生(指孔尚任)初至海陵,即过访敝庐,殷勤赠答,高义不减古人。”(《湖海集》卷一)此四年间,孔尚任与黄氏父子多有往来,酒筵歌席间,必会谈及前朝旧事。而且,黄云还向孔尚任不遗余力地荐介遗民,使得孔氏快速融入江南遗民群体,频繁参加相关的文学活动。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一月,孔氏大会扬州诗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泰县署园北楼雅集,孔氏又参加春江社诗友雅集;同年十月,孔氏改兴化拱极台为海光楼,大集名士;十一月,孔氏又在扬州琼花观携友赏月。在这些文人雅集活动中,往往体现出孔尚任的高义。比如,著名遗民诗人孙枝蔚去世后,孔尚任作诗挽之,黄云评论道:“先生赐挽言,倡导海内,真吾道之主盟,预感宁止泉下人耶?”(《湖海集》卷二)再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著名遗民画家龚贤病逝于金陵,孔尚任亲自“经理其后事,抚其孤子,收其遗书。一时故老,皆感高义,泣下沾巾”(《湖海集》卷七)。这些雅集、庆吊活动背后,凸显出孔尚任对故明遗老的真心,更见其对故明旧事的真诚。故明遗老也深为感动,才会在波诡云谲的清初政治活动中,甘冒时讳,将其所知前明掌故、故事和盘托出。孔尚任在《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中说:“开瓮墙头约,天涯似耦耕。柴桑闲友伴,花草老心情。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同时夜话的邓汉仪(字孝威)、黄云(字仙裳)等,皆是颇有时誉的遗民。他们席间谈论的都是“朝皆换”,也就是明清鼎革之际的秘闻。邓汉仪在评语中说得更为确切:“漱翁以八十四老人,诗酒之兴不减。一夕快谈,差销旅寂,然不堪为门外人道。”(《孔尚任全集辑校辑评》)既然“不堪为门外人道”,那就是语涉时忌的敏感话题。这也就表明,遗民群体也全然接纳了孔尚任,且引以为同类中人,否则断然不会将不为人知的秘闻倾囊相告。这些席间访谈,自然也就纳入了《桃花扇》的写作当中。实际上,这也是延续的口述史的进路,只不过是孔尚任作为采访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亲自访求的口述史罢了。
同样,孔尚任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地考察。尤其是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开始,孔尚任登扬州梅花岭。嗣后,他又至金陵,登燕子矶,寓冶城道院,过访明朝故宫,拜谒明孝陵,游栖霞山,并至白云庵访张瑶星。这些实地考察所得,孔尚任皆笔之于诗,触发了他的兴亡之感,更写进了《桃花扇》中。他在写给王安节的信中坦言,此次金陵之游就是为了“览大邦之山河,交上国之人士,稍拓鄙见,为他日读书之助”(《孔尚任全集辑校辑评》)。其实,这些实地考察不仅是为了“读书之助”,更是为了写作《桃花扇》之助。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尚任在考察之前,是有着明确的规划和特定的安排。这都是为了使《桃花扇》成为“信史”而必须做的准备工作,更因此而对南明旧事,有着更为深切的“了解之同情”。因此,在《桃花扇》中,他才能够举重若轻地处理好明清鼎革这一特殊而又敏感的话题。其实,剧末诸如柳敬亭、苏昆生、老赞礼,于明清易代之后,在龙潭江边感慨兴亡,抒写其在此历史巨变中的内心感触和情感依托,又何尝不是孔尚任本人的身心体验呢?因此,孔尚任在《先声》中,借老赞礼之口说到《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其实也是孔尚任本人的心声。
三、叙事策略与思想真实的曲折呈现
清初政治环境颇为恶劣,表面上,清廷重开科举,诏举博学鸿词科;实际上,又严禁结社讲学。在此严酷的形势下,谈论明清易论之事,显然极易触犯忌讳。孔尚任江南采风期间搜罗到的“不堪为门外人道”的秘闻,无法通过戏剧的形式公之于众。因此,如果不进行策略性的处理,而仅如史家般直笔其事的话,难免重蹈“明史案”的覆辙。
从今本《桃花扇》来看,孔尚任也是深悉其中利害,如《孤吟》中借老赞礼之口说道:“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正是通过“含糊”与“遮盖”,才使该剧能够顺利地面世。比如,在《先声》中,作者安排老赞礼出场,自称“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并且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出现了“河出图,洛出书,景星明,庆云现,甘露降,膏雨零,凤凰集,麒麟游,蓂荚发,芝草生,海无波,黄河清”等十二种祥瑞。这显然是对清廷带有明显阿谀性质的赞颂,盖作者有意通过颂圣之名,消解世人对《桃花扇》的猜忌。更令人称奇的是,该剧虽写清兵南下、明清易代之事,清兵却始终没有出场,包括史可法的兵败城陷。其实,依照《明史·史可法传》的记载,扬州城破之后,史可法自刎未遂,被参将拥至小东门出城,却被清军捉住。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遂被杀。然而,在《桃花扇》第三十八出《沉江》中,作者有意进行了改写:扬州城破后,史可法直奔仪真,途遇老赞礼,方知弘光帝外逃。本想到南京护驾的史可法,此时万念俱灰,也就腾脱下袍靴冠冕,投江自尽,以全忠节。这样一来,既避免了清军杀害史可法,又歌颂了史氏的赤胆忠心。孔尚任又在《桃花扇·小引》中明确写道:“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呈现出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为此,他将剧作的主要矛盾迁移到南明朝廷的腐朽和权奸的误国。一方面,孔尚任重点塑造了马士英、阮大铖两大奸佞,他们视迎立皇帝为生意,为儿戏,借此谋取私利,呼朋引党,甚至向弘光帝选优献乐,而在扬州告急之时,他们却携带着民脂民膏仓皇出逃。另一方面,孔尚任又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以黄得功为代表的江北四镇武将的内斗与腐败。值此国家危亡之际,他们手握重兵,却为了争夺军帐位次而大动干戈,甚至故意移镇上江,堵截史可法军队,让清兵乘虚而入,长驱南下。更令人愤慨的是,刘泽清、刘良佐两镇,甚至把弘光帝当作宝贝,希望送与北朝后得以争功邀赏。比起史可法、李香君、复社文人,他们的恶劣行径,也就成为导致南明政权覆灭的罪魁祸首。上述的巧妙改写,不仅达到了反思明朝覆亡的主题旨趣,更使得该剧完成之后,一时洛阳纸贵,且盛演不休,甚至传到了“万山中,阻绝入境”(《桃花扇本末》)的楚地容美。
综上可见,孔尚任本着“信史”的原则,注重口述史料和史籍文献的多重印证,更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该剧的征实性。同时,他又鉴于清初严酷的社会环境,进行了策略性的叙写,将历史反思归结为权奸误国,实现了预期的写作旨趣。因此,该剧庶可称得上是“历史真实”和“思想真实”双美并重的杰作,不仅在撰成之后频繁演出,更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本文系江西科技学院校级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佛教视阈下的明末清初戏曲研究”(项目编号:232RWYB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