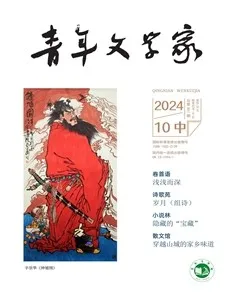从“志异”到俚曲



出身于日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和商人家庭的蒲松龄,身上寄托着家族几代人考取功名的愿望。然而,当他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的名次后,他的科举之路就此止步。但蒲松龄渴望得到认可的名士心态并未因此而削弱,反而更加激发他倾注一生心血来创作《聊斋志异》。蒲松龄在年过花甲后,创作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叙事形式—聊斋俚曲,这是根据当地的方言和俚语填词创作而成的长篇戏曲作品。它旨在“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蒲箬《柳泉公行述》),以达到劝善惩恶、教化民众的目的。
蒲松龄是一名儒士,前期不懈的科举追求也是渴望有所作为,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立功”的机会并未青睐于他,所以他转向“立言”,通过自己的胸中笔墨、耳中清谣来表现平民大众的喜怒哀乐,抒发忧国忧民之思,因此他更是一位站在农民立场的发言人。无论是小说《聊斋志异》抑或戏曲作品,都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世情味。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理解蒲松龄前后创作风格的改变和文化视角的转移,再理解戏曲本身的魅力才会更有意义。
一、《聊斋志异》:苦闷的独奏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蒲松龄出生时正值明末清初改朝迭代之际,兵荒马乱,自然灾害多发,风雨飘摇,但他对科举的追求却没有因外部环境的恶劣而有丝毫的变化与动摇。蒲松龄在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就以县、府、道三个第一的优异名次补博士弟子员,名震一时。他本以为建功立业的辉煌前景即将展开,却没料到科举之路短暂止步于此,此后的数次考试屡试屡败,皆未中举。郁闷孤愤成为蒲松龄创作花妖狐鬼故事的心理动机,如学者所言:“少负异才,以气节自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经生以终。平生奇气,无所宣泄,悉寄之于书。”(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
功名之路艰难坎坷,然而蒲松龄渴望立言的名士心态并未因此而削弱,反而更加激发他倾注一生心血来创作《聊斋志异》。在小说序言中,蒲松龄开篇就感慨自己的创作初衷,“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与司马迁和屈原发愤著书的心态一样,蒲松龄怀抱“香草美人”的政治理想,借花妖鬼狐与男女恋情之酒杯以纾胸中不平之块垒。这部孤愤之作描写的是有情的异类和无情的人类。
《聊斋志异》之所以选择花妖鬼狐作为主角,原因众多。首先,是社会动乱的时代因素。其次,是地域文化的传统因素。蒲松龄的家乡山东淄川古属齐地,有关狐狸的传说最多、最丰富,每村每户都有巫戏表演、神灵祭祀的习俗,是北方神仙方术和浪漫文化的渊薮。因此,特殊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文化的背景。最后,更重要的是蒲松龄个人的成长因素。正如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幻想只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贫乏的时候才能支配我们。……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想象便被激发起来,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蒲松龄在《聊斋自志》开篇也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这样的性格为他的文学创作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书写花妖鬼狐、幽冥异域使得郁闷孤愤的蒲松龄在现实世界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蒲松龄笔耕不辍,倾注半生心血不断修改《聊斋志异》,向同为士大夫的读书人呈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希望得到才华和志向上的肯定。所以,《聊斋志异》不仅是文言文,更是有意为文。故事叙事的裁剪安排、语言的精妙典雅,使得小说“无一字无来处”,而又出神入化、文学性和古文风格极其明显。蒲松龄仗义执言、刺贪刺虐,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在自己的笔端之下,即使这一“阳春白雪”由于语言阅读障碍致使传播范围只停留在知识分子层面,蒲松龄也毫不在意,因为这并非为了出版和稿费的功利性产品,这是仕途不顺的蒲松龄作为传统儒士真正涌动着生命意识的写作,是穷而后工的生命寄托。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发愤著书、摆脱苦闷与压抑的独奏。事实上,蒲松龄落寂苦闷的独奏不是一个人的,还属于无数同他一样,在那个时代关心世道、关怀民瘼却郁郁不得志的苦闷文人。当蒲松龄度过境况艰难的大半生后,他终于找到一条超越生活痛苦的道路,将自我的苦闷与压抑化解为救世的平和,通过文化视角的下移,创作聊斋俚曲获得心理的超越与自得。
二、聊斋俚曲:救世的合唱
俚曲又称“俗曲”,创始于民间,经过文人的笔墨加工成为艺术化的民间歌曲,兴起于元代。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繁荣,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民歌也随之引入,与原有俗曲混合交融,传播范围更大,盛行一时,因此这种新俚曲又被称为“明清俗曲”,而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又是蒲松龄创作的聊斋俚曲。
与引经据典、多述历史故事的文人剧作不同,聊斋俚曲以道德劝诫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以教化万民为己任,同时又能寓教于乐,劝诫的意味往往在喜怒哀乐中被民间百姓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感受到,这对扩大聊斋俚曲的传播范围起到很大的作用。王骥德指出:“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也。”(《曲律》)聊斋俚曲的语言通俗自然、幽默诙谐,保留了淄川一带大量的方言土语、俗谚民谣,成为底层民众传唱不衰的流行曲调,体现了戏曲创作的本色。
从题材上来看,十五篇聊斋俚曲有三种类型:一是就地取材,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二是演绎、重编以往经典的神话传说和戏曲小说,如编排《西游记》《水浒传》故事的《丑俊巴》,戏写了《西游记》中猪八戒与《水浒传》里潘金莲的艳事;三是对小说《聊斋志异》七篇作品的改写和翻新,这部分对聊斋俚曲的思想内容做了最典型的概括,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它们分别是取材于《江城》的《禳妒咒》,取材于《仇大娘》的《翻魇殃》,改编自《珊瑚》的《姑妇曲》,来自《张诚》的《慈悲曲》,将《商三官》《席方平》两篇小说融合创作而成的《寒森曲》,改编自《张鸿渐》的《磨难曲》。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数《磨难曲》,戏曲的背景是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四十三年淄川的诸灾并作,从官员对待灾荒和百姓的态度可以看出作者对贪官污吏的极力讽刺和批判。戏曲中的卢龙知县老马在灾荒来临时,不仅瞒灾不报、无所作为,反而逼迫百姓上缴钱粮、乱作为。而《禳妒咒》则将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把江城这一悍妇、妒妇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对其行为逻辑的设置也更为合理,而原著小说更强调夫妇二人的前世孽缘才是二人婚姻的障碍。因此,俚曲的现实教育意义比之小说更胜一筹,反映了百姓真实而多元的家庭生活。
聊斋俚曲与《聊斋志异》一脉相承甚至略胜一筹的是世俗化描写,将这种“俗”和大众化发挥到了极致,更详细地展示了广阔的生活面貌。蒲松龄在展开故事的同时也指导着人们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问题,无论是家庭中的夫妻问题、婆媳问题,还是邻里关系以及官与民的关系等,方方面面都给出了相当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说,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和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都真实地反映了家庭中的人伦关系,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真实心愿。
三、《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之异同
《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的风格迥异是显而易见的,为清晰表述,以下列表对比: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中年和壮年时期完成的作品,体例繁多。那时蒲松龄对科举满怀热望和理想,然而现实的冷酷和黑暗,使他不得不在花妖鬼狐中寻找知己与慰藉。蒲松龄历经数年心血将自己的一腔孤愤之感灌注在近五百篇小说之中,以至作品情感浓烈、笔触浪漫,是文人雅士皆为之称奇的志怪小说集。而聊斋俚曲大都写于蒲松龄的晚年。那时蒲松龄的热情和目光早已转向了民间,他更关注日用农桑知识的普及和对百姓道德伦理的劝惩。因此,表现在俚曲当中,其语言是浅白易懂的,感情是真切幽默的,笔调是现实主义的。蒲松龄的人生阅历使他在晚年体察到广大民众的疾苦,并与之产生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实现了从文人化书写到民间叙事立场的转变。
从根本上来说,“慰藉农人”的救世思想是《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的相同点,是扎根于蒲松龄心底深处的信仰。尽管“慰藉农人”一词是蒲松龄在年过七十的晚年才有意识提出的,但他的两种文化视角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蒲松龄的目光并不是突然在晚年就转向了底层民众,《聊斋志异》的许多素材都是来自民间,蒲松龄在街道里巷摆设烟茶,搜集往来路人听到的奇闻逸事,所以它只是借用个人笔触,抒发的依旧是普世的合唱。而通俗戏曲的魅力在早年也已然引起了蒲松龄的注意,正如学者指出,蒲松龄在青年时期就已着手俚曲的创作,对其创作模式十分熟悉,且“把多种艺术形式去芜存菁,融为一体,在俚曲写作上驾轻就熟”(郑秀琴《同枝异叶 雅俗共赏—从〈聊斋志异〉到聊斋俚曲》)。
邹宗良先生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的关系概括为“先铸剑而后打刀”(蒲先明、邹宗良《聊斋俚曲集》),一体两面,揭示出蒲松龄贯穿始终的济世救民的文化心态。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出,“梦是愿望的达成”。以此观点来看,《聊斋志异》可以被解读为蒲松龄通过笔下人物的梦境,实现其内心愿望的象征性满足;而他采用俚曲这一独特形式进行创作,让这些愿望得以真正实现。蒲松龄将满怀关切的目光聚焦于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救世情怀转化为关心百姓的实际方法。这种将文化视角转向基层,以及创作思路的更新,不仅是对他长期关注民生疾苦精神的自然延续,也是他站在农民立场,以农民视角深入晚年生活的深刻体现。也正是由于俚曲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民间生命力,帮助蒲松龄实现了救世婆心的合唱,并且为后世聊斋戏曲的不断改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真正地实现了流传不止、传唱不衰。
本文系2024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清代《聊斋志异》的图文关系研究”(项目编号:KYCX24_247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