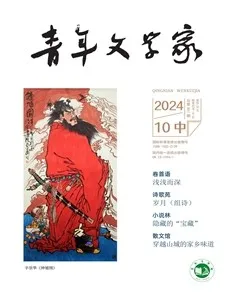疑古思想探究古史的层累修缮

疑古是对传统的怀疑,落实于治学,往往以“疑经”“辨古史”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悠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以前的先秦时代。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本文对《禹贡》成书的探究想法受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的《疑古》《惑经》篇的直接影响,本质上《禹贡》不算一篇严格的地理写实著作,其经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尚书》可以分为四个年代:史实年代、写作年代、整编年代、流传年代,《禹贡》的形成过程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乃层累修缮,很可能最终完成于战国,最早可追溯至商朝。
一、以“五服”天下观为例的成书年代探索
(一)“五服”释义
《禹贡》为篇名,《书序》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每服对当时天下首领的义务不同,天下首领对每服的要求和责任也不同。其排列顺序从中央到四方,自都城向外地。《禹贡》中写道:“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国都以外五百里叫甸服,又称王畿,种天子田,服天子事。其中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内的百姓捆束禾穗,直接缴纳;二百里内的百姓割下禾秆,交纳谷穗;三百里内的百姓去除谷穗的颖皮,缴纳带壳谷粒;四百里内的百姓交纳脱壳的糙米;五百里内的百姓交纳白色精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是王朝卿大夫及王子们的食邑与各类侯国。其中,一百里内是王朝卿大夫及王子们的食邑,二百里内是爵位较低的担任王朝杂务的小国领主,剩下三百里是封土授民的较大侯国。“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是蛮夷与中夏的缓冲地带,三百里内推行天子的文教,以文明礼貌对待外来蛮夷,外面二百里的为天子警戒。“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居民虽是夷人,但距离中国较近,心慕中国文明教化,愿意学习并结盟约,所以称为“要服”。三百里内是夷狄所居,外面二百里流放罪行较轻的犯人。“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距王城最远,其中三百里内蛮戎居住,外面二百里流放重刑犯人。
(二)“五服”中的大一统雏形
所谓“大一统”,其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大”是动词,后来大家把它变成名词。对于《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历来解释不同。但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大”作“尊重、强调”解。至于“一统”,比较常见的解释是“统一”,即国家统一于一个政权,不分裂。但《公羊传》本义似乎并非如此。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把“大一统”释作“大一始”:“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此外,六经之一的《周易》云:“《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此处“元”和“始”互训,至于“统”,郑玄在《周易郑康成注》曰:“统,本也。”前面引的就是何休的注。可见“统”和“始”都含有“本”的意思。“大一统”强调“一”的本根性和始基性。《春秋》“五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含有“一”。作为开端的“一”是一切的根本,类似于“道”或者“无极而太极”。《春秋》的“大一统”是体元居正、慎始保本之意。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此处的“大一统”也是“体元居正”的意思,谓君主以一为本,常居正道以施政教。后世将其引申为国家的统一、制度的统一、思想的统一,也是从“大一统”的“元”与“本”之意引申而来。
夷夏之辨在“五服”中的体现是很清晰的,将距离都城二千里以外的地方划为夷、蛮之地,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对夷蛮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态度,中国从礼仪、服饰、文化、经济各方面都较其他民族先进,因此会有这种自信的态度。根据“五服”记载,中国对待当时所谓蛮夷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只要他们不生事端,愿意“揆文教”并结盟约。
“九州”最为体现大一统的雏形,而“五服”中也有体现,只不过与“九州”相比,“五服”更鲜明的特征是夷夏之辨,但仔细研读也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大一统雏形。对于“服”的解释,荀子论五服制称:“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郑玄对“服”的定义是“服,服事天子也”(《周礼·职方氏》)。通过将地域划为五服,对“服”字的态度,以及《禹贡》的记载,可知蛮夷居所是流放犯人的去处。当时概念上中国为天下中心,把要服荒服也划进五服里面。结合周穆王有征犬戎之意,这种明确的夷狄之辨显然不是大禹时代所有的,而这种自信睥睨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未来大一统的发端。
其次,从《禹贡》的成书年代来看,上升到政治文化上,作为与“九州”相对应的“五服”,具备大一统的发端条件,但同时这种天下观太过超前。结合文献来看,“五服”观念的来源可能追溯到商朝的内外服,大盂鼎中就涉及商朝的内外服,铭文中的“厥匿,匍有四方”“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辞,率肆于酒,故丧师祀”,记叙殷朝无论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官员大多酗酒,导致殷朝灭亡,也见于《尚书·酒诰》。其中“甸”对应《禹贡》“五百里甸服”,国都以外五百里为甸服,可以看作商朝的内服,是直接统治地区。“侯”对应《禹贡》“五百里侯服”,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是王朝卿大夫及王子们的食邑与各类侯国,可以看作商朝的外服,是附属国和盟国。商朝的内外服制度虽然没有西周的“五服”分类那样细,但一种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其历史渊源,商朝的内外服制度就是西周“五服”制度的历史渊源。
“五服”中的天下观包含着王制的地缘认知,他们希望自己能力所及,使文教武卫及于四海之内的所有地区,“五服”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对后代的“九服”制度与大一统国家理想乃至成为现实提出先见构想。但在大禹时代,从地域观念来说不可能酝酿出这样宏大清晰、规整的天下观,这也从文化观念上反映了《禹贡》成书绝不是《尚书》中所说的那样成于大禹治水之后,其中的“五服”观念至少要在西周时期才能形成。
二、地理矛盾记载对成书年代的探究
孔颖达认为《禹贡》是夏史所作不可信,目前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有三种主流观点,分别是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又以战国时期的观点影响最大。
西周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徐旭生、辛树帜先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到:“《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其主要从文字风格上判定《禹贡》的成书年代,但文字风格后人可以模拟,因此这无法作为有力证据。徐旭生先生在《读〈山海经〉札记》提道:“《禹贡》之为书,除梁州贡铁稍露破绽外,如依其文字推测,则不惟春秋可有此等作品,即在西周亦无不可能处。盖商周之际,去禹遥遥千载,故事因民众之讴歌称颂而渐张大,既已形成。”但根据持春秋和战国观点的学者们来看,《禹贡》中非西周所作的破绽有很多,不止梁州贡铁这一项,因此从地理证据来看,《禹贡》的成书年代要晚于西周。辛树帜先生在《禹贡新解》中反复周详论证:“《禹贡》成书时代,应在西周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它是当时太史所录,绝不是周游列国‘不到秦’的孔子,也不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时的学者们所著。”从疆域和周初分封历史,从政治与九州的关系,从九山九水、五服、任土作贡等方面进行的分析,多取材于《诗》《书》,且符合西周状况。这确实是对《禹贡》的周详分析,为后人研究《禹贡》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但它只能说明《禹贡》成书过程中西周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能判定这是最终的成书年代,只有《禹贡》中出现最晚的地理证据才能判断其成书的最终年代。
支持《禹贡》成书于春秋的学者有屈万里先生,他据《左传·哀公九年》载吴王夫差“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通粮道”,而《禹贡》篇载扬州贡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几经辗转,可见此时江、淮尚未沟通,因此判断成书必早于吴越争霸之时。对此观点也有反驳意见,谭其骧先生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中认为河道变迁复杂,可能存在《禹贡》中的河流与《汉志》中的河流并存的情况,又或者从宿胥口北决堤后形成了《禹贡》河,只是文献记载匮乏,不能证明《禹贡》中的这条河流当时存在过,因此不能作为证据。
作为战国说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考证,《禹贡》也采用了战国史料,先生认为春秋之前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战国之世七国拓展疆域,才将中国疆域看成天下,又进而论证五服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至战国而消亡,而九州制是由战国时期开始酝酿的,到汉末而实现。先生在接下来又提出了五个具体论证,便不逐一列举。史念海先生也专门探讨过《禹贡》的年代,在《论〈禹贡〉的著作年代》中,并与辛树帜先生商榷过,收在《河山集》第二集。他从五个方面推断《禹贡》为战国时期的著作,其成书年代不早于公元前482年,即周敬王三十八年和鲁哀公十三年,乃吴晋黄池会盟之年,并从两个方面推断其出自魏国,这一分析为《禹贡》的成书时间及地点提出了新的见解。蒋善国先生在《尚书综述》中从九州名称由来与畿服制度的演变,以及战国铁的大量使用状况,考证《禹贡》篇最终成于战国。《禹贡》中提到梁州的贡物中有铁,虽然战国中期以前从未记载梁州出铁,梁州大量产铁在战国末期,但这不能证明战国中期以前梁州并不产铁。
综上所述,《禹贡》中有颇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春秋战国初本已发生的巨变它没有记载,但同时又记载了一些战国时期非常后来的现象,这是非常矛盾的,因而猜测现在所看到的《禹贡》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从目前最晚的地理证据来看,《禹贡》最终成书于战国时期。而关于其最早成书年代,推测最早可至商朝:首先,西汉时期的今古文《尚书》中均有《禹贡》篇,证明孔子修书时《禹贡》已经存在,要早于该时期,只是从地理记载矛盾可知后续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完全是西周春秋时期的面貌。其次,著名考古学家邵望平先生从考古角度作出判断,认为《禹贡》的蓝本出现在前,其后经过加工才呈现出现在所见的面貌。对于《禹贡》的蓝本出现年代,他在《九州学刊》发表过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商朝的地理条件与《禹贡》“九州”划分颇为吻合;从青铜器的出土、武丁时期的甲骨材料来看,商朝文化的发达程度不亚于西周初期,武王、成王时期有文献传世,商朝史官也具备了形成《禹贡》蓝本的条件。从上述条件来看,《禹贡》的初始形态可以推测到商朝,而其地理与西周东周实际地理的矛盾以及自身地理记载的时间矛盾可以证明,《禹贡》最终成书于战国,作者为不同时代的人,且是一个层累修缮的过程。
本文主要探讨了“九州”的划分背景,并以“五服”中的天下观为例对《禹贡》的成书年代进行初步探索,最后通过地理记载中的矛盾分析成书的最晚时期为战国,最早可推至商朝。在过程中有很多以目前的学识无法认识与分析到的地方,个人的一些论证与结论都有所欠缺,在日后将不断阅读相关原典,追寻学界进展,以求更好地完善目前还不成熟的想法。
回到疑古思想,按《尚书》说法,《禹贡》作于大禹时期,若古人不敢疑古或没有疑古意识,无数有价值的研究都将湮没于历史潮流之中。刘知幾的《疑古》和《惑经》两篇,历来被认为是疑经思潮的开山之作。如果经典不容置疑,将如19世纪、20世纪的海外汉学家所言,儒学禁锢了国人的思想,阻碍了国家发展。但禁锢思想的不是儒学,儒学本身是非常伟大的文化发明,任何文化都不是绝对和永远正确的,真理也有时代性和条件性,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后来人会发现五经也会有错误,而他们敢于质疑,并寻找正确的答案,文化便在不断发展中延续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