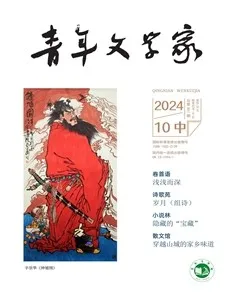乡村振兴:以诗歌的形式回应新时代文艺思潮

诗歌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体裁之一,其对时代话语的在场性表达始终都是文学书写时代不可缺少的声音。王单单的诗集《花鹿坪手记》是以诗歌形式回应新时代乡村振兴文艺思潮的典范之作。本文拟以诗集《花鹿坪手记》为例,从诗境、诗情、诗艺三个方面对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创作作具体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创作的时代价值,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乡村振兴语境下的诗歌创作
海德格尔曾提出过“诗人何为”(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以此来强调诗人歌唱时代的使命与担当。他认为诗人作为“潜入黑夜”的“冒险者”,其职权和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应该成为诗人诗意的追问。因此,在乡村振兴这股声势浩大的文艺思潮中,诗歌自然不会缺席,其对时代话语的在场性表达始终都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文学创作书写时代的重要版图之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密切相关,且有着庞大的脉络。从刘大白的《卖布谣》到臧克家的《难民》,再到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乡土诗作为乡土文学脉络的一部分,一直都在以诗意情怀书写乡土大地。虽然1949年以后的许多乡土诗仅从“题材”层面对生活作时效性反映,但20世纪80年代伊始,新边塞诗和新乡土诗的出现,昭示着诗歌在乡土书写的长河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振兴题材诗歌,作为乡土诗在新时代的延续,有着属于乡村振兴语境的特点。它们力求通过贴近现实的书写,来揭示乡村振兴发展与乡土传统性之间的平衡,其中延续的乡愁和焕发的精神力量,则表现着乡村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存在形态。被评论家王士强称为“主旋律写作样本”的《花鹿坪手记》,很好地体现了“大”与“小”的辩证统一,诗人没有因乡村振兴这一时代大主题而抛弃自己的形式,也没有被响彻其中的欢呼完全同化了自己的声音。他投身云南“花鹿坪村”这一乡村大地的一隅,将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具化为生动鲜活的小细节,在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形象中延续着宏阔的新乡村想象。
二、《花鹿坪手记》:诗歌介入现实的努力
与以往的乡村诗意书写不同,《花鹿坪手记》这部诞生于乡村振兴语境下的诗集,是王单单作为驻村扶贫队员的亲历见证,不仅保留了他写作乡村诗歌特有的灵气,还激活了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诗意之间的关联。
(一)诗境:再现安放乡愁的精神原乡
《花鹿坪手记》以乡村变迁为主线,涉及花鹿坪村的方方面面。王单单通过对乡村环境变迁的记录和对乡村情境的建构再现了花鹿坪村在脱贫和振兴过程中的深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王单单融入了自己切身的生命体验,以宛若家乡的花鹿坪村为原型再现了安放自己乡愁的精神原乡。
1.乡村环境变迁
王单单对花鹿坪村这一精神原乡形象的塑造,是通过“博物志”式的书写展开的。诗人耐心而深情地细数着花鹿坪村的细枝末节,甚至专设《花鹿坪风物谱》一辑来展现乡村的美丽,诸如早春时压满枝头的梨花(《早春》),暮春时漫山遍野的苹果花和遍地疯长的野草(《暮春之初》),月上柳梢和蝉声止息的寂静黄昏(《黄昏记》)……这种对乡土大地的审美发现,昭示着乡村美感已弥漫于乡土自然的每一个角落,不经意间便可被发现。除此之外,《花鹿坪手记》还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为背景存在的“碎片式”乡土景色用诗歌串联起来,使其“完整图像化”。由此,幽美静泊的诗境随之出现,乡村振兴变成了诗意的现场。王单单借助这一诗境,唤起的是人们对乡土之美的记忆。其意在表明,乡村不只有“泥滋味”和“土气息”,天然的美丽使它本就有被振兴的价值。与自然风光同在的是并不理想的人居环境,通过对其变化的书写,乡村振兴的成果得以具象化。从坑洼泥泞的土路到平坦硬化的公路,从破旧的土屋到崭新的楼房,从垃圾遍地到干净整洁……位于大地褶皱中的花鹿坪村沐浴在乡村振兴的阳光下,焕发了新的生机。
2.乡村情境建构
柄谷行人在《风景之发现》中认为,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它被发现、被意识从而进入审美视野的过程,紧密关联着主体观照世界的方式。与乡村环境变迁一起被纳入“博物观照”视野的,还有花鹿坪的“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调动自我感情,将个体命运和人际关系组合成以乡村情境为表现形式的艺术体系,以此来提高诗歌的审美品质。
在《花鹿坪群像图》一辑中,诗人描写了各种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诸如不忍杀羊的牧羊人(《冬至》)、从容坚毅的补瓦人(《补瓦记》)、舍己为人的老党员罗泽新(《老党员》)等。王单单欣慰于他们身上闪烁的美德和点滴的进步,却也为他们身处其中而不自知的惰性和愚昧感到焦虑。他在《融化记》中耐心劝说不修牛圈的养牛人,在《激发帖》中训斥懒汉,在《村中巡记》中劝返辍学打工的女孩……这些独具个性的村民,如同大地上坚韧生长着的一切,潦草而又神圣。除此之外,乡村振兴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易地搬迁、故土难离、疾病缠身、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基础设施改善等。王单单扎根花鹿坪村,又跳出花鹿坪村,他把花鹿坪村的变迁过程看作是整个中国大地变革的缩影,从侧面折射出了时代的波澜壮阔。王单单曾在《诗歌作伴好还乡》中直言,希望在诗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庄,为期两年的扶贫实践,他见证了花鹿坪村的变迁,花鹿坪村也因此变成了凝聚着他情感的家园,成为他安放乡愁的精神原乡。
(二)诗情:回望原乡形象的人文关怀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写作《花鹿坪手记》的过程其实也是王单单和花鹿坪村的一次互相发现。诗人扎根乡村,用生命来体悟花鹿坪村的一草一木,而花鹿坪村善良淳朴的村民也温暖了他的人生。
《花鹿坪手记》写尽了人生百态。在《放牛郎》中,他赞美把牛看得比人还金贵的“放牛郎”;《花鹿坪手记(二)》里,他感动于依偎稻草人睡着的老寡妇陈石芳;他共情于《慈母》里为给儿子减负而去苹果园打零工的六十二岁老人……诗人怀着深厚的情感,带着对世事人情的体谅,将一个人的命运娓娓道来。然而,好的主题诗歌创作,是会从“小我”走向“大我”,由“个人性”上升到“时代性”的。在《新时代》《花鹿坪变迁帖》这样充满正能量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视野境界的升华。在《假如没有扶贫》中,诗人从脱贫民众的小人生中看到了扶贫工作兼济天下的大慈悲,“假如没有扶贫,再富强的国家/失却兼济天下的慈悲,也只是徒有虚名”。在《中国民工》里,他以“时代的英雄”致敬乡村建设工作的参与者,响应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论断。面对乡村振兴这样的时代变革,来自乡村的诗人热情地投身其中,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建构了诗人“在场”的诗歌价值体系。
(三)诗艺:诗性叙事的创造性表达
为了建构“花鹿坪村变迁史”这座整体建筑,王单单在《花鹿坪手记》中延续了自诗集《山冈诗稿》开始就一直坚持的叙事性写作手法,并赋予了这一手法新的变奏。在《花鹿坪手记》中,散点透视变成了整体建筑,花鹿坪村鲜活又散乱的故事被整合成了诗的经验,呈现出个体之和大于整体的诗美效果。
王单单在这部诗集中一改之前单向凝视的写法,他将目光聚焦于留守儿童、老党员、残障人士等村民的同时,也在自我反视。他借花鹿坪村民的困顿与劳苦来写自己的父辈,在群体聚焦中发酵诗意。通过对花鹿坪群像的描绘,一种在国家意识形态背景下建立个人话语的历史意识在王单单的诗里成长起来。以此为统摄,王单单恰到好处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其呈现为“由叙事抵达抒情”的路径。例如,《种子》一诗,整首诗都在讲李三元晒茄子的方法,直到最后才点出种茄子的目的“李三元拿去集镇上卖了/换成妻子的药钱”,此刻诗歌不再清淡如水,而是饱含着李三元家的辛酸与不屈。经这两句反推前文,诗歌开头“土墙上挂着一个茄子/被风吹着,荡来荡去”和“把茄子从内部撑开/以便阳光照进去”在单纯叙事之外,也将“茄子”和李三元家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了一起。同样,在《花鹿坪手记(二)》中,诗人身上的泥土却是“小小的误会”,其中“藏着苍天/巨大的慈悲”。这本诗集大部分都是这样以事传情的书写,据此,吴思敬在《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庄—王单单诗集〈花鹿坪手记〉序》中指出,王单单所秉持的叙事原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这种叙事并不以全面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或塑造一个人物为目的,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某一瞬间,因此来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和某种体悟,从而达到对现实生存状态的揭示。
三、以诗歌形式书写乡村振兴历史进程的时代价值与存在问题
回望新诗历史,每一次时代的变革都会使诗歌的面貌发生变化。在此次乡村振兴的浪潮中,以《花鹿坪手记》为代表的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创作通过诗人个体和国家整体的对话彰显了诗人的“在场性”,为乡村振兴实践注入了诗意力量。
(一)为乡村振兴实践注入诗意力量
以《花鹿坪手记》为代表的乡村振兴题材诗歌以文铸魂、以文兴业,将诗歌的诗意之美洒在了乡土大地上。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乡村环境和生活情景出发来构造诗境,记录着诗人身处其中的真情实感。此时,乡愁不再只是知识精英站在启蒙视角上俯视乡土中国的代名词,而是诗人以“贴着地面飞行”的方式为变化着的乡土大地挥洒下的诗意,这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真实而又深切。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诗歌作为审美特性与政治功用的结合,是诗人群体对时代主流话语询唤的回应,这展现了诗人想象时代共同体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中,诗人对时代共同体的想象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乡村振兴既是振兴乡村也是想象乡村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诗歌将这一基于现实的想象过程描绘出来。第二,诗歌想象时代共同体的努力,体现了诗人以诗歌介入现实的文学观。第三,乡村振兴在当下并不是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诗人不仅要忠实地记录这一历史进程,还要对其进行个体的展望。
总体来看,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创作作为诗人在时代回响中建立起来的精神化现实,在诗学和社会学的深度对话中激活了诗人的感物能力和现实精神,其最终意欲达成的是以诗歌之“真”为呈现形式的“诗性正义”。
(二)“同质化”的整体创作倾向和缺乏精神升华的浅表叙事
就目前而言,现有的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创作已然在助力时代意识形态宣传的过程中,凸显了中国政策的优势。但“同质化”和缺乏精神升华的浅表叙事的创作倾向,仍是目前大多数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创作的弊病。乡村振兴实践的实施手段和理想目标都是在国家的统一号召之下进行的,作家面对相似的过程难免会遇到“同质化”的问题。所以,尽管该题材诗歌创作数量不少,但优秀诗歌却不多,大多都流于概念化、模式化。由于一些诗人对乡村振兴政策的认识还不深刻,往往看不到乡村变迁背后的本质,因此当下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叙事仍停留在浅层,缺乏打动世界读者的力量。乡村振兴作为国家行动,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文学书写和政治实践的结合,始终存在着一些无法忽视的先天性悖论。主题诗歌创作往往变成“唯主题”诗歌,个体性、文学性在突出“主题”创作的同时很容易被政治性、社会性所取代。即便是《花鹿坪手记》这样的佳作,也难免存在着语言过于生活化的问题。
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诗歌创作作为新乡土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语境之下,也在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为乡村振兴打造诗意现场。然而,面对目前“同质化”和缺乏精神升华的浅表叙事的创作倾向,诗人应重新思考诗歌创作和时代精神表达之间的关系。当“同质化”成为主题诗歌创作脱不开的魔咒,王单单选择投身于实践,以真实体验来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创作出了乡村振兴题材诗歌佳作—《花鹿坪手记》。这对处于“同质化”困局的乡村振兴诗歌创作而言,无疑具有普遍意义。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绝不是直线式的简单书写,在时代的多棱镜中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呈现。新时代诗人不能唯题材创作,而应该在审视社会景观嬗变的同时,回到诗歌本体性和个人主体性的本质上来,以文学性的方式将时代和现实转化为具有独创性的审美经验。乡村振兴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大事,对于全世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如何写出具有人类共情性的乡村振兴题材诗歌,让诗歌始终在场,这对当代诗人来说是一个艰巨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