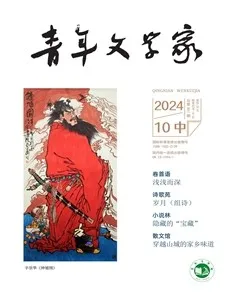符号美学视域下的《人生大事》戏剧分析

2022年上映的电影《人生大事》聚焦殡葬题材,以诙谐幽默又极具温情的风格讲述了一对半路父女的温情故事。影片承载好好活着、珍惜当下的主题,以诙谐幽默又极具温情的风格讲述了孤女武小文和殡葬店老板莫三妹的治愈故事。机灵古怪的武小文在相依为命的外婆去世后遭到舅舅一家的嫌弃,愈加孤苦无依,机缘巧合之下寄宿于老板莫三妹的殡葬店,在经历了一场场啼笑皆非、感人至深的殡葬典礼后,二人互相成为对方的救赎,结为养父女关系生活在一起。下面将运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神话的隐喻内涵和戏剧内涵、镜像认同机制、电影与梦的精神分析等理论对电影《人生大事》进行美学阐释。
一、电影符号美学的理论阐变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符号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我国学者赵毅衡在1993年曾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即“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如今符号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被广泛地应用到包括绘画、音乐、建筑、电影、语言、文学等诸多其他学科领域。
随着当代工业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影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电影符号学就是在此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理论。20世纪中叶,克里斯蒂安·麦茨在其论文《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一文中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进行创新性发展,阐释了关于第一电影学符号的基本理论,探究了电影镜头的符号学意义和影片文本叙事结构的符号特性,将叙事电影和影像外的视听符号、文本语言、叙事结构等明确为电影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初步建构起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电影符号学理论。之后,克里斯蒂安·麦茨又融合了弗洛伊德、荣格和拉康等人的理论,在第一电影符号学的基础上阐发了第二电影符号学,提出了电影符号学的电影镜像认同机制、电影与梦的精神分析、电影角色符号的直接性、假定性、隐喻性等创新性理论,将电影研究的对象从叙事电影、电影文本拓展到电影观众,构成了电影制作与电影观看的双向编码与解码的艺术过程。电影符号作为视听美学的载体,其蕴含着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分析电影符号及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排列组合,从而全面了解电影符号的形式、影片的内涵以及人在观影过程中的审美体验。纵观电影符号学的理论发展脉络,我们不难看出电影符号学就是对电影的符号进行分解重构,对电影的各种细节做微观与宏观的解剖,从而构建起一个共通的电影符号美学创作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
二、《人生大事》视听符号的能指与所指
电影符号学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对电影艺术的符号信息进行编码、解码以及重新组码的过程。在欣赏观看一部电影艺术作品,观众总会第一眼被电影角色的造型、言语、动作所吸引,对演员的声台形表作出自己的艺术判断。对电影塑造而言,电影角色塑造得是否真实立体、生动鲜明对电影成功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电影角色身上的表意符号和深层隐喻,正是观众理解电影故事文本和创作者思想内涵的展示窗。
电影《人生大事》采用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视听符号。影片开场以张巧珍演唱的楚剧《寻儿记》的选段“年复年”为背景音乐,直接将观众拉入到充满地域特色的武汉烟火人间场景,同时戏曲唱词运用精妙得体,与电影主题交相辉映。音乐的选配一直是电影精心构造的部分,恰当的音乐会渲染氛围,影响观众的情绪,甚至可以和电影情节呼应,增加电影作品的张力。由于符号传达功能的差异,影视中的声音符号可划分为指示性声音和非指示性声音,也可按照创作主体和创作方式的不同划分为人声、音乐和音响。电影开场的电话铃声和小女孩的一声声四川口音的“外婆”属于指示性声音,指示性声音具有明确的声源,更能引发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作为承载着信息的能指符号,引导观众去探究其隐藏的信息。小女孩和外婆家中的麻将、广场舞扇子、全家福、一盒盒的药物、墙上的涂鸦、儿童蜡笔画以及孙悟空与哪吒的挂画,这些视觉符号营造出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场景,参与构成该影片整体现实主义的基调。
李·斯特拉斯伯格认为创造表演人物的首要任务是关注语言。语言的地方特色、语气的轻重缓急、语调的高低变化是塑造影视角色整体形象的重要听觉符号,对其进行解码重组,可以有助于间接拼凑出角色的身份和性格特征,从而增加角色的厚度和立体度。例如,男主角莫三妹,设定上他是一个浑不懔的武汉人,因此影片中呈现出来的莫三妹操着一口急躁的汉腔,时不时还夹杂几句汉骂。武汉方言包括武昌话、汉口话、汉阳话以及青山话等不同类型。演员朱一龙在塑造莫三妹的语言风格上,就采用了多样方言进行表达,如莫三妹和父亲以及大姐交谈时的武汉本地口音;与日常生活在一起的外地朋友,这时他的语言就转变为武汉话和普通话的夹杂,不像本地武汉话那样难懂,但同时又极具武汉生活特色。而在与陌生人沟通时,莫三妹的语言表达则变成了带着武汉口音的普通话。通过影片男主角莫三妹的语言符号,我们可以从背后探究到武汉本地的语言习惯。一部好的作品,不仅仅通过观影时展现的符号元素为观众提供审美享受,更能让观众在观影后体会到电影作为第七艺术所展现的无穷魅力。
三、《人生大事》角色的神话隐喻和戏剧内涵
电影的本体论就是一种影像的逼真性和假定性特征,创作者通过视觉隐喻创造出直接的“符号象征”系统,将情感表达寄托于角色的视听形象,符号的隐喻性使得角色内涵更加丰富立体,具有深度和可探究性。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通过对角色表层视听符号的探究解读,接收到创作者的深层表达内涵,以此完成整个符号系统的编码和解码过程。
从影片《人生大事》不难看出电影角色符号特征的直接性、假定性和隐喻性。影片有意将莫三妹与武小文与中国传统神话的孙悟空和哪吒进行缝合,从人物性格、道具、台词、剧情等多方面进行隐喻性表达。道具符号往往被创作者赋予了有助于角色塑造和剧情展开的某些特定含义。影片中武小文扎着用红绳系着的双丸子头,这种发型也就是俗称的“哪吒头”,她手里拿着火尖枪玩具,背上背着一只独特的虎头包—“豆角”(这包上的图案与影片镜头一闪而过的《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封面上的哪吒形象不谋而合),还有外婆家里的乾坤圈、哪吒挂画,都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中国传统神话的哪吒形象。武小文的哪吒装扮和火尖枪就是她内心盔甲的外化,影片前期在与莫三妹的矛盾冲突中,武小文一直是哪吒装扮,拿着自己的火尖枪;直到武小文被莫三妹的朋友收养和莫三妹生活在一起后,才换回普通小朋友的装扮,而当莫三妹将武小文送还给归来的亲妈后,武小文又变回了哪吒装扮拿起火尖枪。观众在影片中看到的一些具体物象,都被创作者赋予了特殊的美学内涵,之后武小文放弃了亲妈而选择和莫三妹生活,和哪吒“剔骨还父”形成了艺术层面上的互文效果。如果之前和莫三妹生活是武小文无家可归的被动选择,那么这次的主动性选择,是超越血缘关系上的亲情,也让莫三妹感受到了自己的被需要,二人的精神世界同时被拯救。莫三妹的紧箍咒手环、孙悟空同款虎皮裙、五指山沙发、孙悟空摆件以及多次出现的桃子等多样元素符号都源于孙悟空,莫三妹和武小文结为父女后,便摘下了自己的紧箍咒手环,扔掉了五指山沙发。当叛逆的“小哪吒”遇上同样不服输的“齐天大圣”,两个在亲情中都有一定感情缺失的人,在一次次矛盾冲突和互相合作中产生羁绊,最终突破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结为非血缘意义上的父女。
在剧情叙事上,武小文大闹“殡仪馆”对应着神话中“哪吒闹海”。外婆去世后,武小文找莫三妹的时候,屋外是大雨倾盆的黑夜,外婆的去世对武小文这个“小哪吒”来说就是“陈塘关”被水淹了,家园被摧毁,她要和大人对峙找回自己亲爱的外婆,其精神内核都是反叛果敢的无畏。哪吒的无畏强权精神经过戏剧层面的移位,重构成武小文坚定对抗生死、拯救外婆的天真果敢。影片后半段莫三妹身着孙悟空戏服和小伙伴在戏院上演“大葬活人”,后被对方家属找上来大闹一场,啼笑皆非的故事情节配上极具戏剧特色的造型服饰,再加上《大闹天宫》的背景音乐和烟雾缭绕的场所环境,活脱脱一幅“孙悟空大闹天宫”现代演绎版本。电影结合中国传统神话隐喻致敬经典,增强了影片的戏剧美学风格和神话叙事厚度。
四、《人生大事》的戏剧造梦与镜像认同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第七卷提到的“洞穴理论”元素,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电影也恰恰是造梦的艺术,都是欲望的满足与压力的释放,洞穴构造与如今的电影院极为相似。观众的思维在观影过程中,通过荧幕进入“想象界”,对影视叙事结构和影视形象进行解码再重构,完成受众与创作的双向互动。《人生大事》以独特的视角站在死亡的终点回顾人生,在生死的边缘去审视人世间的鸡毛蒜皮。影片通过殡葬的视角,展现了主人公们向死而生的生活历程,旨在告诉人们如何好好活着。莫三妹在处处碰壁的现实和生死更替的工作中找寻自我存在的意义,孤女武小文在寻找亲情依靠的过程中成长,二人双向地完成了双方的救赎与被救赎。
“人生,除死,无大事。”正如莫三妹的父亲所言,生而为人的我们总会面临生离死别,如何正确地看待生死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终身学习的命题。《人生大事》从孩童的视角出发,去探寻死亡的真谛。“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爱过我们的人。”外婆在儿童手表里留给小文的日常关心话语正是本片的催泪之处,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认同机制是将观众与电影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是电影与观众之间的桥梁。通过观影,观众进行“知觉移情”,将自己的成长经历投射到主角身上,从而随着故事情节或喜悦或哭泣。观众审视整个影片和角色,获得心灵和生理上的满足。
莫三妹所代表的社会小人物群体,在生活的锤炼下找寻活着的意义。莫三妹的优缺点很明显,他是不完美的普通人,他所面临的家庭矛盾、心理压力和生存危机也是我们广大普通人能共情的。也正是因为角色的不完美,观众产生情感共识,感主角之所感,从影片中领悟人性之美。莫三妹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借着桃子这一符号意象传达给观众朋友。“在《西游记》中,桃子也是心的一种隐喻,这可能是它的外形和心脏多少有些相似的原因。”(叶梦寒《〈西游记〉中的〈心经〉与桃子》)在影片前半部分,莫三妹的父亲同意把殡葬店的房产证交给莫三妹时,他坐在椅子上大口吃桃,发出清脆的响声,神情难掩愉悦。而当他与前女友发生争执,武小文来捣乱打翻桌子上的一盘桃子时,正对应着床上辗转反侧的莫三妹。影片最后,莫三妹接纳武小文亲妈一起加入殡葬店的大家庭,一群人坐在台阶上吃桃子看星星,构成了温馨和谐的视觉美学画面。莫三妹对武小文及她亲妈的接纳,使得主角完成了隐喻层面上孙悟空的从“泼猴”到“成佛”的转变,他开始接纳他人,与自己、与世界和解。这是前面影片整体治愈基调的又一次升华。
如果说武小文的成长经历戳中的是中国人关于隔代亲情的渴望和情感表达,那莫三妹则更多展现的是当代社会中被现实蹉跎的芸芸众生。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人们电影符号的逼真性和假定性特征正如梦境,做梦和观影都是欲望的满足与压力的释放。现代社会的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而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一个宣泄口,观看电影便成为当代人放松身心的便捷方式。《人生大事》将死亡这件事摆在明面上讲给观众,没有过分渲染悲情,而是用武汉的烟火人间、人生的嬉笑怒骂来化解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承载着好好活着、珍惜当下的生活美学内涵。
电影处处展示着死亡,却更是向死而生,正如导演刘江江在一次专访中所言:“其实葬礼是办给活人看的,是治愈的过程。《人生大事》整个电影其实是站在人生的终点去讲该如何好好活着,我们是逆向来表达这个主题的,用活色生香、鲜衣怒马的方式去传递积极的生活态度。”在当下的戏剧创作环境中,创作者更应保持初心,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丰富立体的角色形象,扎根中华大地传统文化土壤汲取养分,以真心真情打动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