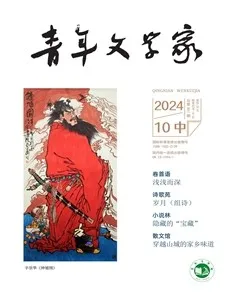韩裕文小传


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各种学术流派、思潮互为激荡,争鸣不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儒学思潮的兴起。自五四运动时,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肇端,标志着新儒学思潮的逐渐兴起。新儒家学者群体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解答中西文化转型中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在这些传统先行探索者中,熊十力的贡献无疑值得重视。熊十力(1885—1968),号子真,又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熊十力学贯古今,援佛入儒,融摄道释,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心学”哲学体系,并为20世纪新儒家的后续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提起熊十力的弟子,以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三巨子最为声名显赫,而像刘公纯、黄艮庸、韩裕文等其他熊门弟子,则湮没无闻,鲜为人知。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入室弟子的韩裕文,熊十力对其做人治学颇为称许,并尽力栽培,由哲学编译会帮助,以自费公助的方式去美国留学。惜天不假年,韩裕文英年早逝,在哲学研究上未尽其才,每念及于此,熊氏辄哀婉痛惜不已,更对韩裕文发出“吾舍汝,其谁望矣”(《十力语要》)之感慨。本文拟通过相关回忆性文字,大致勾勒韩裕文生平经历及其思想,继而讨论韩裕文求教熊十力的问学点滴,以期学界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的关注。
一、韩裕文生平述略
韩裕文(1914—1955),字质如,山东济南莱芜人。1929年,其毕业于莱芜初级中学。1934年8月19日,北平《益世报》载,北大本届新生发榜,共录取226名,韩裕文添列其中,就读于北大文学院。在北大就读期间,韩裕文戛戛独造,苦心孤诣,在中西哲学方面,浸淫至深。韩裕文和任继愈、石峻两位先生是同班同学,任继愈多年后回忆说:“韩裕文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任继愈《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1938年,韩裕文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并赴四川继续求教熊十力,研治佛学与儒学。此时,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并邀请熊十力一起授课。韩裕文跟随熊十力同赴复性书院,后因熊、马二人在治学思路方面发生分歧,加之书院内部人事矛盾丛生,彼此心存芥蒂,熊十力退出书院。韩裕文与熊十力共进退,一起返回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来凤驿黄家花园暂住。
韩裕文为学笃实,侍师毫无怨言,从无愠色,其尊师之念,维护师说态度之诚,绝无半点儿勉强。这可从徐复观、唐君毅的两则回忆材料中得到佐证:“有一次,我和他(指韩裕文)提到熊先生所说的‘超知’的问题,表明我不很赞成之意。他当时便很严肃地向我讲解了一番,内容我现在已完全忘记。不过在当时我觉得他说得很深切,很能表达熊先生的本意;我才知道他对于熊先生的学问,是实有所得的。”(徐复观《徐复观全集: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熊先生当时生活很苦,住在一花园之台阁中,只有一个床,熊先生睡床,裕文每天晚上便在楼板上睡。我去住三天,亦与他同睡楼板。他除随熊先生治学外,亦照护熊先生生活上的事。如交信、买菜,都是他的事。我在那住三日,吃饭时有肉食,但裕文却只吃菜蔬,从不拈肉,因要留给熊先生吃。”(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
熊十力早年曾在南京的一所佛学院师从欧阳竟无(欧阳渐)研习佛学,尤其在唯识学方面,造诣颇深。其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新唯识论》自出版以来,引起马一浮、汤用彤等学者的高度赞扬。熊十力对《新唯识论》一书中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用功至深,曾多次修订其中内容,以使学界受众能够传播理解。熊十力指导钱学熙将《新唯识论》改写为语体文本。1939年冬,韩裕文接替钱学熙工作,继续《新唯识论》改写工作。经黄艮庸核校,《新唯识论》语体本上卷成稿。
熊十力在治学思辨培养上,对韩裕文甚为苛责,每日方至饥肠辘辘,才可释卷。然生计日艰,终日难得饱食,韩裕文被迫离开熊十力而为稻粱谋。1942年,贺麟组织成立“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编译会暂设在西南联大,韩裕文、樊星南、曹仁和、顾寿观、陈修斋等青年学者参与其中,据陈修斋回忆,编译委员会“人员薪资由教育部通过联大(后为北大)代发,研究编译员大都借住在联大的教职员宿舍里,一切待遇也大体与联大相应的教师一样”(陈修斋《哲学生涯杂忆》)。在编译会工作期间,韩裕文与任继愈等合作译介B·Rand选编《西洋伦理学名著选辑》;抗战胜利后,韩裕文相继任教于西华大学、浙江大学。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韩裕文连续在《申报》发表《鲍桑克底美学述要之一:审美经验的特性》《审美经验里的心与情:鲍桑克底美学述要之二》《审美底对象:鲍桑克底美学述要之三》《对象的形式与实质:鲍桑克底美学述要之四》《审美之对象与情感之合一:鲍桑克底美学述要之五》《鲍桑克论身心关系》等多篇文章,对英国学者鲍桑克(又译:鲍桑葵)的美学思想予以翔实介绍。韩裕文也曾翻译其他学者的作品,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将他的作品整理出来。
1948年夏,韩裕文由哲学编译会帮助以自费公助方式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大学研究部,继续研究哲学。1955年12月18日,韩裕文因患肺癌,在美病逝。唐君毅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美某君信,谓韩裕文已逝世,念彼最后一函谓彼不至死,因其尚未对社会他人恩惠加以报答。彼十六年来一直在孤独中生活,在友人中彼对我为最信赖者,闻其噩耗甚为悲痛。”(唐君毅《唐君毅全集:日记》)
唐君毅致函徐复观、牟宗三,劝诸人撰作悼念文字,缅怀韩裕文其人其事。韩裕文丧葬诸事,由严倚云料理,碑文由胡适撰写。身旁友人清检其遗稿,有英文写作的休谟哲学著作一部,论文若干篇,亦存留日记及写给友朋信札若干。
韩裕文旅居异国,精神上倍感苦闷,常生孤独寂寞之感。据唐君毅回忆,二人信札往复所谈内容多为哲学问题,韩裕文倾慕古希腊哲学面对自然、人生问题所做的经典思考,对此方面颇下功夫,阅读了大量原典。韩裕文还自修德语,学习当时流行起来的语义学,对英美经验主义哲学持保留态度,认为哲学研究应关注现实人生,面对人类生活,以内在而超越的心态去进行思考。作为知己,唐君毅评价韩裕文“是一沉潜笃实而属于内倾型的人”(《敬悼念亡友韩裕文先生》),很少发表文章,读书仔细,不轻言著述,与人谈话,深自谦抑,性情敦厚,总是居于请益的地位。对于韩裕文治学思想,唐君毅在《敬悼念亡友韩裕文先生》一文中评述云:“他是一真正莫有中西古今之蔽的好学之士,以他的沉潜笃实,他应当是属于大器晚成的形态的人。”“他的思想以儒学作根柢,大约此数年中其研究学问的方向,仍初是偏在西方之正宗的理想主义传统哲学方面,由此而附及于西方之宗教思想。”
牟宗三一直寄希望于韩裕文学成归来,朝夕相聚,共同弘扬儒学。谁料韩裕文一去不返,竟成永诀,徒增凋零伤悲之感。牟宗三认为韩裕文性情狷介,少爽朗之气,胸怀稍欠豁达,为人处世上颇为拘谨,因此心底有事便放不开,长久积压,则不免心境悲郁,这也是他不得永年的重要原因。
二、问学熊十力
自1935年起,韩裕文开始求教熊十力,时间跨度达十余年之久。从《十力语要》所存留下来的札记来看,熊十力在个人日常家庭杂事、内心生活等方面,对韩裕文倾吐甚多。例如,熊十力鉴于“民国”时期教育弊于浮杂而成见太深,故深觉闭门著书于事无补,决定以全副精力讲学授徒,以维系儒学之道不坠,宣扬先哲之遗训。要实现讲学之愿,熊十力去函韩裕文,告知他有成立一哲学研究所的打算,“冀聚若干有志士得与吾共朝夕,专而不纷,期以数年,精神通,思理达,夫而后此学此道不失其真。斯所以上对千圣百王,下为无量人群广植善种子,则吾之心尽,而天地生民其亦有所与立、有所与托矣”(《十力语要》)。熊氏深知自己性情孤僻,不擅长人际交往,不想势利为之,仰人鼻息,面对哲学所经费之筹措,一筹莫展。这些内情都是不为外人所能道及的肺腑之言,而熊氏去函韩裕文,言其苦闷心曲,可见师徒之间情谊之深。
熊十力一再嘱咐韩裕文对其《新唯识论》等著述要勤加阅读体味,对韩裕文在为学取径方面影响至深。在为学取径方面,熊十力告诫韩裕文说:“学问之道,于此深造自得,于彼亦可深研;于此粗浮作解,于彼亦是粗浮。粗浮者,即一无所知、一无所得也。汝曹返诸良心,曾受何种严格训练免于粗浮,而遽欲违吾以自立乎?汝非天才也,吾望之者,取其笃实也。”(《十力语要》)
熊氏之论,其精髓在“笃实”二字,希望韩裕文忌粗浮,以平实心面对学问,如此方可有所自得。熊氏进一步强调,治学之要,应以思考开始,然运思过程,非漫无边际的想入非非,需要通过大量读书。然读书,需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切忌浮泛涉猎。对于读书过程中所存疑惑,时存心头,反复思考,方可面对万事万物之幽深而产生问题意识,以问题意识为凭借,分析其所立所成之因果,思其所然与所以然,则可有自得之见。然“心之官则思,系于日常实际生活者,情识也,非心也。情识之役于境,是系缚也,不能思也。离系而后能见心。心不为情识所障,而后无不睿也”(《十力语要》)。因此,思考之得要证得本心,以见其理所在。所谓证者,即本体呈现也。学至于证,则本心自明,真理可得。
在辨析儒、佛之异时,熊十力对韩裕文教益颇多。熊十力认为,儒、佛二家之学,推究其本源处,皆归于明心见性,“诚能见自本性,则日用间恒有主宰,不随境转,此则儒佛所大同而不能或异者也”(《十力语要》)。从体用不二的立场看,儒学即用显体,不是滞于用而不见体。若只谈用,则儒学与俗学有何分别?佛家谈体,是不生不灭、不动不变,不免有将体用截成二片之嫌。
对于宋明理学之问题,熊十力亦对韩裕文时时点拨。例如,韩裕文问熊十力,“阳明教学者只求明体而不求达用,其末流遂陷于罪恶,何耶?”(《十力语要》)熊十力认为,良知乃为心之本体,是一切知识之源,但若内守而不推致此良知于事物上去,即缺乏辨物明理的知识。而此一念之间,未经磨炼亦靠不住,乃任意见而起弊,亦即以意见为天理。在教韩裕文宋明理学本体论知识时,熊十力认为理学家以静属体,以动属用,此问题值得一辨。熊氏辨析说,体自是静的,但也不能说它是凝固不动的物事。如果无动,如何显现为大用流行。用是动的,但也不能是嚣然浮动的物事。如此,则体不能成用之体,如何讲得通?最恰切的理解是:“吾人于用上而识其本体,则知用之相虽是变动不居,而用之体毕竟真常寂静。所以就用上说虽是动的,而确是即动即静的。验之吾心,当动应万端时,原自湛然虚静,此理岂待外求?”(《十力语要》)
对于20世纪上半叶儒学史研究而言,其所依托的科举制度被停废后,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被打破以来,儒学被文史哲所划分的学科门类分割,衍生出不同的专史方向。后来者治儒学史者,在聚焦主流学者学术思想及其经典文本的深究方面,取得成果累累,然多集中在某个断代或某一固定典籍之中,以作为其毕生努力方向,难窥经学之全貌。尤其对儒学源流、损益演变之迹,难以整体贯通深入,所得流于浮泛者,比比皆是。除关注名入史册的儒者外,对于隐入历史尘埃中的非主流学者,学界无论在文献整理,还是学术思想阐释上,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亦有进一步思索的空间。
像韩裕文这样的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的儒学史系谱中扮演的是一位居学术边缘的角色,其人其学,隐没不彰。若我们转换研究视角,眼光向下,将韩裕文视作中下层边缘儒家学者群体的典型代表,专门关注这类学者群体文献的搜集、整理及研究,思索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群体哲思成就,则无疑会扩充20世纪儒学史研究视域。以韩裕文为媒介,从学术理路层面来看,我们不仅要留意剖析这类群体学者的思想内源,还要关注他们思考的儒学议题、学术交往等。尤其是这类学者群体的时代思考,业已渗入历史思想的潜流,被后来书写机制所遮蔽,资料分散难寻,生平踪迹难觅,如何返回当时思想语境,思考他们的思虑关怀、人生境遇、著述心得等,似是后来者应努力的一个方向。从更为广阔的儒学学术生态环境而言,将这类学者群体置放于当时社会生活话语体系里,注意他们的思想与时代的互动,边缘与主流的交光互影,新潮与旧学的对话,中西哲思互为阐发的影响等,亦是未来可值得考察的一个学术视点。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徐复观年谱”(项目编号:23XJC720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