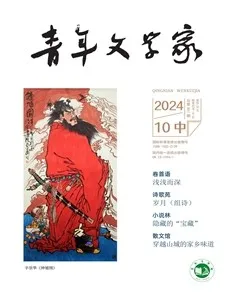那一勺油

一
一直以来,我都想就我姥爷写些什么。
他是我母亲的父亲,也是一位我并不熟知的老人。
从小到大,关于祖辈的来历,我一直被这样告知:我的祖上在清代是科举出身,在地方乡试中考中秀才,虽未谋上一官半职,成为一方的显赫门第,但经几代人的打拼,多少还是有着一路赚钱的营生,掌握着大小数余亩地的收成,算得上方圆里外的乡绅名贵。
那年,应当是我祖上家境最为殷实的一年;那年,姥爷含着金汤匙,以少爷的身份出生在偌大院落一角的厢房内。毫不夸张地说,“祖上的荫庇”这五个汉字对于我姥爷的意味,可绝非现在小说中司空见惯的文字设定可比,而是真真实实可闻、可见、可感的切身经历。可闻,是八仙桌上名贵菜肴所携的奇闻异香;可见,是服侍的丫鬟裸露臂腕处佩戴的翠绿首饰;可感,是举家上下对太姥爷—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毕恭毕敬的态度。
当然,其中的许多意味并不是一个懵懂年幼的小少爷能够解读的,是多年后姥爷一点点破译的。类似的疑惑会有很多,其中大多会在少爷被父母拉去上私塾后被逐一解开。兴许通过一两个偶然的瞬间,他会慢慢察觉自己在周遭同龄玩伴中的特殊地位,会发觉自己总是能分到更多的糖果,会理解自己为何会得到长辈更多的注视。
也有些疑惑是需要许多年后才会解开的,如家中的门槛。他想不明白自家的门槛为何要造得比旁人家中高上几分,且不说自己每每越过这道门槛时都需要旁人搀扶,家中的老仆人几次经过时险些绊倒,就连平日里总是闲庭信步的太姥爷遇了这道坎都会一改常态,在它面前劳心费神地屈膝挪步。
除去那些本就久居屋内的人外,还有许多与他同样不习惯这道门槛的人。例如,不时来的长工,他们的双腿鲜有能真正跨过门槛的时候,未经主人许可便轻易踏入屋内,无疑是十分的逾矩与不敬,因此他们往往也只能战战兢兢地立足屋外等候。又如,佳节之时,从八方各处来访的众多亲朋,在这道门槛面前,他们有着同样的笨拙与迟疑,只有当太姥爷出面,略带赔罪的笑意亲自将他们迎入宅中,他们的步履才会恢复往日的自然。
后来,他明白了:主人刻意修这道不便人行的坎,对屋中所居之人而言,讲究的是“财气不外漏,煞气不内流”。对来自屋外的访客来说,这是客人在面见主人前整理仪表、修正步态的一种提醒。
可天意注定难从人愿,坚挺了不知道多少年头儿的门槛终究还是被外人踏平了,那屋内秘藏严守的财气也随之而泄。那年的姥爷未满十岁,刚上了几年私塾,才刚刚熟悉跨越这道门槛的节奏。
踏平这门槛不是一队人,而是一群人。他们不懂礼数,尚未整理仪容和仪态便急匆匆地闯了进来。领头的人亲自从宅内拽出早已惊慌失措的太姥爷,他拉着太姥爷转向院落外围看热闹的邻里街坊,看向人群,高声宣读着太姥爷的罪状。宅内人只是低头看着,不敢多言语,即便有人心存不甘,想辩解几句,尚未出口的话语也会被这些人愤怒的目光震慑回去。
这群人中的其他人也没闲着,他们找村民借来了柴刀、木锯,就着宅中的砥石磨起刀来。在旁人看来,他们磨刀的动作兴许会比平日里更为严肃、慎重。历经百余年的门槛本就被岁月的酸雨腐蚀着根基,面对这饱含爱国情绪的刀刃又如何能够抵挡?所以当对方正义地举刀挥下,封建的腐朽门槛便也识相地被连根拔起。看似牢固的门槛如此轻易地被砍下,可能会在挥刀者的心底激起微小的惊异,可尚不待抚平心底这一缕无关紧要的涟漪,他便禁不住周围同伴的催促,继续帮忙搬弄那一屋子的家什了。
姥爷看着这一切,自那天后,少年便不再为这道难跨的门槛而苦恼。
坦言之,我很少在这样的叙述中听过关于太姥爷此时的描述,面对如此家庭变故,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可以做到无动于衷,即便是不得已之下的忍气吞声,一个人多少还是会有所表露才是。
但没有,我全然无法知晓太姥爷是以何等的姿态承受下这一切。可能在那一刻,他的心便已经死去,彻底冷漠。他的身躯便枯死在左右架着他的臂弯中,无法动弹。也有可能当场他便发了狂,全然抛弃了读书人的文雅,直至被众人团团制住,刀口架到脖颈儿。
那状况,其时必是相当惨烈,只是旁观的少年事后记不清了,这也难怪,毕竟与之相比,少年深刻记忆的,是几天后发生的那件事。
几天后,是每家每户分粮的日子。按照新规,公共资源不多不少都得按需分配。以往遇到这种事情,都是家中佣人前来代领。可这时已经没有家了,积蓄下的粮食也均被收缴,充当公用。前天夜里,原来的佣人已作鸟兽散,不知踪迹。没办法,太姥爷只得顶着众多乡亲的冷眼,亲自拖着一家老小来到领油处门口。今日,这里发放的是一个月的油量。太姥爷报上了自己的需求,耐心地等着。
掌勺儿的小伙儿终于清点完人数,拿出一个喝汤用的勺子,从装油的大锅中挖了一勺,随后连油带勺递给太姥爷。太姥爷接过这一勺后,继续等着,等着下一勺。他看向对方,却发现对方也在等着,等着他离开。他明白了,一勺,一家六口,一个月的量。他笑了,平日里他所享用的菜肴的油,每一道都不是这一勺可以与之相比的。
没人知道太姥爷当时想了些什么。
当着全家人的面,于全村人的目光中,太姥爷仰起头,像饮烈酒那般将这勺油一饮而尽。这勺油被吸收得是那般干净,以至于他连一滴都没给他身后的家人们留下。随后,太姥爷朝着村口走了出去。没人敢在这时候拦着他。他的身影越发遥远,消失在了阳光与众人视线交汇处。
姥爷伫立原地,默默地看着太姥爷出走的背影,从此,少年再没见过他的父亲。
二
经由母亲转述这段经历时,语调是那般平静。就像她的父亲一次次给她讲述这段经历那般,母亲也一次次不厌其烦向我讲述这段过往。从这样的叙述中,我难以听出那种名为“怨恨”的情绪。同样,时隔如此久远,我也很难从今日的姥爷身上挖掘出名为“少爷”的蛛丝马迹。
偶尔,我母亲和她的姊妹想起姥爷描述中的那曾经殷实的家底,她们会想,那些人来得再怎么突然,也不会连一点儿疏漏都不留下。人心都是肉长的,肉长的人心会强挤出那么些许空间,给深处的贪欲留下点位置。即便在那个夜晚,这点位置也许会因为众人的注视而变得分外狭小,一件贵重的首饰或许容纳不下,但几件日用的朴素碟器多少还是放得下的。说不准就有几件这样的瓷器被姥爷继承保留至今,说不准这几件此刻便静躺在姥爷独居的老家中,普通的瓷碗碟器放在今日,说不准就是某样文物,说不准便是价值不菲的古董名器。
说不准,是托词。
靠着内心对幸运的幻想,她们以此为逻辑得出了这个结论,即使她们也知道幻想破灭也会是一种不幸。
她们将这样的幻想扔给了姥爷,他花了好些时间方才理解女儿们的心思。就如提问那般,他的答复也同时裹挟了幸运与不幸。幸运的是,这样的物件还是留下了几件;不幸的是,就在两年前它们均已经被买走。
女儿们仍未放弃,连连出声追问买家的来历。
可那人就连姥爷也不认识。只知道那人来时,对姥爷极为恭敬,几句客套,便与姥爷热情攀谈起来,主动探问起我们家的历史。姥爷当时一人在家,见有人能如此有兴致与他聊天儿,自是欣喜得很,以至于对来者的话术、用心均毫无防备。此后的事情不必细说,不到半晌,那些流传下来的瓷碗碟器便以一个极低的价格落入外人之手。后来同村的人问起来,才知道这人在每家每户都问了相似的问题,在附近逗留了几日后,便了无踪迹、再难寻觅。
这事近来我才听闻,我没有从母亲的言语中听出太多责怪,有的只是叹惋与感慨—父亲实在是老了、不中用了,可怜父亲老实、善良,又怎能禁得住一个专门投机倒把的游商闲贩的几句说道?
就这样,连那个传闻中见证我家族历史的最后一点儿痕迹也消失殆尽了。
三
回到现在,当我想着前人往事之时,我正坐在驶往老家的车内。近年来,大多数时间姥爷都是独居乡下。因为多方面缘故,我已有数年都没再见到过他。出于这一考虑,父母便心血来潮,计划着一次短访。对此我并无异议,毕竟那个需要开车的人并不是我,我只要在车上待着就好。
那年的姥爷没上完私塾,后来的公立学堂自然不会留给他位置,到底还是识不得字。原本联系他和文字的,是我那念完了中学的姥姥,可自多年前姥姥因病去世后,便也再没人能帮他读书看报了。
姥姥去世得早,在她最小的女儿,也便是我的母亲成人之前,她便已然离世。自出生起,我从未见过我的姥姥。我对她所有的了解,都来自母亲转述的久远记忆。
在母亲的记忆中,与硬朗的姥爷不同,姥姥是柔软的。她的心是柔软的,以至于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位小学教师可以轻易放下村中人的闲言碎语,悄悄掩藏心中的革命激情,与我姥爷这么一位封建落后子弟成婚;她的言语是柔软的,柔软到她吐露的每一个字句都化作最为清澈的河渠,浸入子女心田的土壤深处,以至于虽为孙辈的我至今仍能听闻前者的诸多话语;她的身体是柔软的,这样柔软的身躯终究还是扛不住残酷生活的重压,垮了下去,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双腿渐渐失去知觉,她是靠着两条板凳方才勉力支撑。
姥姥走后,姥爷便是家中唯一的顶梁柱。好在他个头儿很高,一米八余QRQoQyM1zD8fWjmqzR4+oCVtmD/ovGVS+NXzkWhvzxE=,硬朗的身子经得起岁月的折腾,数十年的农务都没能压弯他的脊背。便是靠着这样的身躯,他将四个子女送出了这座不起眼的村落,送出了这偌大世界的渺小一隅,送出了这口偏僻孤陋的里弄天井。
和大多数子女一样,成家立业后,母亲和她的姊妹也希望能将她们的父亲接到城中居住,如今还有什么做农活儿的必要呢?姥爷吃了一生的苦,受了一辈子的辛劳,年事渐高,是该颐养天年,好好休息了。
但在乡下住惯了的姥爷并不理解,只是答应试试。只是每次尝试要不了一阵,他便急匆匆地逃回乡下。这倒不是因为被城市里什么骇人听闻的见闻所惊吓,按他的话说,他没法儿理解城市里的一切,这种生活实在无趣得很。
姥爷不会用电视,不熟悉智能手机,也跟不上广场上那些年纪相仿老人跳着舞的队伍。来到城市居住后的每天,他唯一可做的事便是顺着楼宇间错综的街道来回散着步。因为担心会记不得回时的路,他不敢走太远,便绕着住处兜着圈儿,绕完一环绕二环,绕完二环绕三环,向外延伸,直至这道痕迹的头尾恰好形成一个完整年轮时,他便也厌倦了这样的日子,要求回乡下去。
女儿们拗不过父亲的坚持,只好作罢。若当旁人问起,她们也只能略带无奈地感慨—父亲这是希望回乡下享清福啊。
“享清福”是中国自古流传的一句老话,经常被很多人提及,但若问什么是清福?清福有何可享?却鲜有人能给出具体的解答,一直以来,我也只能暗自琢磨。
我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中,以至于窗外记忆中的乡村蜃景越发接近,我却未能及时察觉。
四
母亲唤我下车。
时值三伏正午,酷暑难当,踏上老家门口碎石铺就的小路,迎面而来的热浪直教人睁不开眼,心生怯意。
不远处,知晓我们即将前来,姥爷便早在屋檐下坐着,在残存的阴影中躲避烈日的炙烤。
见到我们,他微微起身,向我们打着招呼。
父亲提着来时路上购买的日用品,一件件运入屋内,母亲则像是平日电话里那般,和姥爷长一句短一句拉着家常。
我们一同走入主屋内。
一见之下,我深为这个房间的逼仄和简陋而吃惊。这倒不是因为房间原本的狭小,仔细想来,房间本身并不算小,倒不如说是被其中摆放的诸多物件活生生给挤成这般大小的。旧时梳妆台和木制长条桌贴在房间角落,其上横七竖八地叠放着长短不一的板凳、座椅,满布灰尘。装有农具的布袋敞着口倒在桌下,如喝醉了一般耷拉散落在地面上,与其接壤的是几个撕去封皮的塑料水瓶。类似的锅碗瓢盆,以及其他零散物件则以微妙的弧度倚靠墙体,像初春时老宅向阳处生长的藤蔓,爬满了整片墙壁。
除却大门一侧,房间没有其他窗户,使人联想到囚房独有的晦暗、窒息。三十余平方米空间大气层传来的无形压力,像一块巨石横亘心头,叫人再难承受。
走出屋外,我望着眼前的景象,望着这栋房屋与他周围的地貌,望着它荒凉的垣墙、空洞眼窝般的窗户、气味难闻的成排芦苇,那周围几棵腐烂发白的枯树,连灵魂也感到无比苦闷。正对的田埂多年前业已荒废,无人修整,杂草丛生,排水沟内残余着半凝固的泥水。
此刻,世俗的情感已无法表达内心的哀愁,唯有瘾君子梦醒时分的惆怅方才与之作比。
不,不是这样的,回过神来,我怎能这般描述姥爷的居处?只怪那天太过沤人的闷热,我这良心怕是随着头脑一同发了昏。只有内心阴暗的无知宵小才会见到这般光景。
关于此地,我想起另一种写法—
家道中落后,姥爷便一直生活在这间宅屋内。对于这座老宅究竟是由何人出资而建,我无从得知。直至现在,那座老宅依旧保持着近半个世纪前刚刚被建成时的模样,似乎岁月从未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宅中居住的人数一直在变化着。在最为热闹的那段时间里,这间小屋或许会因为容纳了一家六口而略微拥挤,不足十瓦的灯光从简陋的矮窗处溢出,稍显昏暗,带着几分世俗却又简单的温暖气息。
门口正对的几亩田地是太姥爷留给后人所剩无几的遗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交到了姥爷的手上。在该上学读书的年纪,生活交予姥爷的便是这样一册无字书。无字书的书页是如此坚硬、粗粝,寻常的笔尖无法在其上落笔,但姥爷很快便明白了这本书的写法。
姥爷原是识不得字,也念不得书的,但这本书他一写便是数十年,被无数次耕种的土壤,形同开卷的泛黄书页。蘸着浓稠的泥水,一笔一画,姥爷书写得很是认真规矩,这片土地也没有辜负他的努力。作为回报,他摆脱了禁锢他的身份,换来的是一介农民的平凡。
如今,姥爷已经不再书写这本无字书,但有时他依然会到田间走走。
此时已是深秋,远近几亩的田埂沉淀着昨夜的雨水,每一片小小的水面上倒映着墨色天空,仿佛棱角分明的黑白照片,凝结着尘封的记忆。
不远处伫立着一座窄桥,桥头处依稀可见粉白色的棋盘涂鸦,借着放学后、归家前的一段短暂闲暇,年少的母亲与她的姊妹时常在此玩耍。偶尔,孩子们会在玩耍中忘却了时间,家中做饭等候的姥爷发觉迟迟不见人影,便遣姥姥顺路寻找。在渐晚的夕照中,声声呼唤在昏黄的暮色里回荡,远了,又近了,似乎从另一个世界悠扬传来。
桥下淌着一条浅溪。在溪水尚且清澈的那段时光里,时常能从中窥见鱼虾的踪迹,若是好运的时节,甚至能从水流中找到几只来不及躲藏的螃蟹的身影。孩子们喜欢到溪畔找寻这些小生物,偶有幸运的时候,他们来不及穿鞋,便赤着脚湿漉漉地赶回家,向父母展示着他劳动得来的战利品。随后的傍晚,餐桌上便会肉眼可见得丰盛几分。
但这一切都是很久前的事了。
回想起刚刚宅屋内的场景:早就无人使用的旧时梳妆台、过去锅灶台时代特制的铁锅、满布灰尘的相框、生了锈的农具—这些物件便是令房间显得格外狭小的罪魁祸首,但这些物件也是姥爷舍不得丢弃的。
我想,在姥爷眼里,这间屋子一定也同样狭小、拥挤,但不是因为这些事物本身,而是别的什么……或许,这也是姥爷至今仍独自留在乡下的原因。
话休烦絮,言已至此,即使是世间最为驽钝之人也理应明白“清福”的含义。
因此,我转身回到屋内。
五
姥爷不善言辞,他很少主动说些什么。
乍看之下,屋内似乎是姥爷正和我的父母聊着天儿。但只需稍加细听便会发现,大部分的话题和提问都是由我的父母抛出,姥爷总是略显笨拙地接过话茬儿,若遇上不知如何回复的句子,他便哑声微笑稍作掩饰。
出于礼节,我并未如往日一样拿出手机顾自埋首,而是坐下默默听着身边人的谈话。
谈话的内容都很简单、平常,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单调,无非是“最近身体状况如何”“邻里街坊又有哪些新逸旧闻”“家中姊妹近来过得怎么样”之类的话题—都是些我插不上嘴的话题。
这时,姥爷缓缓起身,像许多迎接远客的主人那般替众人倾倒茶水。原本绵延在屋子上空的谈话声也因此短暂停歇,取而代之的是凝结成块状的寂静。
我不失礼貌地笑着,接过姥爷端来的茶水。但随之我也隐隐察觉,空气中一种莫名的空虚感正随之袭来。这份感觉原本便一直存在,此时更是被短暂的沉默进一步放大,生出几分坐立难安的焦灼。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呢?我还需要说些什么呢?虽然常从他人口中听说与姥爷相关的事,可我已记不清上一次与姥爷的交谈是什么时候。眼前的老人是如此熟悉,却又无比陌生。
房间中的老人与我便形同路边随处可见的木桩与石子,偶尔会有视线的交汇、停留,却鲜有言语上的交流,仿佛在两者之间,已然有着一道如马里亚纳海沟一般的深邃天堑。
常常在饭桌上,我见过那些不那么沉默寡言的长辈,他们往往通晓人情世故,不待你先开口,便会熟稔地抛来各式各样的疑问与客套。即使有时很难分辨其中是否蕴含着真正的热情,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年龄悬殊的两代人之间一种较为普遍的交流方式。可姥爷毕竟不属于前者,我又怎能进一步奢望?也许谈话应该由我来开这个头,可又该从何聊起呢?
或许,我可以问起那个遥远的祖辈的故事,故事里那位太姥爷后来是否真就此一去不返,还是曾一度回去探望当年被抛弃的妻女,留下无尽的愧疚与悔恨;或许,我可以谈起我那素未谋面的姥姥,谈起耳聪目明的她所犯下的那个美丽错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与他是如何相识、相爱,最后又是如何相惜、相别;或许,我可以询问老人逝去的青春,在与我相仿的年纪,曾经的少年,在夜里怎样酣然入眠,又做着怎样斑斓的梦,数年后又是如何褪去这层稚气……
在老人所写的无字书上,一定会有盘桓心中的这些疑问的所有注释,所有解答。无穷的可能正轻叩我的心门,但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只是在等着。
我等着言语的声浪渐趋平稳,等着杯中的茶水被一点点饮尽,等着阳光自门外的树梢滑落,等着离开的念想攀上父母的心头,等着需要我挥手作别的时刻来临。
终于,我跟着父母上了车,车内的空气中还残留着几分炙热。
窗外,老人仍在来时的那片阴影处站着,目送我们离开。
这时,我才留意到,老人的眼神并不似他本人那般沉默寡言。
后视镜里,老人的身影越来越小。
在一片似水的沉寂中,我们驶向远方离去,使人想起黄昏时分,趁着暮色归家的渔民。
六
这样的宁静,使我反复回想刚刚别离的场景,不断咂摸礼貌的用意。
这样的宁静,也使我回想起开头处母亲给我不断讲述的那个故事。
多年来,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太过诡谲,也太过离奇,它有着小说似的戏剧感,却很难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毕竟这故事的主人公并非余华笔下虚构的福贵,而是与我血脉相承,并存活于世的太姥爷。
太姥爷的不辞而别,抛妻弃子,杳无音信,更是让人很难想象这一系列行为竟是出自一位秀才的手笔。这段故事,若是只有自家人知晓还好说,要是让旁人听闻,只怕是要落得外人笑话,不仅损害了家族的声誉,也有辱先祖的书香门第。
这么想来,事态便严肃许多,我自然不敢怠慢。即便是此刻,我也可以借想象为墨,以记忆为宣,将这个故事稍加润色、修改,如此一来,他日旁人问起,也算有了应对之策。
在我的想象中,太姥爷毕竟是秀才之后,是那样的礼貌文雅、知书达理,直至领油的那天,他也没能忘了夫子遗训、前人教诲。
报上需求后,太姥爷抬过头,认出给他添油的掌勺儿,那人不久前还在他手下接过不少短工。那人几次家中有急,还是他亲自准的假。
望向对方,太姥爷奉上一个礼貌、客气的笑,这笑放在往日是不多见的,此时更是多添了几分谦卑,甚或谄媚的意味。他希望对方能读懂他的意思:念在过往的情分上,多称给他一些。可他没能捕捉到对方的眼神,对方并不正眼瞧这位曾经的熟人,只是斜眼看着他。
那人掌勺儿的手很是稳当,太姥爷想,做过农活儿的手都理应如此稳当。
很快,太姥爷便明白昔日的人情到底用在了何处。这天稍晚些时候,他清点着这一天所领的粮食,才发现除了一开始所领的油外,其余粮食无一例外都缺了斤两。他知道,斤两的缺少并不是因为称量它们的人无意间的失误。这是讨债,这是人民在向他讨着他昔日欠下的债。他前半生是如何奢华度过的,后半生便要如何尽数奉还。当时他享了一日的福,现在便要多受两日的苦。这多出的一日,便是债务的利息,便是他必须fwik+tnpf2fp6PYDqJGbcU4e1jSTA8GKv5aQ5QZT/dQ=偿还的罪孽的一部分。如今,他所欠的债,哪怕用尽他的余生去偿还,怕是也还不清。他嘲笑起自己的天真,竟然还指望着几个谄媚的赔笑、几分昔日的人情便能偿还债务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些赔笑、人情纵使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借据上赤字的一个零头。自己是如此不知足,以至于已经到了如此田地,还不能认清现实,还抱有这般天真的念想。
太姥爷心里清楚,自己那天能够侥幸活下来,已是三生修来的福分。隔壁村的老刘,平日里对手下的长工刻薄至极,那天便被围观的人殴打,出来时已经全无人形。几个月前还一起打过牌的老赵,一天夜里带着相濡以沫的妻子上了吊……
于是,太姥爷想到逃离。这是一个同样静谧的夜晚,寻着四下无人,他带着几近背德的罪恶感,背负行囊,屏息而出,悄无踪迹。
寻出几步路远。
沿途所见的,一定是同样的风景;心中所持的,必定是相同的心安理得。即便这只是想象中的太姥爷,此刻,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能读懂他的心境。
晚风中,久远的诗句缥缈而至—
“我如何能悠然离去,不觉哀伤?不,作别此城,我的心灵必有伤创。”
太姥爷适才饮下那半碗浊油,油顺着喉管滑入胃囊,厚重的油腻带着刺骨的冰冷,在所经之处留下了永久的灼伤。他察觉自己的胃剧烈地翻腾、扭曲,紧随而来的是激烈的干呕。
耳畔的风声呼啸而过,这个世界也在翻腾,在天地间一片齐整的黑暗中,他是其中难以容纳的异类。
在我身后的,是那个在睡梦中安眠,不知道明日会发生什么的孩童,他的眼皮微微收拢,掩藏着那半辈子尚未消散的懵懂;在我身后的,也是那个年过耄耋,别离时总是让人难以与之对视的老人。
他们之间竟如此相似,我想。
隔绝这两者的,绝非时间上的沟壑,而是眼神中那半辈子尚未消散的清澈记忆。
七
在那次短暂的重逢之后,我心中始终萦绕着对姥爷过往生活的种种遐想。那勺油的故事,如同一道深深的烙印,刻在我的记忆里,让我对姥爷和他的家族历史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尝试从不同的渠道去了解姥爷和他的家族所经历的种种。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试图还原那个时代的风貌,同时也尝试与村中的老人们交流,希望从他们的口中获取更多关于姥爷家族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姥爷的生活远比我想象得复杂和丰富。他的坚韧和乐观,不仅仅是在面对家族衰败和个人命运多舛时的表现,更是在平凡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每当我想起姥爷在田间劳作的身影,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都让我深感敬佩。
有一天,我决定再次回到老家,与姥爷进行一次深入的交谈。这次,我不再是那个只会默默倾听的旁观者,而是带着一颗探索的心,准备与姥爷共同揭开那些尘封的记忆。
当我再次踏入那个熟悉而又略显拥挤的小屋时,姥爷正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相册,静静地翻看着。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脸上,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岁月在他脸上的痕迹,也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宁静与安详。
“姥爷,我想听听您以前的故事。”我鼓起勇气,打破了屋内的宁静。
姥爷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随即又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好啊,孩子,你想听些什么呢?”
我走到姥爷身边坐下,轻轻接过他手中的相册,翻到了其中一页:“就从这里开始吧,这张照片上的地方是哪里?”
姥爷顺着我的手指看去,眼中闪过一丝回忆的光芒:“哦,那里啊,是我们家族的老宅子。那时候,家里还算是有些家底的,只是后来……”姥爷的话音有些低沉,似乎不愿过多提及那段往事。
但我知道,这正是我想要深入了解的部分。于是,我轻轻地握住姥爷的手,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姥爷,我想知道更多关于那段日子的故事,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熬过来的。”
姥爷看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他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缓缓开口,讲述起了那段充满艰辛与困苦的日子。从他的口中,我听到了家族衰败的无奈,听到了生活的重压,也听到了他如何在逆境中坚持下来,一步步走出困境的坚韧与勇气。
听着姥爷的讲述,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动荡的年代。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身影在田间辛勤劳作,看到了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也看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那一刻,我深深地被姥爷所打动。我明白了,那一勺油不仅仅是一个家族衰败的象征,更是姥爷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的见证。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我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我都会想起姥爷的故事,想起那一勺油所承载的深意和力量。
从老家回来后,我整理了自己在姥爷那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文章。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了解姥爷和他的家族历史,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同时,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像姥爷一样,保持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