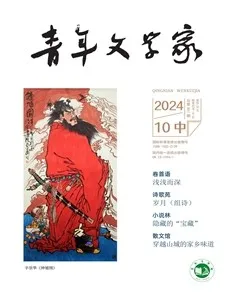青春,一直在乡下
周末。“回老家拿些米,没有米吃了。”老婆说。
我的老家在夏庄。记得第一个住宅旁边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20世纪80年代,盖的房子大多是土墙,顶缮茅草。20世纪90年代,有条件的家庭盖起砖瓦房,墙是红彤彤的砖,房顶是红彤彤的瓦,好气派。童年的我好期待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就在我家的土墙即将完成使命之际,老爸想到了比红砖更省钱的大砖。他一个人把水泥倒在模具里,待凝固后,就成了一块又一块沉重的大砖。我们家的大砖房就是这样盖起来的。大砖房虽然比之前的土墙房宽敞亮堂了不少,但比起别人家耀眼的红砖,大砖墙灰溜溜的颜色,还是印在了我的童年里。
直到今年看电影《隐入尘烟》,看到主角马有铁和曹贵英结婚后,用泥土和成一块块砖,晒干后建造房子的画面,我想到老爸当初制作大砖的情景,泪水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在农村,从无到有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过程,所以老爸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老爸打蒲包,是夏庄最快的一个,每天连编带压二十几个蒲包。他还很会用网捕鱼。小时候,夏天雨后池塘常常会满溢,老爸就会提一个网兜站在水渠里迎着水流等鱼。有时候,排在老爸前面有好几人,但是捕得最多的往往是老爸。
我在大砖房里住了二十年左右,从上学到工作。上学那会儿,我骑着自行车,从出门到小学,后来到初中,沿着曲曲折折的乡下小路,骑行大约三里的路程,可以双手不扶车把,一直骑到校园。
我工作后,第一站在新袁,买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到新袁大约二十里路程,也就二十分钟。春天采槐花、捉蝌蚪,Pcr6VO9O5IakNyTF/2wyEQ==夏天就更精彩了,我每天都要在鱼塘里泡一下,遇到庄头的一位大叔过来钓鱼,就故意打着喷喷(方言,发出声响),让他常常一无所获。有时候,我的身上会盯着一只蚂蟥,上岸后团下来,用小刀切成几块还是活的,撒上盐才能将蚂蟥置于死地。那时我还经常偷后庄的西瓜,有时脱光衣服下河后,再把身上抹上滑滑的泥水,瞄着瓜地没人,就去摘瓜。摘到后我就立即跑到河里,一边洗掉身上的泥水一边吃瓜。
偶尔我也会跟在老爸后面,在一场雨后用铁锹去挖地下的知了猴,恨不得把一夏天的蝉鸣声都挖掉。我也曾经举着裹着蜘蛛网的竹竿去粘树上的知了猴,只是所获甚少。最后悔的是我曾经和小伙伴们用腊条抽打岸边草丛里的青蛙,抓到后残忍地烤吃青蛙的大腿,真是无知幼稚。
秋天,叶落了。我经常用一根铅条去戳一片又一片的叶子,收集后放到锅门当柴火。冬天,雪下得很厚,几乎都能漫过脚上的长筒靴子。我喜欢听靴子踩在厚雪上发出的咯吱咯吱声,可惜后来雪下得越来越薄,越来越没有儿时的味道了。
最有趣的是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女孩们喜欢踢毽、跳绳,男孩们的娱乐项目就更多了,打梭、打枪、打牌,还有丢沙包、老鹰捉小鸡。记得我还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直到老妈喊吃饭了才散伙。如今,当年的小伙伴们都成家立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一起再来一次捉迷藏?总之,我做梦是经常梦到小伙伴们的。小时候,我其实也很害羞,见到小姑娘脸就不由自主地红了,有诗句为证:“年少桃花红粉姿,难藏羞涩怕人来。”
告别老宅,沿着缘庄圩到卢集的一条道路前行。这条路通到李口时,恰好是经过我家旁边的一条小路,小路需要拓宽,我家成了拆迁户。拆迁后,我家就在离家近的一块宅基地上盖了两层小楼。后来因为要盖另一块离李口街更近的宅基地,我家就把这楼房卖了。
后来的新居虽然更宽敞了一些,但因工作环境的改变,不得不重新买房,孩子们也都随着我工作的地点而改变了学校,除了逢年过节,也就很少回家了。现在想想,我的青春记忆应该都留在大砖房里了。
刚到家门口,我就看到了老爸老妈那佝偻的身影。我蓦然发觉:老爸老妈的青春,一直都在这个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