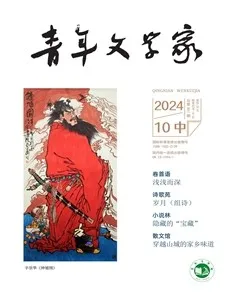哦,老屋!
这些年,回老家,到老屋坐一坐,收拾收拾,我的心才会归位。
上次倒瓦后一直没得空回去收拾,假日第三天,我就回了老家。看着土炕上父亲的棉大衣,我潸然泪下,轻轻抱起,仿佛还能嗅到父亲二十多年前的味道。我温柔地弹掉大衣上的灰尘,生怕劲儿使大了会弹疼父亲一般。破旧沙发上是姐姐包的红色金丝绒布,姐姐只比我大两岁,却懂事很多,而年轻时的我从未想过要为这个家做点什么。儿子一到老家便到处翻找,他发现了我上学时候的练习册,给我指出好几个错别字,而且指着一篇日记笑话我,说我要坚持搜集谜语,却只在日记本上集了三天再也没了。他笑话我不能坚持干一件事情,笑话我说到却做不到。
十印的大铁锅盖已掉提手,即便十几年不用,却依然那么明亮干净,依稀可见母亲当年的勤劳、洁净。三扇门的大衣橱,六十元的木头床,仍然摆头的“金龙”电风扇,“2+1”沙发,这些都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物件,现在看来却是如此老旧,却又如此富有记忆和情怀。
天井里杂草丛生,香椿树初绽新芽,摘下鲜鲜的嫩叶,一入口,浓郁的香气便蔓延开来……纯野生的蒲公英,摇曳着黄灿灿的小花,茁壮有力而又生动、空灵。
中午时分,三爹叫我过去吃饭,母亲说:“还是有家好啊。”母亲很高兴,我也高兴着母亲的高兴,感谢着三爹和三妈的招待。
午饭后继续收拾整理。母亲和先生用一下午时间将小院的杂草清理干净,我和儿子则负责室内卫生,很快就有了家的样子。
在村南不远的果园,我们家还有五间老屋。
这五间老屋,承载着父亲、母亲、姐姐和我,我们一家人的辛劳和欢乐。起初只是右边三间,有土炕,有床,有灶房,我们一家人曾生活在这里。母亲养着几十只鸡,鸡一般不怎么喂,只是吃果树上的虫子。栽种苹果,是非常劳累的,一周一次农药,冬天剪枝,春天疏花、疏果。全家人最喜欢秋天收获的季节,红彤彤的红富士挂满枝头,一家人忙碌着、快乐着……冬天,大舅和二舅会帮忙过来剪枝,那时家里穷,听母亲说有时候路费都是两个舅舅自己搭上。
二十多年前,销售渠道非常单一。二叔帮忙处理一些苹果,再将剩下的存地窖,然后赶集,或拉乡(方言,走街串巷)去卖。父亲喜欢批发,骑上“大金鹿”,带着两筐苹果去林戈庄(邻村一个比较有规模的集市)赶集。小贩喜欢我家的苹果,不用激素,吃起来香甜口感好,他们会以批发价从父亲手中购得。父亲也乐意省事,可以早点回家。母亲则喜欢零售,零售价高,能多挣几块钱,不过每次赶集都得傍晚才能回来。大姑父和小姑父开着拖拉机,拉着我们走街串巷去卖,一车苹果,还是比较好卖的。但是在丰收季节,二十多亩的果园产量非常喜人,而单一的销售途径会导致苹果积压,来年春天天气变暖,总会有不少烂掉的果子,至今,我都忘不掉父母面对一个个烂果的心疼和难过。
左边两间房是后来加盖的,用来储存农药、肥料、农作物器具。我们经营这片果园大约十年,直到父亲查出身体不适,才被迫终止……
这几间老屋在风雨洗礼中日渐衰落,窗上的玻璃被小孩子打碎了,后来母亲把门窗卸下来拿回了家。如今这里只剩空壳,远远望去,甚是荒凉。
和儿子又到果园老屋看了看,才知三爹早已将老屋修缮了一番,恢复了原先的模样。园子里有了桃树、梨树、杏树、枣树、李子树,还有了大葱、拉瓜、黄瓜,以及鱼塘……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回老家,我和儿子又有了一个好去处。
门开着,我和儿子进去坐了一会儿,感觉很温暖,心里也非常安宁。
暮霭四合,拎着大包小包,我们又要返程了。我朝着老屋挥了挥手,心中盛着满满的不舍。
哦,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