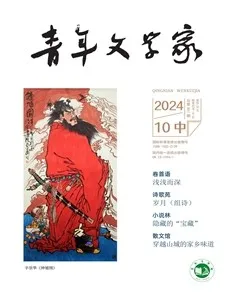姥爷的故事——关东列车
1963年,姥爷十七岁。怀里揣着两个“糠菜太多不成个儿”的窝窝头,姥爷离开了老家,去了遥远的黑龙江。
兖州火车站“是德国人盖的”,对于那个年代的姥爷来说有些新奇,不过他毕竟念过书,并没有觉得多奇怪。按理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新奇的哥特式建筑,当有不少人注目,但在那个年代里没有人顾上这些。拖家带口的,一户户,都是要去关东的人,站外挤着的,是要留在家里的人。小些的孩子被抱着,大一些的被扯着,不小心在人流里挤散了的呼喊着,嘈杂的声音伴随着站里循环播放的宣传广播。男人和女人背上都扛着大大的包裹,姥爷也不例外,里面露出叠好的被子、褥子、棉衣、棉裤,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器具—一去不知归期。人们的眼神中有光,或许里面是期望、信仰或是忧虑,但总归不是麻木,只是脸上疲惫的神色终究遮掩不住。
汹涌的人流簇拥着姥爷上了列车,最终,停在了车厢的一个角落。站在一旁的恰是一位村里相识的老太太。老太太精瘦,不高,年纪不小了,眼里却一点儿也不浑浊,在村里辈分相当高。
“老奶奶!”姥爷上前打招呼道。这位老太太也是一脸惊喜:“宝墩!”
罢了,老太太便取出了一把叉子似的旧梳子,缺了一些齿,用力地梳起头发来。旁边的篮子没有盖布,许是挤掉了,干枯的头发伴着头皮星星点点地落在了装着油条的篮子里。姥爷的眼神,时不时瞟向篮子,偶尔,不自觉地抽搐一下。过了一会儿,老太太也感觉出了一丝不对,她顺着姥爷的目光看去,落在了自己提着的篮子上,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看给孩子饿的,今天还没吃上吧?这里有几根油条,拿去吃吧,别客气。”说罢,她便从三根油条中拿出了一根向姥爷递去。姥爷连忙推辞,这根油条就像烫手的山芋。“那根油条,看着那星星点点的,自然提不起食欲。再说,那年头儿都知道有这么点吃的多不容易……”姥爷后来回忆道。
后来,两个窝窝头,虽然糠有些拉嗓子,还是在三天的旅程中先后被姥爷狼吞虎咽而下。掉在地上了一些碎糠,在拥挤的车厢内难免挨上几脚,姥爷也浑然没有嫌弃,一点点捡起,又挤过去打了免费的开水,趁热冲着咽下了肚子。
看着姥爷这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饿成这样,老太太也是可怜姥爷,把剩下的两根油条反复地递给姥爷,可姥爷最后也没有接过。
到了山海关,列车员拉响了铃声,广播道:“旅客同志们,我们的列车就要出关了……”没有听清后面还说了什么,车上立马陷入一片混乱,乘客们纷纷掏出自己的所有能加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时间有些推推搡搡。姥爷也慌忙掏出包里的棉花,一把又一把地往夹袄中塞去。直到过了好一阵,才有人反应过来:“嘿,这关外也没那么冷啊。”哄笑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开向了那片据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神奇之地、希望之地。
年轻的姥爷挤着扒到了窗边,睁大眼睛看向了外面的世界。金黄的大地,深深的垄沟,高天淡云,晃过的粗大杨树上遍布个头儿不小的鸟巢,凉爽而不寒冷的秋风吹起了刚刚变成棉袄的夹袄中的一丝丝棉絮,也吹过了姥爷年轻的脸颊。
夜幕降临,肇东要到了,姥爷要离开这辆来自故乡的列车,远乡情怯,不知将往。老太太便给姥爷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虽然裹了小脚,却没有耽误后来爬树上墙,玩得好似野孩子一般,为了打牙祭,掏老鼠洞、剥老鼠皮……种种趣事与糗事,让姥爷在欢快中渐渐忘却了担忧。
列车停在了站台上,幽暗的环境中只有几盏大灯,将辉光射进车内。老太太的眼里却透出了深深的担忧与心疼,“有事没事传个信儿,传个信儿……”说着老太太流下了眼泪,姥爷也哭了。去投奔几千里外一个不知道还在不在的亲戚,去不知道能不能进去的生产队,也不能知道家人能不能从这场困难中度过。或许,这就是那个年代老一辈的人生吧。
但,一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