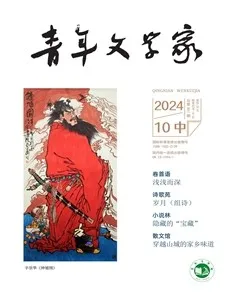故乡的冬天
我坐在26楼室温22℃的阳台上,眺望着窗外的临工大桥,思绪万千。临近年关,越来越思念故乡,那些发生在冬季里的一幕幕,又涌现在眼前。
因为大伯在东北,爷爷和父亲都在那边生活过,所以我们家搬到公路边的新家后,也像东北的父老乡亲一样,在厨房里做了一张大炕。每年冬天,我们全家都搬到大炕上,非常温暖。大炕隔壁就是灶台,一天三顿饭后,炕就热乎乎的。晚上睡觉的时候,父母再往灶膛里放一些干柴,一晚上炕都很暖和。有时候表弟会去我家做客,加上大伯家的堂弟,一个炕上六七个孩子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在冬天里,那个有炕的厨房是我们最温暖的乐园。
前段日子翻影集,看到当年三舅给我们拍的在炕上嬉闹的照片,感慨万千。20世纪80年代,鲁西南农村的冬天,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生出冻疮。先是在脸蛋儿、耳朵、双手和脚这些部位长出红肿的硬块,后来溃烂、化脓,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才会痊愈,但偶尔还是会奇痒无比。上学后的教室里,时常听到嚓嚓的声音,那是脚遇暖发痒忍不住碰课桌腿的声音。
那个年代,乡亲们在冬天是很少洗澡的,即便是镇上也没有浴池。孩子们脱了棉裤睡觉的时候,会发现膝盖和胳膊肘处都是脏东西,甚至在棉衣的缝里还会翻出几个虱子。母亲为了彻底除去这些虱子,就把我们的衣服用滚开的水烫了,女孩子的长发也给剪了,彻底清理。现在想起这些还浑身发麻。一个冬天都不洗澡,过年了应该会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吧?母亲会找来一口大缸,放在我们有炕的厨房里,缸上用大塑料袋子支起来保温,一锅一锅地不断烧开水,再倒入缸里兑好凉水。此刻,屋里已水汽弥漫。然后,一个娃一个娃轮着来,洗干净的立刻转到炕上的被窝儿里,一个冬天的泥垢清洗掉,别提有多舒服了。
儿时的我们没有什么零食,冬天更没啥吃的了,但我们自己发明了一种食物—“冻地瓜”,感觉是最美味的食物了。从地瓜窖里拉上的地瓜,洗干净,晚上放到院子里的井台上,第二天一早拿过来,就成了冻地瓜了,有时候带到学校里,在上学的路上几个小伙伴你一口我一口津津有味地吃着,别提多美了。除了冻地瓜,我们还会创造很多美味:做完饭后,地锅还有余火,大蒜、土豆、地瓜都埋在灰里,过一会儿扒出来,香气扑鼻,特别解馋。那时除了用厨房里的地炕取暖,堂屋里一般还会有煤球炉子,大伙儿有时候就找粉条去炉火上烤,吃起来也是香喷喷的。这些成了那时冬天最美味的食物。
最妙的是下一场大雪吧,整个村庄都白了。村里的孩子们都出来了,大家有的穿着草鞋,有的穿着胶鞋,草鞋里面是厚厚的麦秸,胶鞋里是母亲做的棉袜。堆雪人、打雪仗、滑雪……整个村庄都是我们的声音,整个村庄的雪也都是我们的。大家会找一处有坡度的地方,踩得结结实实,然后轮着从高处滑向低处。不大一会儿,这处斜坡就亮亮的、滑滑的,成了全村孩子的滑雪场。孩子们每天都在大人们此起彼伏的“吃饭喽,吃饭喽”的喊声中收尾回家。
故乡的冬天,老人们都很闲,他们常常穿着厚厚的棉衣蹲在墙角晒太阳,没有任何语言,只是看着过往的人们,也许,他们是在期盼着什么吧。在外忙碌了一年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了家,他们会在街边某个地方找一堆柴火点燃起来,大家一起谈谈各自的见闻,寒暄着童年的故事……
远在他乡的游子都少有团聚,家乡那个承载了我们很多回忆的小院也荒凉了。还好大弟说:“斟酌再三,我们今年都回老家过年。妈妈从妹妹家先回去收拾了,小弟也给爸爸订好了深圳飞菏泽的机票。”是的,没有父母的小院是没有生机的,没有亲人团聚的冬天是不完美的。
哦,故乡的冬天,是苦中有乐的冬天,是团聚幸福的冬天。
我抬头望了望窗外,冬日暖阳下的沂河已经开化了。我想,在故乡的母亲是不是又把小院收拾得干净温暖,等待着我们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