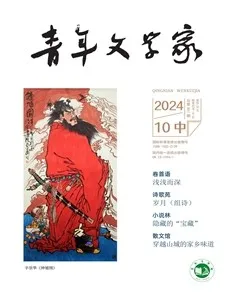故乡
故乡,是一个地理概念,是生命最初绽放的地方;故乡,也是一种浸润血液里的深情,一处灵魂的依托。离别日久,对故乡的思念,像妈妈做的苦瓜,入口甚苦,品过后却回味绵长,放不下。
我的故乡冲田村,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村子依山傍水,一条大河环绕大半个村子,一条古街穿村而过。古街上连婺源古县城清华镇,下接瓷都景德镇。我家在古街东头路边。
我家的老房子是前店后居结构。房梁、窗棂、厢房门格上都雕了花鸟虫鱼或历史人物之类的图案。20世纪80年代初,老房子被拆倒重建,再建的是普通的砖木结构房子。据说,古时冲田大路两边的人家都是店铺。我小时候看到的民房,朝大路这边都是店堂,杉木条做的门板墙,类似于今天的卷闸门。开店时,门板可以全部卸下。1949年以后,商业国有化,村民的房子成了纯粹的民居。
门口的石板路是孩子们游戏的乐园。孩子们常在路石齐整、平滑的地方,摆开阵势“拼杀”起来,或走宫,或掷包。玩得起劲时,人们挑东西路过都不让,天黑了也不回家。
故乡,不光是曾住过的老房子,也不光是儿时走过的路、爬过的山、游过的河,还有一代又一代口口相传的先贤故事和融入血液里的语言方式、行为特点。“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无奈,“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叹,想必每一个落户他乡的人都会有。
故乡的人,故乡的事,除了熟悉的亲人与邻居,还有一些虽未曾谋面,打小儿便印刻在记忆里的那些人和那些故事。小时候,在邻居家听老人讲故事,听得最多的就是齐梅麓的故事。他名扬徽州六府,从小就很聪明。齐梅麓最露脸的事有两件:一是他成为“天子门生”,曾经旧祠堂大门上悬挂有“天子门生”的匾额,据说是嘉庆皇帝所赐;二是他七岁的时候就为村子争了脸,村里大事从此由村里人做主。
相传,离冲田五里远有个村子叫大塘源,有个士绅叫李大世。他是当时附近几个村子的“大爷”,哪个村子有什么大事,得由他到场主持拍板。村里请戏班唱戏,得等他点戏,才能鸣锣开演。齐梅麓七岁这一年,冲田又请戏班唱戏。但李大世摆谱儿,迟迟不来。小齐梅麓说:“不用李大世点,我来点。”他点了一出《潘洪摘印》。李大世在半道儿的山岭上,听到冲田村里的锣鼓响,惊讶地问:“我没来,谁点的?”有人告诉他,是村里小孩儿齐梅麓点的,戏名《潘洪摘印》。李大世感叹:“雪山高不过太阳,冲田出人啦!”然后,他失落地返回大塘源。
这些故事虽没记入族谱,但村里大大小小的人,说起齐梅麓,都会说起这两个故事。在他们看来,这些故事比齐梅麓是一名科学家、诗人,更自豪。
村里有位叫齐子望的老人,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族谱。族谱详细地介绍了村子变迁,乡贤事迹,地方掌故。齐梅麓是族谱里最亮的一颗星,关于他的事迹记载最为翔实。三十年前刚参加工作时,我曾拜访过子望老人,在他家里看过族谱,读过齐梅麓写的一些策论和诗文,以及为村里修建馆阁写的记文。
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勤快的人家很快把老房子扒了,修了新房子。大路两边有不少老房子变成了新房子。现在,人们又生起思古怀旧的念想,在新农村建设中,处处融入古典元素。村东路口,矗起一座石牌坊,上刻四个大字:翀麓古街。古街两旁旧房子的拆建也被叫停。所剩不多的老房子,则成了旅游资源,常有游子和外地客人来参观。村里修建了“彦槐广场”。广场正中安放着齐梅麓雕像,周边还修建了篮球场和一应健身设施,以及一个50平方米的表演舞台。广场成了村民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与广场遥相呼应的是村北边的翀山南麓的“太平窝”,山上修建了步道、亭台楼阁,山下修建了龙泉山庄。
清明时,我回到了冲田村,看了看村子,又看了看儿时常爬的山和常游泳的河。古街的石板路已修整过,墙上还张贴着一些古语和村训,这些都让我感觉熟悉又陌生。
啊,随着时光流逝,故乡将渐渐化作一个个符号,留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