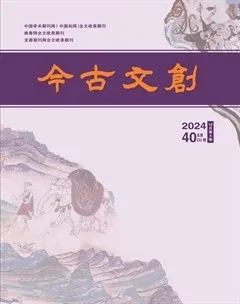镜像理论视野下《白老虎》中的人物分析
【摘要】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代表作《白老虎》获得了2008年的曼·布克奖。该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巴尔拉姆从一个底层人物通过暴力手段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故事。本文以该小说为研究对象,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巴尔拉姆周围的他者(父亲、雇主和司机朋友)对其自我建构的影响,探索他如何在周围他者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建构的过程。
【关键词】《白老虎》;镜像理论;他者;自我建构
一、《白老虎》介绍
阿拉文德·阿迪加1974年出生于印度,并在印度和澳大利亚接受教育。他曾于2000年在纽约担任金融记者,2003年回到印度后又担任《时代》杂志的记者。这段经历为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使其能够更好地思考印度社会问题,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老虎》是阿拉文德·阿迪加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即获得2008年的曼·布克奖,热度居高不下。小说讲述了一个底层阶级人士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故事。主人公巴尔拉姆·哈尔维是一个人力车夫的儿子,与他的家族一起生活在印度比哈尔邦伽雅地区的拉克斯曼加尔村。他的姓氏“哈尔维”处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底层,所以他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从事最低级的工作,做一个茶馆伙计。在此期间,他受到村庄里地主的压迫和传统习俗的束缚。为了“像一个人”一样生活,巴尔拉姆离开了他的村庄,去往一个相对现代化的城市丹巴德,成了地主家的一名司机。随后,巴尔拉姆发现,作为一个司机或仆人对他来说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他的雇主并没有给他提供真正的尊严。最终,他杀死雇主,携款逃往班加罗尔,并在班加罗尔创建了出租车公司,开始了他的企业家生涯。巴尔拉姆从茶馆伙计向企业家的转变,正是其自我建构的完成。
本文以该小说为研究对象,运用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试图分析巴尔拉姆周围的他者对其自我建构的影响,以及巴尔拉姆是如何在这些影响下进行自我建构的。
二、理论框架
如果将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及其理论装订成册,法国的雅克·拉康必将在其中占据厚重的篇章。镜像理论是拉康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拉康的理论起点。在镜像理论中,最核心的阶段便是“镜像阶段”,在这个阶段,6个月到18个月的婴儿能够识别镜子里的自身形象,形成初步的自我意识,把真实身体和镜中形象相统一,从而确立自我同一性和整体性身份认同的过程。在此之前,婴儿的各项功能(包括意识和感知能力)都还处于不够完善的状态,对周围环境没有产生感应和知觉,没有独立自我的概念。在镜像阶段,孩子第一次实现了自己身体上的自主性。
在拉康看来,“他者”在人类“自我意识”的确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自我的认同总是借助于他者,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构建的,自我即他者。”[3]43镜像阶段中提到的镜像,实际上就是想象的他者,成为婴儿创建自我意识的关键工具。当婴儿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完整影像时,他们并没有因为认出镜中的自己而停止动作,反而是在积极地迎合镜中的影像。由此可见,婴儿的自我意识尚未建立,而是将镜像误认为真实的“我”,将这一外界镜像看作是自己真实的形象。然而,镜像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婴儿期。实际上,镜像作为一种他者,纵贯着人类自我塑造的整个过程。由于自我本质上存在的内在缺失,其需要不断地从外在的他者那里获得充实和确认自己。这里的镜像,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它代表了和父母、朋友、社会的互动,以及他人的目光、认可和评价。这些因素在自我塑造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最初塑造自我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将自我以外的他者形象误认为是真正的自我,并将他者用作自我建构的基准,这正是拉康的“小他者”概念,与代表语言文化的“大他者”所对应。下面将从“小他者”出发,探析《白老虎》中主人公巴尔拉姆的成长历程和自我构建。
三、巴尔拉姆在他者影响下的自我建构
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提到,从镜像阶段开始,婴儿就开始区分“自我”和“他者”。透过镜子,婴儿意识到了“他者”的存在,进而认知“自我”的身份。“他者”所投射的注视,帮助婴儿认清了“自我”,不断地指引着“自我”的认知。在“他者”的注视下,镜像被婴儿吸收转化成为“自我”,即个体会通过“他者”来确认自己的主体身份,同时理解“自我”与“他者”间的联系,以及通过“他者”来建构“自我”。
小说《白老虎》中主人公巴尔拉姆从黑暗之地到光明之地,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旅途。从茶馆伙计到企业家,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和“他者”产生了交集。他的父亲、雇主、司机朋友等人作为“他者”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他完成了自己身份的建立,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姓名的建构
谈及自我建构,最明显的就是主人公姓名含义的变化。由于父亲的工作十分忙碌,母亲常年生病,二人均没时间给他取正式的名字。所以在他上学之前,家人随意地叫他穆纳,这个姓名没什么含义,仅仅是“小男孩”的意思,可见家人对其姓名的不重视。上学后,他的老师在登记学生姓名时,现场为他取名巴尔拉姆,此名是牧牛神克利须那最忠实伙伴的名字。有趣的是,老师的姓名正是克利须那。就此,主角的第二个姓名确立。对于这两个名字,主人公对于这两个名字均无明显的喜恶,此时其意识还未觉醒。第三个姓名是由督导为主人公取的。在一次突击教育检查时,只有主人公读出来督导在黑板上写下的四行字,并对督导随后的问题对答如流。督导夸赞他聪明,在学校难得一见,稀少程度可以和丛林中最稀有的动物白老虎相媲美。于是白老虎成为他的第三个姓名。在他理解这个姓名的含义后,表现出了明显的喜欢,而其意识也在慢慢觉醒。
前三个姓名均是他人赋予巴尔拉姆的姓名,但又有些不同。对于“穆纳”和“巴尔拉姆”,主人公无明显喜恶,但对于“白老虎”他十分喜欢,之后他也以此自称。因为其中蕴含着督导对他的高度认可,督导的评价对主人公产生了影响。
主人公第四个姓名是阿肖克·夏马。在德里谋杀雇主后,他用抢来的钱作为启动资金经营了一家出租车公司,并且采用原雇主的名字更改了姓名,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社会企业家。不同前三个姓名的被动性,第四个姓名“阿肖克·夏马”是主人公自主更改的姓名。他看到的雇主阿肖克是文明的上等人,期望成为和雇主一样的人,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以雇主的名字来建构姓名。
(二)心理的建构
1.父亲的作用
镜像阶段中,当孩子被带到镜子前时,往往可以看到镜子里投射出的旁边父母的影像。在《白老虎》中,作者很少提及母亲这一角色。主人公的母亲在他六岁时就已去世。由此可以看出,父亲的角色在巴尔拉姆的成长过程中,对他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更具有主导性。父亲很可能是巴尔拉姆自我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他者”。关于父亲的形象,巴尔拉姆在小说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父亲的脊椎好像是一节一节的麻绳,就是村里的女人们打井水用的那种。他的锁骨高高地突在外面,活像狗戴的项圈。父亲的身上疤痕累累,从胸部往下,到腰部,再到髋部,臀部,触及之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口和疤痕,就像岁月的鞭子在他身上刻画出的记号。”[1]25
此处通过人与狗的类比,论述了阶级的二元对立。可以看出,狗被视为由人类所驯化的“他者”,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而构建的奴仆。人类驯化狗的过程如同种姓制度的上层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对下层阶级的奴役。上层阶级将自我置于主体位置,为下层种姓构筑卑微的“他者”地位。不仅如此,上层阶级在宣扬自身优越性的同时,还利用婚姻和家庭等制度来内化和延续下层阶级的“他者”身份,导致他们自发维护这种“平衡”,成为理想的“他者”。巴尔拉姆的父亲是种姓制度中最直接的受害者,身为社会底层,他日复一日地拉着人力车,安于现状,任劳任怨。父亲对工作负责的态度影响了巴尔拉姆,让他在谋生初期对雇主忠诚又恭敬。
虽然父亲对于工作兢兢业业,但在工作中有着自己的底线。在巴尔拉姆的记忆中,当其他人力车夫蹲在茶馆附近,以印度仆人常见的蹲姿等客时,父亲从不蹲下。他更愿意站着,不论要等多久,也不论有多累。每年的雨季,巴尔拉姆的叔叔们就拿着发黑的镰刀去乞求地主给他们分配工作。父亲本可以和他们一起去地主的田里寻求工作,但他选择不去。他在种姓制度中选择了无声地反抗。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巴尔拉姆的父亲满足于现状,但他在必要时也会与上层阶级作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潜在地影响了巴尔拉姆,使他在反抗意识觉醒后,敢于与上层阶级斗争。此外,他父亲的教导对巴尔拉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他因为害怕蜥蜴而不想去上学时,父亲与他一同去往学校,帮助他克服恐惧,并对他说:“我这一辈子都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儿子,至少有一个儿子能够活得像个人。”[1]28此番话语在巴尔拉姆的心中播下了种子。在那之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像一个人一样生活并且为之努力。
父亲的行为潜在影响了主人公的思想,巴尔拉姆反抗意识的觉醒离不开父亲。正如主人公亲口所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穷人,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正人君子。如果没有他的指引,我今天绝无可能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坐在这样的枝形吊灯下。”[1]21
2.雇主阿肖克的作用
阿肖克是拉克斯曼加尔村四大地主之一“鹳鸟”的儿子,从小被送到美国学习。在巴尔拉姆去往丹巴德谋生时,阿肖克刚从美国留学后归来,恰巧需要一名司机。经过“鹳鸟”的考验后,巴尔拉姆顺利成为阿肖克的司机。与传统的地主不同,这位受过美国教育的雇主思想先进,把巴尔拉姆看作一个“人”而非奴隶。在这样一位雇主身边工作,巴尔拉姆日益接触到了西方事物。他秘密观察阿肖克,并且将他看到的镜像内化。当他看到阿肖克穿着一件白色T恤和鞋子走进购物中心,他也模仿雇主的服装,悄悄进去体验“上等人”的世界。在巴尔拉姆看来,阿肖克代表着文明。他梦想成为阿肖克那样的人,达到被视为“人”的标准,并得到认可。他觉察到自己归属的团体是由上层阶级所构建的。在这个阶段,巴尔拉姆的意识第一次正式觉醒。
随后,阿肖克的文明表象下地主的本性使巴尔拉姆的意识进一步觉醒。后来的生活中,阿肖克逐渐偏离了巴尔拉姆理想中的“他者”,替家族贿赂高管,与巴尔拉姆所厌恶的印度上层阶级同流合污。阿肖克的妻子平姬夫人酒后驾驶撞死小孩之后,阿肖克还主张巴尔拉姆认罪。阿肖克兄弟因为巴尔拉姆向穷人施舍一卢比而一起斥责巴尔拉姆。这些事件使巴尔拉姆彻底了解这个群体的相同本质,于是对阿肖克失望,不再忠诚,开始欺骗雇主,随后他犹豫是否要杀死雇主,抢走雇主用来贿赂高管的70万卢比。当提及巴尔拉姆的婚事,阿肖克轻飘飘给出的一百卢比让巴尔拉姆彻底失望,不再犹豫,决定实施谋杀。当他决定策划谋杀时,有句话反复出现在他脑海,那就是“你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那钥匙/可那道门却始终敞开着”[1]228,在他认知到这扇门一直处于敞开的状态时,他的自我意识同时从印度下层阶级中解放出来了,摆脱了此群体的“他者”地位。
3.平姬夫人的作用
平姬夫人是阿肖克的外国妻子,同为巴尔拉姆的雇主。不同于阿肖克的混合身份,平姬代表了纯粹的西方文明,与传统的印度不相容。当阿肖克带她去故乡拉克斯曼加尔村时,她强烈表示对村庄的不喜。她喜欢后来去往的德里,因为那里非常像纽约,充满现代感。
平姬的评价对巴尔拉姆自我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巴尔拉姆在信的开头便说:“我们两个人都不怎么懂英语,但有些事却又只能用英语才说得清楚。”[1]2可见巴尔拉姆对平姬代表的西方文化十分崇拜,所以他很重视平姬对他的评价,将其内化。巴尔拉姆有嚼槟榔的习惯,所以他的牙齿很黑。平时他不以为意,但当平姬厌恶他牙齿黑时,他买来牙粉刷牙,并训练自己摆脱下层阶级嚼槟榔的嗜好。当平姬嘲笑他说错的英语单词时,他就在背后练习正确的发音。
4.“白癜风嘴唇”的作用
“白癜风嘴唇”是巴尔拉姆跟随雇主到达德里后认识的司机朋友,小说中未提及他的姓名,因其患有白癜风而有此绰号,下文以司机作为其简称。作为同样是来自黑暗之地的人,司机传授给巴尔拉姆在德里生存的技巧。他向巴尔拉姆介绍了仆人们人手一本的《谋杀周刊》——一本描写仆人杀害主人过程的杂志,该杂志带领当时忠诚的主人公进入新的领域。司机经常戏弄他的雇主,和其他司机谈论雇主的一些秘密并且嘲笑雇主;利用职务便利倒卖洋酒、高尔夫球等;利用车辆日常保养欺骗雇主以获取利益。雇主以为一切情况均在自己掌握之中,却没有意识到仆人也在欺骗他们。透过司机,巴尔拉姆看到了不是一味忠诚的主仆关系。后期,巴尔拉姆对雇主态度转变后,其主动请教司机欺骗雇主的具体方法。
但是司机的反抗仅是欺骗主人、做些小把戏等,并没有想要跨越阶级。当他看到巴尔拉姆在车里学习上层阶级专属的瑜伽时,他像是在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嘲笑他。这也是小说中提到的“鸡笼”的“魅力”。那些被驯化的人不愿看到同阶级的人超越原本的社会阶层,因此努力压制自己的同类。他们不愿意逃离“鸡笼”,更不愿意让别人逃出“鸡笼”。这也显示了像主人公这样的人的稀缺性。
四、结语
本文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出发,分析了“小他者”对主人公的影响。主人公巴尔拉姆从茶馆伙计到社会企业家,途中遇到了许多人。他们影响了主人公的自我建构,使他从印度上层阶级建造的他者群体中脱离出来,成了他心目中的“人”。从服从雇主到反抗雇主,再到成为雇主,他的自我建构在世俗意义上是成功的。然而,主人公虽然已经成长到了这一阶段,却不知道他实际上走进了一个更大的“鸡笼”。正如他的出租车公司只是一家服务于美国公司的外包公司一样,他依旧是被西方欧美世界构建成“他者”的角色,思想还没有跳脱模仿西方世界的怪圈。
参考文献:
[1]阿拉文德·阿迪加.白老虎[M].陆旦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冯美.成长中的“他者”与言说主体之间的构建关系探析——以拉康镜像理论看《我11》中主人公的自我确立[J].东南传播,2013,(08):98-100.
[3]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郭粒粒.他者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艾米丽畸形人格的拉康镜像论分析[J].文学界(理论版),2011,(11):106-107.
[5]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J].学术交流,2006,(07):24-27.
[6]毛婷玉.文明冲突下东方文明成长的“自我”与“他者”构建——以《白老虎》和《我的名字叫红》为例[J].作家天地,2022,(16):52-54.
[7]邵文硕.拉康镜像理论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构建[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03):95-97.
[8]张一兵.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0):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