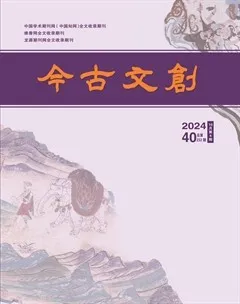虚构与真实: 《玛迪》中的文学地图想象
【摘要】梅尔维尔于1849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说《玛迪》延续了其前两部小说《泰比》和《奥穆》的叙事风格,以虚构故事贯穿小说始终,但《玛迪》有其独特之处,即在虚构叙事中嵌入真实性。小说中的维文扎岛、多米诺拉岛等地名既是梅尔维尔虚构出来的,同时也是空间信息的图示化表征。本文将基于文学地图学批评视角,重点分析小说中的维文扎岛和多米诺拉岛两处地方,以此阐释《玛迪》中的虚构与真实,探索梅尔维尔的文学地图想象。
【关键词】《玛迪》;虚构;真实;文学地图学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心理视域下20世纪中美文学战争书写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22Q151)。
《玛迪》(Mardi,A Voyage Thither)是美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于1849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尽管梅尔维尔是公认的美国经典作家,但国内外学界对其关注仍主要集中在其《白鲸》(Moby-Dick,1850)上,对其他小说的关注则较少,尤其是《玛迪》。国外评论界对该小说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将其视为《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和《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的结合体,认为这是一本“奇特的书”[1]193、“伟大的天才之作”[2]67,具有“新鲜感、独创性”[1]199,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书”[2]68。但也有将其看作是一部“荒唐的小说”,“毫无秩序或联系地混在一起”[1]227,是一部令大多数读者感到“难懂的作品”[3]2305,“它被认为不仅枯燥乏味,而且难以读懂,令大多数读者感到困惑和失望”[4]235。
从叙事手法上看,《玛迪》以冒险故事开头,但在第二部分转换成游历叙事,并通过在虚构地名串联起来的完整地图之中进行。此外,梅尔维尔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按照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讲述航行的冒险经历,但是跨越到第二部分时,却将叙事方式改变成空间叙事,即时间上相对静止,空间中无限蔓延的叙事形式,使得叙述者的冒险故事在若干个不同的空间中并行展开。可见,《玛迪》的重点并不在于第一部分以时间线性为特征的冒险故事,而在于第二部分以空间叙事为特征的游历故事。也就是说,如果对《玛迪》的阅读期待还停留在以时间为参照的海外冒险故事中,就无法真正了解并欣赏《玛迪》的独特魅力。正如西尔斯所说,“梅尔维尔在1849年出版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旅行书,它的吸引力在于他的描述和叙述能力以及他对新信息的利用。”[5]411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小说的游历叙事部分,通过文学地图学批评视角,重点对小说中的维文扎岛和多米诺拉岛两处地方进行分析,以此剖析《玛迪》中的虚构与真实,试图探索梅尔维尔的文学地图想象及其对当时世界问题和国家问题的关注、思考与批判,为深入理解这部小说提供参照。
一、文学地图学的内涵
20世纪以来GOhzexKInwEAoZBjkWhdYAObct8x4b5+gaLNC9L2glQ=,随着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文学地图学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布里斯科(J·D·Briscoe)等人合编的《英国文学导图》(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介绍了19世纪英国的伦敦、哈代的威塞克斯等地区,并收录了9幅英国不同时期的文学地图,大大加深了读者对英国文学空间分布特征的了解[6]6。20世纪中期开始,空间开始进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话语之中,弗兰克的“叙事空间”、巴赫金的“时空体”、福柯的“异度空间”、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索亚的“第三空间认识论”等相关理论都促使“文学的空间研究逐渐盛行”[8]110,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地图的文化阐释进行实质性的融合,共同催生了一种新的批评模式——文学地图研究”[10]112。郭方云曾对“文学地图学”(literary cartography)的概念作出阐释,即“特指文学地图批评图示的建构——一种利用地图学特殊的认知模型结合操作范式进行文本分析和寓意阐释的文学批评视角”[7]115。可见,文学地图学属于一种文学批评视角,是用来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的新视角,属于文学和地理学科之间的交叉地带,符合跨学科特征,既同时带有文学特点,又属于地图学或地理学的学科范畴,更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视角,通过跨学科的发展和空间研究的重新兴起,“文学地图学”或“文学地理学”成为了一种崭新的文学空间批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可以挖掘许多曾经无法在文学文本中发现的新内涵,而这些内涵很可能会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感知深度,对文学文本的流传和接受产生影响。因此,在文本分析的实践中,使用“文学地图学”的视角是十分必要的。
二、虚构的多米诺拉岛与其对真实“大英帝国”的
隐喻
如前所述,《玛迪》分为两个部分,叙述者均为“我”,亦即塔吉(Taji),但当塔吉从小说第一部分的海上冒险故事中抽离出来,进入第二部分为追寻伊拉(Yillah)而展开的游历故事时,塔吉隐退到叙述者之后,成了一个个故事的旁观者。叙事视角则变成了第一人称外视角,即申丹[9]74所指的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眼光。叙述者第一次和伊拉到达太平洋玛迪群岛的时候,他们留在了国王米狄亚(Media)的岛上,在几天的时间里,塔吉和伊拉收获了幸福。然后伊拉突然消失。因此塔吉带上国王米狄亚、诗人尤米(Yoomy),哲学家巴巴兰贾(Babbalanja)和历史学家莫希(Mohi)一起出发踏上了追寻伊拉的漫长旅程。
要理解《玛迪》之旅对小说结构的重要性,读者需要首先了解《玛迪》之旅的整体形状,它是由若干岛屿组成的,周围环绕着一个圆形的暗礁。塔吉的航行在叙述的其余部分将继续在这个圆圈内展开。正是玛迪群岛的形状让塔吉把它称为“世界中的世界”。可以说,“玛迪群岛为小说提供了第一个微观世界:岛屿周围的珊瑚礁将与叙述者在大宇宙中所旅行的赤道相对应”[10]415。塔吉等人所驾驶的三艘独木舟载着这群神奇的人踏上了玛迪群岛的大旅行,接触到了所有可能找到伊拉的岛屿。随着塔吉的游历进展,读者开始意识到玛迪群岛代表了梅尔维尔所处的整个世界及其各种面孔,而其中的多米诺拉岛(Dominora)表征了19世纪的大英帝国。
小说中的第146章主要讲述了塔吉等人在多米诺拉岛上的游历经历。塔吉等人上岛后不久就发现,多米诺拉岛的国王贝罗王(Bello)“精明过人”[11]328,偏爱扩张领土,只要发现哪里有可能存在岛屿的迹象,就“迫不及待地派遣船只,前去占领[11]328,而当的确发现了暗礁时,贝罗王会“在礁石上插上他的皇家标枪”[11]328,声明这些“领土”[11]328已归自己所有。这种强烈的征服欲和扩张欲与梅尔维尔所处时代的大英帝国十分契合。19世纪见证了英国全球殖民版图的急剧膨胀。自1801年爱尔兰并入,英国正式更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起,其对亚洲的征服步伐非但未曾停歇,反而加速推进,最终蜕变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帝国。该帝国的巅峰时期出现于19世纪初期,彼时其人口规模约达4至5亿,占据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其疆域横跨3367万平方公里,亦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因此赢得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称号。步入19世纪中叶,英国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还残酷镇压了1857至1859年间印度爆发的民族大起义,进一步巩固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此外,大英帝国的侵略触角还广泛延伸至伊朗、缅甸、南非、埃及、东非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并逐渐向南美洲渗透,最终在该地区确立了其作为最大投资国的地位。这一切的扩张,皆是在勃勃野心、奴隶劳动以及勇敢探险家的助力下实现的,使得英国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飘扬,构建起了一个横跨多个大洲的强大帝国。
因此,当读者读到贝罗王“在礁石上插上他的皇家标枪”时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疯狂的殖民行为,象征着维多利亚女王的贝罗王甚至还“对一些偏远地区国家的事务也横加干涉”[11]326,只要哪里的人民野蛮无理,难以教化,他就“直接去接管那个国家的政权”[11]326,以此来解除其政治恐慌。而海军力量最为强大的贝罗王也正象征着19世纪成为全世界头号海洋强国的英国。
不过,梅尔维尔并不只是客观正面地再现了19世纪的英国,而是通过叙述者塔吉和其四个同伴的谈话来暗讽英国的殖民和奴隶贸易行为。尽管贝罗王威风凛凛,但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驼背。对于贝罗王驼背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领土太大了,一个人统治不过来”[11]329;有的认为“遥远的殖民地不仅没有给他增加收益,反而给他带来许多麻烦”[11]329;还有人则断言,“他的国家已经强大到了他无法掌控的地步”[11]329。但不论是哪一种解释,最终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贝罗王无止境的疯狂扩张和殖民行径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成为其驼背的根源,而这种驼背的后果在另一个国家看来,代表的是其大限将至,“游戏结束”[11]330,贝罗王即将给更多优秀的人让路,而这个“人”则喻指了19世纪的新兴美国,喻指对象是维文扎岛。
三、虚构的维文扎岛与新生的美国
小说中的维文扎岛是与多米诺拉岛放在一起被描述的,而维文扎岛的重要性在小说中不可替代。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维文扎这个“强大的共和制国家”[11]238的:
“由于近来收复了大部分领土,维文萨①举国上下热情高涨……维文萨国和它的人民简直是不可征服的。
维文萨人绝不是懦夫;他们生性勇猛,永不言输,仿佛是雄狮孕育的民族。他们在歌谣中把自己描绘成玛迪岛的新兴民族,他们决心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新世界。”[11]328-329
这些描述中无不透露出维文扎对美国的喻指。首先,维文扎是一个崭新美好的世界,它“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好像朝霞满天的黎明”[11]329。塔吉甚至把维文扎比作圣·约翰②,约翰之所以被称作“爱的使徒”,是因为他讲到爱的重要性比任何其他新约作者都要多。将维文扎岛比作圣·约翰似是隐喻了美国的“天定命运论” ③,即身负重要的传道使命,撒播爱的种子。这是梅尔维尔时代的美国人在看到美国的急速发展之后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然而,梅尔维尔绝不只是歌颂赞美了新兴美国的积极一面,他还深切关注殖民时期美国大规模扩张、征战以及蓄奴的现象,并表达出其强烈的批判态度。《玛迪》中的维文扎人尽管很勇敢,但却也喜爱吹嘘,他们的士兵就像一只只“高傲好斗的公鸡”,“整日高唱他们的民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11]329。塔吉甚至认为,维文扎是可耻的,并质问道:“你们究竟勇猛在何处?难道不是从充斥蛮勇的多米诺拉岛带回来的吗?除了多米诺拉,还有哪座岛屿提供给你僵直的脊梁?最蛮勇的心脏?”[11]329“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能妄自称大”[11]329,更是对当时的“天定命运论”的无情讽刺及对美国前途的焦虑担忧。
此外,奴隶制问题也成为梅尔维尔对维文扎岛展开最直接分析的“中心问题”[12]46。当塔吉等人参观维文扎岛最南部地区时,发现了那些会让初访者感到特别反感的景象:
“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几百个戴着项圈的人正在田里劳作——这里的土壤最适合种植芋头。在他们的身旁占着一些神情冷酷的家伙,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皮鞭,不住地抽打辛勤劳作的奴隶们。血和汗混合在一起,一滴滴落进了土里。”[11]374
当巴巴兰贾问一个拿着皮鞭的家伙纳利(Nali)奴隶们是否有灵魂时,纳利回答说:“他们的祖先也许曾经有过,但是他们的灵魂已经在一代代的繁衍的过程中消失了”[11]374。而当巴巴兰贾询问一个奴隶相同的问题时,得到的回复却是“在鞭子的威胁下,我只能相信我的主人的话,我是一个畜生。但是在梦里,我把自己当作天使。我和我的孩子们受到禁锢——他们的母亲的乳汁也是苦涩的”[11]375。纳利听到巴巴兰贾和奴隶之间的对话后,异常凶狠地说:“你们妄想在这里点燃反叛之火吗?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些奴隶一旦被怂恿去争取什么自由,他们就会在可怕的复仇之火中毁灭吗?”[11]375对于纳利的这种控诉,诗人尤米则表示:“总有一天,复仇者会拔掉他们锁链上的铆钉”[11]375。
《玛迪》中对维文扎的这段对奴隶和奴隶主的描写堪称关切时事、针砭时弊、直戳要害。美国在其从殖民地到成为独立国家的300余年历程中,其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一直与免费劳动力以及成百万非洲奴隶的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1803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与法国皇帝拿破仑谈判,达成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令美国的领土面积翻了一番。而“新购的领土上,本就生活着差不多3万名奴隶,国会也驳回了在当地限制奴隶制的提案”[13]19。在19世纪中期,美国南部是“西方世界里除了巴西,古巴和波多黎各外唯一保留奴隶制的国家”[14]454。到19世纪50年代矛盾激化成为政治危机,亲蓄奴制和废奴主义情绪愈演愈烈,都固执己见。奴隶制在美国建国后不仅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废除,由于奴隶制而产生的暴乱还愈演愈烈。克拉曼[13]21就梳理了部分奴隶暴乱事件,如1800年夏天,奴隶加布里埃尔·普罗塞(Gabriel Prosser)计划在弗吉尼亚里士满领导一场奴隶暴动,致使26名黑人被判绞刑;1822年,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曾挫败过一场奴隶暴动。白人指责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自由黑人海员怂恿另一名自由黑人丹马克·维奇(Denmark Vesey)策划了一场暴动。此次事件中,35名黑人被处死。最有名的一起暴动则是发生在1831年夏天,由奴隶传教士纳特·特纳(Nat Turner)领导的美国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奴隶起义[13]26。这些真实的奴隶起义都是对虚构的维文扎中的奴隶的隐喻,暗含了奴隶主纳利所说的“复仇之火”和诗人尤米所说的“复仇者会拔掉他们锁链上的铆钉”。
此外,梅尔维尔还通过维文扎岛上的岛民对多米诺拉岛上岛民的谴责来暗讽美国人民对美国土著人的血腥屠杀。如叙述者指出,“那些指责贝罗王在政治上过于贪婪的人,其实也应该受到同样的指责”[11]326,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尽管像维文扎岛上的岛民一样将贝罗王形容成一个“贪婪的领土大盗”,但维文扎岛上的岛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维文扎岛,“那些世代以打猎为生的土著虽然尚未彻底灭绝,但也已经被驱赶到越来越偏远的西部地区”[11]326,土著民族已被逼入绝境,无路可退。这不正是美国西进运动的生动写照吗?“美国内战前,在西进运动中死于印第安部落冲突的移民不到400人,只占移民者总数的千分之一”[14]522,但与之相对的是印第安人的大批死亡。在西进运动中屠杀印第安人的罪行是罄竹难书和令人发指的。几乎每一次向西挺进的人流都踩着印第安人的白骨和血迹行进。香农(Shannon)曾指出,1637年5、6月间,在梅斯提克河畔对佩克特人的大屠杀就是殖民时期的一个典型例子。马萨诸塞殖民讨伐队指挥官约翰·安得黑尔自己供认,曾在这次讨伐中把拥有400人的印第安村寨烧杀一光,幸存者不过四五人,村寨内血流遍地,尸骨成堆,简直难以通行[15]100。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资产阶ms4Zxz/nqUn8wB9CCt6s/A==级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和屠杀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19世纪20和30年代西北地区、乔治亚和佛罗里达的讨伐,使许多印第安村落夷为平地。一个又一个的部落遭到毁灭,幸免于难的印第安人不得不重新聚集,渡过密西西比河,退居西部“印第安人之乡”的荒凉地区。当时在美国统治者当中曾经流行着这样两句穷凶极恶的口号:“野蛮人必须消灭!”“一个好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16]174可见,维文扎岛上岛民对多米诺拉岛上岛民的谴责同样也成了梅尔维尔谴责美国的理由。同样都是野蛮扩张、血腥迫害,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又有何不同呢?唯一的区别也只是英国的扩张触角延伸到海外,而美国的扩张暂时停留在北美大陆上。
四、结语
《玛迪》这部看似是一部让人毫无头绪的、令人难以理解的长篇小说,但该小说实则包含着梅尔维尔宏大的文学地图想象。梅尔维尔极尽所能将当时的世界局势和国家状况进行压缩处理后放进这部鸿篇巨制中。也许受复杂多变的叙事视角和叙述风格所限,《玛迪》在当时不被世人理解和欣赏,但通过20世纪空间转向后形成的文学地图学视角,我们可以至少在《玛迪》中发现19世纪英、美、法等当时头号强国的文学图示化表征,并通过小说中的具体描述,重新绘制出整个19世纪的文学地图,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社会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信息。
注释:
①原文为Vivenza,于建华等人译为“维文萨”,笔者在文中统一根据音译原则译为“维文扎”。
②使徒约翰(Apostle John),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在传统上认为,约翰是《约翰福音》、三封书信和《启示录》的执笔者,被认为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③“天定命运论”体现了19世纪中期美国迅速发展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和推动当时改革的完美主义理想。“天定命运论”认为,美国在包括但不限于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上拓展自己的疆土是上帝和历史赋予美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其宣扬者坚持认为美国领土的扩张不是自私自利的行为,而是把美国的自由信仰传递到新的疆域的利他举动。
参考文献:
[1]Higgins,Brian&Parker Hershel(eds.).Herman Melville:The Contemporary Review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Pollin,Burton R.Additional Unrecorded Reviews of Melville’s Books[J].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975(1):55-68.
[3]Levine,Robert S&Krupat,A(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Seven Edition,Volume B)[M].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2007.
[4]Graham,Philip.The Riddle of Melville’s ‘Mardi’ :
A Re-Interpretation[J].Texas Studies in English,1957(36):
93-99.
[5]Sears,Michael J.Herman Melville’s Mardi:The Biography of a Book[D].New York:Yale University,1947.
[6]Bulson,Eric.Novels,Maps,Modernity:The Spatial Imagination,1850-2000[M].New York:Routledge,2007.
[7]郭方云.文学地图[J].外国文学,2015,(1):111-119.
[8]郭方云.英美文学空间诗学的亮丽图景:文学地图研究[J].外国文学,2013,(6):110-117.
[9]申丹.对叙事视角分类的再认识[J].国外文学,1994,
(2):65-74.
[10]Sears,Michael J. “Melville’s ‘Mardi’” :One Book or Three?[J].Studies in the Novel,1978(4):411-419.
[11]赫尔曼·麦尔维尔.玛迪[M].于建华,继小明,仇湘云RFI44TozGXqpkNtcGkCZPg==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2]Lorant,Laurie J.Herman Melville and Race:
Themes and Imagery[D].New York University,1972.
[13]迈克尔·克拉曼.平等之路:美国走向种族平等的曲折历程[M].石雨晴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14]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Ⅱ[M].陈志杰,杨天旻,王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5]Shannon,Fred A.American Famers’ Movements[M].
New York:Van Nostrand,1957.
[16]张友伦.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J].历史研究,1984,(3):166-181.
作者简介:
王雅静,女,汉族,博士,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中美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