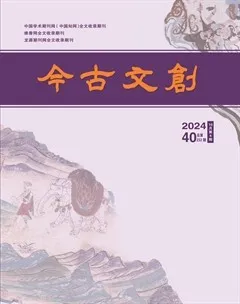古尔纳《赞美沉默》:殖民创伤与疗愈的再叙事
【摘要】《赞美沉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的代表作之一,它展示了作为黑人的无名主人公在英国与桑给巴尔两国的夹缝中痛苦挣扎而产生的精神焦虑与心理创伤。本文以小说中无名主人公的心理创伤为立足点,分析了主人公内心创伤的三个直观表现,即过度警觉、记忆侵扰、禁闭畏缩,并深入挖掘了其多重创伤成因,在家庭暴力、文化创伤、种族歧视三者的裹挟之下,主人公自卑懦弱,陷入了身份迷失的困境,同时,也探究了主人公的创伤疗愈路径,即面对真实的自我,主动与他者建立联系,建构自身的主体性。
【关键词】《赞美沉默》;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创伤;疗愈
“创伤”一词最初被作为医学术语,原意为外力给人的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后来逐渐转变成现代心理学术语。《赞美沉默》中的主人公具有多重心理创伤,其心理创伤直观表现为罹患难以根治的心脏病,童年的惨痛记忆在脑海中反复重现,于众多不同场所之下习惯性地保持沉默;其心理创伤的成因主要来自家庭、文化、种族。他被故土与英国的两个家庭皆排斥在外,他难以被任何一个种族所彻底认同,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身份的找寻,而是从故土逃离,返回英国,在失去一切之后又重新与社会上的他者建立关系,主动建构新的社会身份,以疗愈自身的心理创伤。
一、种族压迫与心理创伤
(一)过度警觉:疾病患者
朱迪思·赫尔曼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归纳为三类:“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1]这三类症状在《赞美沉默》的主人公身上均有体现。《赞美沉默》中的主人公在英国社会里始终保持着一个精神过度警觉的状态。作为一位坦桑尼亚黑人,主人公身处英国这样一个具有种族歧视的场域空间之中,他所属的种族是被西方社会他者化的种族,他清醒地看到了英国社会对他的拒绝与排斥,这使得他时刻保持着戒备的心理去反抗被排斥的痛苦与异国文化的规训。在小说中,主人公因心脏病而去求医治疗,医生却站在白人的立场对疾病加以审视,认为非裔加勒比人心脏爱出问题。疾病作为一个语言符号,常被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利用,将疾病这一被人类自觉排斥的事物与亚非地区的人民相等同,构成对亚非地区人民的污名化。主人公生存于英国这一高压环境之下,剖析了以医生为代表的英国人隐藏于语言背后的种族主义,心理创伤被反复刺激。书中写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我不是非裔加勒比人或任何类型的加勒比人,我甚至和大西洋没任何关系,但我仍然无法逃脱这些早期建构的结果。”[2]这一内心活动正揭示了主人公因备受歧视而愤怒的心理,展现了其精神高度警觉的状态,也正是由于他长期处于紧绷的精神状态之下,他所罹患的心脏病难以根治,并成了心理创伤的外在表征,不断地反复出现。
(二)记忆侵扰:童年暴力
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理论认为:“创伤患者具有重建过去的执念,童年的创伤体验会无意识地一再重演。”[3]主人公的童年充满了残缺与暴力,童年的痛苦回忆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创伤,并反复在脑海中呈现。在小说中,主人公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童年的痛苦,却选择视而不见,将痛苦与丑恶美化,并依据自身的幻想,以谎言的形式叙述给他人,这正体现出主人公对内心创伤的逃避以及对真实自我的否认。“我既没有舅舅,也没有父亲。我根据自己的继父,或多或少为爱玛创造了这两个人物。”[4]然而,虚幻的谎言也是建立于真实的记忆之上,主人公无法欺骗潜意识里的真实自我,在他所编造的故事中,舅舅哈希姆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与浓重的家庭专制主义,他是父权制度的维系者,他支配着母亲的生活,维系着家庭的运转,却没有为主人公提供任何一个建构自身家庭地位的机会。舅舅哈希姆在主人公真实的记忆中对应的是他的继父,继父的存在正是他遭受童年暴力的根源。在与主人公的母亲结婚之后,继父将主人公当作是一个边缘人一般的存在,他认为自身并没有被这一个新的家庭所接受,而是作为一个他者被排斥在外,这实质上是继父加于主人公身上的隐形暴力,构成了他童年的创伤。
(三)禁闭畏缩:保持沉默
斯皮瓦克认为,“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底层人不能说话’,只能成为沉默的他者。”[5]主人公作为一个被种族与家庭所裹挟的底层人,他在多个场域中保持沉默,这多次沉默之中彰显出一个共性,即对于长期饱受压迫的生存处境的一种麻木与适应,这是创伤心理的三大症候之一。在家庭生活中,主人公是一个沉默者。在英国的家庭里,面对来自爱玛父母的歧视与嘲讽,主人公始终保持着沉默与微笑。这种无声的沉默颇具反讽的意味,然而,这实质上也反映了黑人对于自身饱受白人欺凌的处境的一种禁闭与妥协。主人公已经习惯了黑人在英国白人眼中低下的地位,他认为只有保持沉默才能维系目前的家庭生活,他选择遮蔽自身的个性与真实,以懦弱无能的形象去应对来自外界的欺凌性攻击,但这种不断妥协的行动之中所隐藏的是不断恶化的心理创伤。在非洲的家庭里,主人公面对母亲为他张罗娶妻的事情,也选择了保持沉默。他隐瞒了自己在英国已经构建了一个家庭的行为,他恐惧非洲家庭对自己与白人组建家庭的指责。主人公在英国家庭与非洲家庭的选择中踌躇不决,因为一旦做出选择就意味着另一个家庭的失去,也意味着他的另一个身份将被彻底扼杀,而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维持现状的处理方式,这也是他面对现实处境禁闭畏缩的直观表现。
二、黑暗记忆与沉默的他者
(一)家庭之伤:在场的缺席
家庭是致使主人公身患心理创伤的根源之一。主人公既无法修复自身在童年时期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也无法在英国家庭或是非洲家庭里建构自身的身份,他长期作为一个缺席的他者而存在。主人公是一个缺失父爱的人。在主人公的童年时期,他的生父就已经是一个符号化的缺席存在,他的生父在他未出生之前因难以忍受非洲地区屈辱而无趣的生活,抛弃了家庭,偷渡欧洲。主人公对于父亲形象的认知是根据他人的只言片语构筑而成,生父的形象在他心中成了永远的不可知之物,留下了难以言喻的创伤,迫使他穷其一生都想得知生父抛弃家庭,远赴欧洲的真相。雅克·拉康认为:“主体是认同在他人身上并一开始就是在他人身上证明自己。”[6]父亲对孩子而言是一面建构自身身份的镜子,孩子将父亲误认为成是虚幻的自我形象,进而实现对自身形象的完整建构。然而,从小就缺失父亲的主人公无法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他的自我认知始终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在心理创伤的裹挟之下,他的性格变得懦弱而自卑。当继父哈希姆以支配者的姿态强行进入主人公与母亲的家庭生活,并占有了母亲之后,主人公被迫臣服于强大的父权符号压迫之下,进一步抹杀了自身的主体性,继父将他视为亲戚而非儿子一般的存在,他在家庭的地位无法得到认同,已沦为了缺席的他者。随着母亲为继父生下儿子阿克巴,主人公希望得以肯定的儿子身份被取代,他已被彻底驱逐出这一家庭,被非洲故土家庭排斥在外的经历给主人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童年创伤。
(二)文化之伤:磨难的缩影
杰弗里·亚历山大将文化创伤定义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7]在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地区撤退之后,桑给巴尔人掌权并建立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政府,但是,新政府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安宁的生活,而是以暴力武装的形式实行高压政策,以野蛮的行径贯彻专制主义,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为恐怖的回忆,构成了集体性的文化创伤。主人公从小生活在这一片充满了暴力斗争的场域之中,政权的频繁更迭与党派的血腥厮杀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他厌恶管理这片地区的新政府,但桑给巴尔也是他生存的故土,在以暴力为名的文化创伤裹挟之下,他的精神世界不断割裂,他的内心无法在这片充斥着血腥与屠杀的故土里得到片刻安宁。他的继父因涉嫌党派斗争而被新政府监禁数年,街头行走着持枪的恶棍、劫匪与强奸犯,荒淫无度的官员以权力强迫少女顺从,新政府颁布反人性的禁令,不允许任何人言说内心的怒火。混乱的政治局面与新政府对当地居民的残酷掠夺使主人公坚定了前往英国的决心,他所遭受的文化创伤已成为桑给巴尔人饱受磨难的一个缩影。然而,在主人公相隔二十年回国之后,新的掌权者依旧自私冷酷,只着眼于争权夺利,罔顾桑给巴尔百姓的福祉。政府的高层官员身处宽敞的办公室,享受着高物质水平的生活,对民众的粮食短缺、居住环境恶劣等生存困境熟视无睹,主人公对此充满了愤怒与憎恶,他洞悉了新政府的伪善与丑恶,难以整合内心的文化创伤,无法屈从于这一类伪善政府的奴役,最终决定重返英国。
(三)种族之伤:迷失的他者
“后殖民时代,非洲人与殖民者在碰撞中遭受的社会和心理伤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流散者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8]主人公是一个种族身份的迷失者。他既无法抗拒英国白人文化的诱惑,又不能割舍自身作为桑给巴尔人的黑种人身份。身份迷失是他心理创伤的根源,他只能在种族文化的夹缝里艰难挣扎,徒劳地寻找自己破碎的身份。在英国社会中,作为黑人的主人公饱受欺凌与侮辱,种族歧视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他被英国社会所排斥,无法得到任何人的认同,整日被恐惧与孤独所包围,这使得他自始至终都具有一种民族自卑情结,这一自卑情结贯彻了他的行动始终。在家庭生活里,面对恋人爱玛和女儿,他无法敞开心怀,由种族而生的自卑与怯懦将他彻底隔绝在了英国白人家庭之外,只能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而存在。“但在我的笑容和欢声底下隐藏着自己的生活灾难带来的苦2cd714fcc736255f9a0159268a05d234涩。”[9]长久的心理创伤证实了主人公难以与英国生活彻底和解,他转而回到桑给巴尔故乡寻找心灵的慰藉,故土的文化给他提供了一个建构自身身份的可能性,他既无法割舍故土的文明,却也被英国的文化所撕扯。当主人公从英国回到故土之后,接受了英国教育的他已逐渐忘记了故土的习俗与宗教信仰,当他与当地居民共同参加祷告时,他无法记起具体的祷告步骤,然而,他不断参与祷告的行为又彰显出他渴望通过故乡人的认同而平复创伤的矛盾心理。在英国文化的规训之下,主人公内心的天平已经失衡,故土文明对英国文明呈现退让的姿态,这是他身份迷失的关键体现。在回到非洲故土之后,主人公反复表露出对女友爱玛的思念,爱玛是英国的一种符号表征,身处故土的主人公无比渴望回到英国,他的精神已在英国扎根,这与他身体所属的黑人种族构成了一种讽刺性的悖论。主人公难以确认自身的身份,只能在由种族所带来的创伤之中痛苦挣扎。
三、重构身份与治愈自我
朱迪斯·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中指出创伤治疗的必要性,并将创伤复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10]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选择了面对现实,他彻底打破了以沉默与谎言所伪造的虚幻形象,直面心理的创伤,尝试与他人建立联系,建构自身的主体性。主人公在英国与故土之间做出了抉择,他不再隐瞒自己在英国有了女友与3a0244f87754f122b92b159fccc38ce2女儿的事实,告诉了非洲家庭真相。他切断了自己在故土建构身份的可能性,尝试走向真实的自我,直面自己的欲望,这一抉择为其身份重构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内心场域。然而,当他重新回到英国之后,等待他的是沉重的打击与挫败,他的恋人爱玛在他返回非洲期间已另寻新欢,这使得他在英国重建家庭的愿望宣告破碎。他重温与爱玛相处时的记忆,并不断反思过去的自己,追问自己的生父前往英国的原因,身份的迷失与错乱使其陷入了酗酒的泥潭。女儿阿美莉亚难以忍受他的颓败不堪,也离开了他,他的英国梦彻底结束。但是,这双重身份的破灭并没有使主人公一蹶不振,反而唤醒了他潜意识深处的反抗力量,“我必须杀死那个我认识的自己,然后才能找到我将要成为的另一个人。”[11]最终,主人公选择回归到正常生活之中,重新建构与他者的关系,并渴望在新的关系中疗愈自我。他产生了主动联系异性艾拉的想法,并想询问她是否愿意去看一场电影。这一内心活动正反映了他渴望重新获取社会的关注,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追寻自我的身份,修复自身的心理创伤。
四、结语
本文从创伤书写的角度剖析了古尔纳《赞美沉默》中主人公的心理创伤与疗愈。在家庭、文化、种族三重创伤成因的裹挟之下,主人公始终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他保持着过度警觉的精神状态,被童年暴力与家庭残缺的记忆反复侵扰,他在长期的种族主义压迫之下以禁闭畏缩的姿态应对一切。这反映了以桑给巴尔人为代表的黑色人种在欧美国家的生存困境,也揭露出非洲地区自身的政权暴乱与观念腐朽,集中体现了漂泊在故土之外的黑色人种在不同民族文化夹缝之间艰难求生的现状,同时,也展示了创伤疗愈的路径,即直面创伤,哀悼过往,寻找自我,建构自身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1]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31.
[2]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赞美沉默[M].陆泉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11.
[3]SIGMUNDF.Remembering,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III[M].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53-1974:154.
[4]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赞美沉默[M].陆泉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41.
[5]袁俊卿.“最后的礼物”: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沉默叙事[J].当代外国文学,2022,43(02):105.
[6]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全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88.
[7]Jeffrey C.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Jeffrey C.Alexander(ed).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01.
[8]朱振武,游铭悦.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最新诺奖作家古尔纳《最后的礼物》的创作旨归[J].山东外语教学,2022,43(02):72.
[9]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赞美沉默[M].陆泉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101.
[10]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25.
[11]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赞美沉默[M].陆泉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252.
作者简介:
姜贝贝,女,汉族,湖南岳阳人,江西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