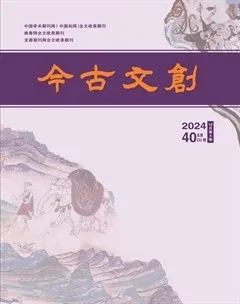离散悲歌
【摘要】山内若子在其戏剧代表作《灵魂要起舞》中真实描绘了日裔美国人的农场经历,剧中惠美子的独特性值得关注。基于离散批评,本文分析了惠美子生存的双重困境,以及身心困境赋予她的双重意象。囿于身体困境,她是笼中之鸟;苦于心灵困境,她是不屈的竹。通过分析发现,惠美子的形象不仅具有个性,更具有普遍性,她是日裔美国作家笔下反传统女性形象的代表,面对困境,她们不再隐忍,勇敢地追求独立与爱,表达了日裔美国女性在压迫中对美与自由的渴望。
【关键词】山内若子;《灵魂要起舞》;日裔美国文学;离散
山内若子(Wakako Yamauchi)是当代亚裔美国女性作家。作为二代日裔美国人,她的生活经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她的作品聚焦于日裔美国人的迁徙、失根、同化与集中营生活[5]。戏剧《灵魂要起舞》(And the Soul Shall Dance)改编自她于1974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延续了她的创作主题。该剧讲述了两个日裔美国家庭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为了生存而痛苦挣扎的经历。其中村田与他的妻女花子和雅子一家过着简朴但温馨的生活,而另一家冈虽然与村田有着同样的梦想,希望能在美国淘金后返乡,他的生活却并不顺利。为了改善留在家乡的妻女静江与清子的生活,冈独自一人来到美国闯荡,然而还未等到他衣锦还乡,静江就因操劳离世,紧接着他被安排续娶了妻妹惠美子,但这段婚姻名存实亡。惠美子被送往美国后,冈与惠美子都生活在痛苦与折磨中。剧中的人物惠美子是最特殊的一个,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孤独地游离在群体与社会的边缘,穷极一生沉溺在返乡的梦中,深陷双重困境,唯有灵魂伴着思乡悲歌而舞。
离散批评经常被用于文化研究、区域研究和种族研究中。“离散”(diaspora)一词起源于希腊词汇“散播的种子”(diasperiein),原是特指公元前3世纪被迫流亡的希腊语犹太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离散”的阐释越来越具体化,“离散”的范围也扩展至全球。后殖民理论家将其他背井离乡的少数族裔也纳入“离散者”的范围。在《国际政治中的现代流散》(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耶路撒冷学者加mPpBk+L1exJZlgGIrbqn1nCV7qbcTBHSsnjgZYNj3DQ=布里埃尔·谢夫(Gabriel Sheffer)提出“共同的种族-民族主体”的概念[8]1,分析了离散mPpBk+L1exJZlgGIrbqn1nCV7qbcTBHSsnjgZYNj3DQ=族裔者与母国和归属国的关系。但离散群体不只限制在少数族裔内,罗宾·科恩(Robin Cohen)将离散群体分为五类,“受害者离散、帝国主义离散、劳工离散、贸易离散与文化离散”[4],这样的分类在细化离散者的同时,将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也纳入离散者的范畴。澳洲学者苏德什·米什拉(Sudesh Mishra)在2006年提出术语“离散学”[7]14,首次明确地将离散作为学科进行研究。
同时,国内文学界也掀起了离散研究的热潮。国内学者不仅仅满足于研究离散现象,他们还不断丰富离散的内涵及其相关概念解读。王宁论述了离散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及其影响,“对流散的现象并不可以一概而论,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173。钱超英也探究了流散文学与身份的关系,他指出应对流散群体进行“族群细分”,并强调了这个“族群”是指“族内群体”[1]84。这个强调肯定了同一离散群体内部仍存在不同之处,并且应重视离散现象背后的复杂因素,看到族内差异。
离散批评的内涵经历了从泛化到具体化的过程,族内差异也逐渐成为离散研究的重要因素。这个过程为讨论惠美子的形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探究离散现象时,必须考虑离散背后的复杂因素,如母国与归属国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移民机缘、阶级、性别等,离散个体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因此,《灵魂要起舞》中的日裔美国群体可以被划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而惠美子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当分析惠美子的形象时,她不仅具有与其他日裔美国人同样的特征,同时仍具有强烈的独特性,这种特质明确地把她同剧中的离散群体剥离开来。与其他角色不同,她遭受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身心的困境同时赋予惠美子两种不同的意象。本文将从离散的角度分析惠美子的双重困境,并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形象成因。
一、惠美子的身体困境
罗宾·科恩总结出了离散群体的普遍特征:远离故土,遭受创伤;希望回归或是仍与祖国有联系;与归属国关系恶劣;在新的国家有集体责任感与族裔意识等[4]180。《灵魂要起舞》中的一代日裔美国人也显示出这样的特征。但因为惠美子的独特经历,她并非自愿来到美国,与群体的关系并不亲近。她就像笼中之鸟,被困于美国土地。
(一)身体困境:笼中之鸟
身体困境是惠美子最明显的悲惨遭遇。终其一生惠美子都活在思乡的梦中,陷于美国大地,生活困苦,她就像笼中之鸟,想要逃离而不得。
身不由己的移民安排让惠美子失去自由,受尽折磨。在故事开始,冈就表明他和惠美子的婚姻是“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他们把她送到我身边来。办理好一切!移民,花销,一切” ①。冈的自陈清晰地表明了惠美子来到美国是不得已被安排而来。后来的对话中她强烈的思乡之情也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她必须生活在美国,但她从不认为应该属于这里。惠美子对雅子说:“我的家……日本……我真正的家。我计划着回去。”[10]145但是这样的计划注定是失败的,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仅仅靠微薄的积攒很难达成理想。并且在故事结尾,冈的举动彻底粉碎了惠美子的归家之梦。他“偷了”惠美子存的钱并花给了他自己的女儿[10]168,使得惠美子再无可能归乡,永远困在了这片土地。除了失去自由,她还遭受着冈的家庭暴力。剧中多次描写了冈“打”和“掴”惠美子的场景,他称惠美子为“妓女”和“疯女人”[10]145-50。失去自由与遭受家暴都体现出惠美子的身体困境。
如果说仅仅是失去自由已够痛苦,那么来到“自由的国度”却失去了自由则更显讽刺。剧中有首名为“笼中之鸟” ②的歌[10]142,惠美子闻歌落泪。她沉浸在歌曲与回忆中,联想到自己,被送到美国来的她就像笼中之鸟,毫无自由可言。来到美国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她除了接受别无他法。在日本,她生活在城市中,接受文化教育,学习“经典事物:舞蹈、筝、花道,当然还有茶道……”[10]147。而到了本应更现代化的美国后,惠美子却过着艰苦的农场生活。惠美子说日本“一切都很有规范”[10]147,而在美国她却不得不忍受不合理的家庭暴力。她说她的父母非常严格,因为他们认为抛头露面的职业不适合女人[10]147,所以他们不喜欢她唱歌并把惠美子送来了美国。按说摆脱了父母约束的惠美子应该能更自在地生活,然而美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日裔美国人落后的生活环境打碎了预想的一切,她只能日日无助又绝望地困在这里。
身体困境使惠美子就像一只失去自由的鸟,被关在这困苦的异乡牢笼。
(二)时代与社会的笼鸟
一个人无法逃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惠美子也是如此。笼鸟的困境是由时代与社会环境造成的,她既经历着日裔美国人所经历着的植根在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又遭受着日裔传统的父权社会压迫。
20世纪初包括惠美子在内的日裔美国人都遭受着种族偏见的压迫。那时许多日本人认为美国是他们的理想国度,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了美国。此时的日本,国家实力正处在上升阶段,日裔美国群体的生活状况优于其他在美少数族裔,然而他们仍无法摆脱种族主义的偏见。1907年,为应对美国劳工强烈的排日情绪,美国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本停止向美国输出劳工,美国停止歧视日侨。因此日侨只能以非劳工身份移民美国,许多日裔美国人在美国西部开始了农场生活。金惠经(Elaine H·Kim)总结了二战前日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他们发展出一种社会经济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与美国主流社会平行但又存在于主流社会之外。”[6]122《灵魂要起舞》也清晰地体现了这样的种族偏见。村田和冈都是为了“赚些钱”,“像个国王一样回家”[10]138,但来到美国后他们发现这样的想法是很难实现的。花子和女儿雅子的对话吐露出日裔美国人在异乡生活的心声,“白人和我们不同……白人是白人……和白人中的日本人不同”[10]153,“我们在这里谁都不是”[10]154。他们被美国社会排斥,生活范围受限于西部农场,与主流社会分隔,无法融入美国社会。这样的平行模式使得日裔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本土格格不入。冈描述说:“他们看不起日本人……那愚蠢的服务生几乎是要把食物扔给我们……食物也很糟糕,雅子根本无法咽下干面包和红肠”,村田听后称那些白人为“蛮族”[10]156。日裔美国人被美国社会排斥,遭受着主流社会的偏见,惠美子也不例外。但与剧中其他角色不同的是,惠美子和花子还是性别压迫的受害者,而惠美子的独特遭遇让她遭受了花子未曾经历的。惠美子是时代的受害者,她是“照片新娘”之一,身不由己来到美国。
“截至1924年,美国国会颁布法律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超过14000名日本女人到达美国,其中大部分是作为‘照片新娘’来与他们只见过照片的丈夫组成家庭”[6]124。惠美子也是“照片新娘”之一,而她的情况还不如普通的“照片新娘”。起初,冈是她的姐夫,这段婚姻安排对惠美子和冈来说就像是一场闹剧。冈说:“我没有娶她,他们把她嫁给了我!就在静江才去世不久……尸骨未寒!没有尊重!他们说她长成了个漂亮的女人,会把我侍奉的很好。”[10]138这段话不仅显示出冈对这场婚姻安排的不满,更显示出在保守、等级制度严苛的日本,男尊女卑已经成为理所当然。日裔美国人也保留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在这个“自由的国度”,女性不被允许拥有工作,所以他们依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生活。村田在剧中说:“在这里,马匹和妻子同样重要。”[10]136冈便是如此,一个传统又保守的男人,认为惠美子应该对他和蔼点。在他的观念里,惠美子是属于他的,因为惠美子的父亲把她像猫猫狗狗一样送给了他,他有权对惠美子做他想做的一切,且他怀疑惠美子的忠贞[10]150。在这种传统父权思想下,从来没有人考虑过惠美子的感受,她不可能拥有自由且独立的生活,攒到积蓄返回日本。她只能日复一日地困在贫苦的农场,悲惨地思乡。
因为种族偏见与传统性别偏见,惠美子成为特殊时代下悲剧的笼中鸟,在夹缝中生存,被束缚在大洋彼岸无法逃离。
二、惠美子的心灵困境
离散批评发展下个体性差异越来越成为分析离散群体的重要影响因素,并趋向于把离散群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分为不同的类别进行探究。张冲认为威廉·萨弗兰和罗宾·科恩的观点聚焦在“散居族裔现象的地理特征、本身的意识”,忽视了离散族裔内部的具体情况,如“阶级、阶层、性别、代等方面的不同”[3]88。从这个角度看,惠美子具有很明显的特殊性,她不属于剧中散居族裔内的任何一类。她是反叛的一代日裔美国女性,这三个特点将她与花子和静江,雅子和清子,村田和冈区分开来。在这三个特点中,最有独特性的就是她叛逆与反传统的形象,与传统背道而驰也使她承受着精神的折磨。面对心灵困境,她就像宁折不弯的竹。
(一)心灵困境:不屈的竹
心灵困境是另一个伴随惠美子一生的阴影,包含着无尽的孤独和她的叛逆。她就像不屈的竹,尽管生活十分困苦,她从未向现实低头,哪怕以折断生命告终。
就像上述所说,惠美子不属于剧中离散群体的任何一类。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惠美子的内心世界,所以她忍受着极致的孤独,渴望与人倾诉。在离家千里的大洋彼岸,作为她枕边人,本应是最亲近的人的丈夫冈只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他嘲讽惠美子说“她懂什么灵魂”[10]145。他只关心现实,不理解惠美子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家中没有留声机,因为冈觉得他们没有机会听,更不能理解惠美子对于歌舞的热爱。在冈看来那些东西是浪漫的,同时也是缥缈无用的,惠美子与冈的冲突就像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个寻觅精神的丰盈,另一个追求物质的富足。村田夫妻也不能理解惠美子,他们知道惠美子渴望返回日本,但他们只认为惠美子是一个无法适应美国生活的可怜女人。在村田夫妇的观念中美国农场生活同样不需要文化训练,只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10]138,他们不能理解惠美子的浪漫,她的精神追求。更不要说二代日裔的清子和雅子了,清子自来到美国后就不断强迫自己融入环境,尽力摆脱身上的日裔痕迹。她觉得惠美子恨她,不理解惠美子为什么不能像花子一样接受这里的生活,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并问花子“那她为什么不回去?为什么留在这里”[10]162,她不清楚惠美子的经历,不明白惠美子的坚持与反叛。而另一个女孩雅子似乎能与惠美子产生共鸣,可仔细探究,这种共鸣只是表层的共情,而非真正地理解。作为二代日裔美国人的雅子,从小在美国长大,从未见过父辈眼中怀念的“家乡”,她不愿返回日本,听不懂日本歌谣,更不能理解惠美子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希望回归故土。因此,没有人能真正理解惠美子的内心世界,她生活在精神的荒漠,忍受着无尽的孤独。
除了孤独,惠美子更是反传统的。花子曾告诉她的女儿雅子说:“好吧,这可不容易……但一个人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弯下腰……就像竹子,当风刮过,竹子就会弯。你要么弯腰,要么折断。”[10]148而惠美子就是这不屈的竹。她宁愿折断也不愿向现实低头。花子认为惠美子“无法适应这样的生活。她无法忘记她在日本的美好时光”[10]148。但事实是惠美子不是不能,而是不愿。就像前文所说,惠美子与冈的冲突就像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在处理她与冈的关系时,其实她知道怎样做能让彼此都轻松些。冈也对惠美子说:“我只是想让你和善点……明白这也不是我的错。让我的生活好过点……也为了你的。”[10]152但在听完了这段话后惠美子仍像以往一样躲开了冈的触碰。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现实,她能够适应但她不愿这么做,哪怕换来的是冈的暴怒和回击。同时,她宁愿生活在思乡的梦中,哪怕深知梦的悲痛。她说:“梦是难以忍受的……无法忍耐的……”但她也说:“因为我必须让梦鲜活……梦是我活下去的全部……如果你让我相信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梦会凋零……我也会枯萎。”[10]152这就是惠美子的叛逆,拒绝顺应现实,终其一生她活在归乡的梦中,尽管她明白梦想无法实现,她也不愿像代表传统日裔女性的姐姐静江和村田的妻子花子那样乖顺、牺牲、忍耐。留在日本的静江的形象在丈夫冈的叙述中是家庭中不被偏爱的那个,她不能去学校,被安排嫁给家里人看不上的冈,她“像狗一样工作,让父亲开心……从不抱怨,做所有家务”[10]150,最终静江因劳累去世。花子也有同样的观念,哪怕在农场的生活再艰苦,她也安于相夫教子,毫无保留地付出,她认为女人必须耐心,悉心照顾家庭,把家庭重任扛在肩上,花子说:“有时梦想让生活更加艰难。最好把脑袋从缥缈的云上拿下来。”[10]154而惠美子绝不愿意用世俗的要求约束自己,她抽烟、喝酒、歌舞,做着传统女性不被允许做的事情,为自己而活。她也不愿像二代日裔的雅子和清子一样,被陌生的文化同化。其他角色来到美国后或多或少地向现实低下了头,改变自己以融入群体,融入环境,只有惠美子是反叛者,坚持为了自己而活,坚持自己的理想。
如果惠美子为现实忍耐,她会过得好些,但那非她所愿。她宁愿直面心灵困境,遭受精神折磨,也不愿向现实低头。她就像孤傲的竹,即使面对疾风,宁折也不愿意屈服。
(二)孤竹的理想与渴望
惠美子心灵困境实际来自她自身的理想与坚持,表面上她不愿向现实低头,但宁折不屈的举动下深藏着惠美子对爱与美的渴望与追求。
尽管身处异国他乡,面对心灵困境,惠美子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热爱的事物,她用歌舞在异国他乡为自己搭建起归乡之梦。剧中有两次直接描写惠美子和歌而舞的场面。第一次是村田一家拜访冈时带来了留声机,惠美子唱起“灵魂要起舞”(The Soul Shall Dance),随着“笼中之鸟”(Kago No Tori)“孤独地站着而缓缓起舞”[10]142。在这次拜访中,她把这首歌谣耐心仔细地解释给雅子听,并在村田一家将要离开时不断挽留。这些举动表明她并不像花子先前所说的那样奇怪冷漠[10]140,相反她十分愿意分享自己热爱的歌谣与舞蹈。她称这个夜晚是个“可爱的夜晚”[10]146,因为她用歌舞为自己构建起生动的梦,听着手摇留声机里传来的歌曲,惠美子好像回到了东京,找到了当时的自己,在台上起舞。第二次描写是在故事末尾,此时的惠美子自知不可能再回到故土,她“穿着漂亮的和服”再次唱起了“灵魂要起舞”[10]174。这次,她真切地知道归乡之梦已经破碎,只能在歌谣与舞蹈中寻找故土,所以起舞时她依然笑了。她舞着,笑着,用热爱的歌舞为自己筑造起思乡的梦。歌与舞是她从日本带来的事物,是她怀旧的方式,更是她不会放弃的毕生所爱。
惠美子的思乡不仅仅是简单的情感渴望,更代表着她对真正理想与爱的追求。在20世纪30年代初,“东京正值现代都市文化繁荣发展阶段”[9]37,惠美子那时就在东京接受文化教育。她喜欢现代都市的歌曲,而且“几乎成了一个名角”[10]147。如果一个人本可以在自己的故乡生活,在热爱的事物上有所成就,突然被迫孤身去往异国他乡,失去从前拥有的一切,任谁都会感到失落与绝望。更不要说惠美子失去的不仅仅是梦想,而是她所爱的一切,不仅包括事物,更包括爱人。她在东京有一个恋人,突然被送到美国切断了她和故土以及恋人的联系。她本可以在城市中过着理想的生活,在恋人的陪伴下进行热爱的事业,而现在她只能终日处在精神荒漠中,忍受着无尽的思乡与孤独。可尽管如此,她也不愿屈服,宁愿受心灵所苦,依旧坚持着回到故土去追寻真爱的梦想。日本有她所爱的一切:歌谣、舞蹈、恋人。回到故乡不仅仅是空间的变更,更代表对梦想的坚持,对爱与被爱的能力的追寻。
综上所述,惠美子就像是不屈的孤竹,特立独行而充满浪漫与理想,心灵困境中的惠美子,仍有她自己的坚持,有她自己对美与爱的渴望。
三、结语
通过离散批评,本文通过关注离散族裔的个体性差异分析了《灵魂要起舞》中惠美子角色的独特性。不同于剧中的其他人物,惠美子经历着身心双重困境,并由此概括出表现惠美子形象的两种意象——笼中之鸟与不屈的竹。剧本之外她代表了一类离散族裔女性。“惠美子”们受过良好的教HuRacDUmUd8VHx2+HhE3kA==育,孤独而叛逆,她们生活在双重压迫下却从未向枯燥艰难的生活低头,她们坚持为自己而活。就像山内若子在采访中说的那样,女性有权利选择要不要成为牺牲者,惠美子的双重困境显示出少数族裔女性对于独立、爱与美的追求与渴望。
注释:
①本文中《灵魂要起舞》的中文翻译均为作者自译,后文对戏剧原文的引用不再标注。
②原文使用的日语罗马音,意为“笼子中的鸟”。
参考文献:
[1]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77-89.
[2]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J].社会科学,2006,
(11):170-176.
[3]张冲.散居族裔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5,(02):87-91+173.
[4]Cohen,Robin.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M].
London:Routledge,1997.
[5]Genzlinger,Neil.Wakako Yamauchi,93,Writer of Japan’s Diaspora[N].New York Times,vol.167,no. 58082,2018:B14.
[6]Kim,Elaine H.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8.
[7]Mishra,Sudesh.Diaspora Criticism[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
[8]Sheffer,Gabriel,ed.Preface.Modern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M].London:Croom Helm,1986.
[9]Takita,Yoshiko.And the Soul Shall Dance: Wakako Yamauchi and Mad Woman[J].Pacific & American Studies,2002,(2):35-44.
[10]Yamauchi,Wakako.Interview with King·Kok Cheung[M].Words Matter: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