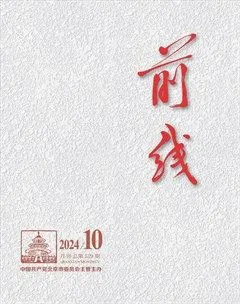一道平冈是九边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进攻的重要防线。明代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尤为明显。明太祖开国时期,西逃蒙古余部势力还在,东北女真部落逐渐壮大。为应对边患危机,明代加强长城修筑,形成“九边”军镇的抵御体系,大小堡垒数百座,构筑了一条较为坚固的防线。清政权建立后,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频繁,关外少数民族与清廷不再是紧张的对峙关系,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发生了改变。
清代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女真部落生活在东北一带,女真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三部,明朝政府设置努儿干都司,对女真各部分而治之,实现对其的控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率领建州女真部众征战数年,结束女真各部相互掠夺残杀的局面,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并迫使蒙古科尔沁和扎鲁特等部众归附。随后,努尔哈赤率领军队对明军展开进攻,双方在萨尔浒、大凌河等地激战,明军主力损失较大。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在征战中被明军所伤,随后病死,由他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公元1636年,努尔哈赤去世10年之后,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改族称“女真”为“满洲”,争天下之志已不在长城之外。松锦之战后,清军转入战略进攻,突破明军防线,进入山海关,定鼎京师。到了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进攻南京城,南明政权灭亡。康熙时期,清廷解决了三藩问题,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地收归中央政权,并成功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疆域的统一。
为实现边疆安定,清廷加强了对相关地区长城的修筑工作。当时,蒙古部落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清军入关前通过军事征服、满蒙联姻等方式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建立联盟。漠西厄鲁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其中准噶尔部较为强大。为防御准噶尔部袭扰其他蒙古诸部及山西、陕西、宁夏等地,清廷在杀虎口、张家口、独石口等重要关口增派八旗兵,并于山西右卫、甘肃凉州屯驻八旗,加强西北长城一带的防务。雍正时期,清廷继续修筑长城边墙,募兵增防古北、宣化、大同三处,增加独石口至杀虎口一带险要关隘的守兵数量。自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廷多次出兵平定噶尔丹部叛乱,最终取得胜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有序。
清廷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在适当保留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实现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在蒙古地区实行蒙旗制度;在西藏地区通过册封确立达赖、班禅的宗教地位,并设置驻藏大臣统掌军政;在新疆继续实行札萨克制度和伯克制度,并派驻参赞大臣、伊犁将军进行监督。
清廷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策略,有效处理中央政权与各民族地区的问题,将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版图,形成大一统的局面。自此,历史上中原王朝所面临的边患基本解除,长城内外各民族间的往来更为融洽,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变。
清代长城修筑工程渐少
大一统格局形成过程中,清廷逐渐减少了长城沿线防御设施数量,压缩了驻军规模,如减少长城墩台、兵丁数量。张家口至山海关较明代所设台座减少十之七八。当然,为了保障京师安全,在独石口、古北口、山海关等边关要塞依旧要驻扎八旗兵,形成拱卫京师的一道屏障。
清廷逐步减少对长城的大规模修筑工作。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浙江道监察御史季振宜奏请修筑西宁至宣大等处颓败的墙体,议政王大臣商议后认为修筑长城的经费支出较大,战乱之后物力难支,不予支持。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工部等提出修筑古北口一带倾塌边墙的奏疏。皇帝则认为治理天下不应专恃险关要塞。秦朝修筑长城,汉、唐、宋朝也时常维护,但边患仍然不断。明朝虽有长城屏障,清军却能长驱直入,入主中原。可见,守国之道在德不在险,修德安民,民心悦则政权稳固、边境安全。修缮沿线长城工程浩繁,派遣众多官兵进行守卫,劳民伤财,实属无益之举。清代诗人、翰林院编修查慎行随驾途中作《随驾行兴安岭上》:“圣朝不画长城界,一道平冈是九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之间再无战事,横亘东西的辽阔草原,牛羊成群,庐帐遍布,安定生活的蒙古部众,已经成为守卫边疆、护卫京师的屏藩。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居庸关的北关因年久失修,出现倾圮残缺,直隶总督孙嘉淦组织人员修缮,以存规制而示观瞻。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潮河暴涨,洪水冲坏古北口边墙。乾隆帝认为朝廷以德威遐讫,不依赖边墙,只需将外层稍加修葺即可。乾隆帝途经居庸关时曾赋诗一首:“居庸天险列峰连,万里金汤固九边。雄峻莫夸三峡险,崎岖疑是五丁穿。岚拖千岭浮佳气,日上群峰吐紫烟。盛世至今无战伐,投戈戍卒艺山田。”写出了昔日边关的险峻和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下驻军、家属以及他们后代日常生活的场景。
尽管停止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工作,清廷仍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对长城进行加固,使得长城依然巍巍壮观,令人叹为观止。乾隆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留下很多关于长城的记载,如“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一条城墙,也没想到它能建到这些地方。站在一处,一眼望过去,这条堡垒式城墙从小山岭到最高山顶,穿过河流上的拱门,下到最深的山谷,在重要隘口地方筑成两道或三道城墙,每一百码左右距离建有一座高大的棱堡或楼塔,整个这条城墙一眼望不到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长城因山势而雄伟,山势因长城而更加险峻,这一伟大的建筑奇迹使得凡是到过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雄伟气势、宏伟规模。
清代长城功能的转变
有清一代,随着蒙古各部归顺清廷,长城关口不再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要塞,而成为蒙古年班进京朝贡的要道。
按清制,蒙古各部来京朝贡往来必经长城关口。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清廷规定,蒙古各部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出入。除此六个边口外,不许从他处边口出入。同时,清廷在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建有通往蒙古地区的官方驿道。蒙古各部通过官方驿道入关,关口处设有员外郎、笔帖式各一人对往来人员、货物进行管理。蒙古年班进入关口时,官弁详细记录人数,出关时再次核对后出关。如携带置买的物件,则需持有理藩院转行兵部的出边执照始准放行。嘉道时期,龚自珍路遇蒙古年班进京使者,在所作《说居庸关》中写道,行至南口,道路或容十骑,或容两骑,或容一骑。他迎面碰见蒙古人鞭打橐驼自北而来,“橐驼冲余骑颠,余亦挝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人大笑。龚自珍慨叹若非实现天下一统,来自江南的他,怎能与高大威猛的蒙古人摩肩并行于万山之间。
长城沿线的杀虎口、张家口、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等关口,也成为清代的重要税关。清廷撤销了明代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边关卫所,设置地方行政建置意义上的郡县,这些边关重镇逐渐发展成为较为繁荣的市镇。杀虎口地处山西与内蒙古的交界地带,明代为防范蒙古各部南下,派重兵防守抵御,时称“杀胡口”,康熙帝亲征大败准噶尔后,改称“杀虎口”。杀虎口、张家口等关口主要对内地与蒙古各部之间的货物进行征税。蒙古的牛马由此进关,山西及南方的茶叶、棉布、铁器等由此出关。这些边关郡县,商旅通行、百货凑集,吸引着众多百姓前来从事商贸活动,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长城关口逐渐由军事关防变成检查流动人口的关卡。清廷限制关内百姓前往东北开垦土地、从事贸易活动,汉民只能通过长城关口出关,经过守口官兵严格盘查后才能放行。山海关外的东三省地方被清朝统治者视为满洲龙兴重地,不准流寓商民杂处其间。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清廷规定,每年年底,流民所往州县地方官要及时驱逐未如期回籍者。在喜峰口等十五处关口加派官兵,会同地方官,逐项查验放行。当然,随着人地矛盾加剧,特别是清代中叶以来,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计困难,东北地区还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贫苦百姓迫于生计,千方百计出口谋生,汉民租种旗人土地的情况增多,清廷基本默许了这种行为。
清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入关前与蒙古部落建立联盟关系,入主中原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不再是对峙状态。由此,长城不再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地带,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也逐渐发生了转变,成为联系各民族人民的纽带以及各族人民交往融合的重要场所。
(作者简介:张艳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