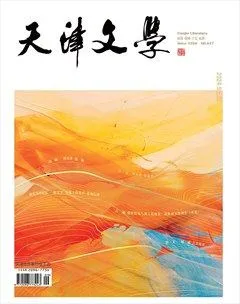雨水里的土豆
她原来不叫土豆儿,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出来饱满丰润,听起来明亮雅洁,是她妈给取的,只不过人们——包括她爸,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
土豆儿属龙,龙年多雨。她出生的那个龙年,雨尤其多。
辽西十年九旱,土地多在山坡上,多雨的年头大多是好收成。农谚云:“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农历五月,雨不要太多,人们除草、间苗、追肥先把地收拾出来,六月里多下些雨,山坡地旱不着,房前屋后的平地也不至于就涝了。不过这一年的雨来得比往年早,从五月下旬便开始下,上一场雨后地上还泥泞着,下一场雨又来了,地里苗和草比赛着长,长着长着,草比苗高了。人们只好雨一停便下地薅草,浑浊的泥水顺着薅出的草根往下淌;薅出的草扔到地头上,也不打蔫,就地扎根,接着生长。
土豆妈生土豆已是六月初,天气仍一阵阴一阵晴,雨还是一阵大一阵小,淅淅沥沥没完没了,简陋的院墙在雨中坍塌了一大块,邻家的公鸡从缺口踱进院子,压着嗓子忧愁地长叹一声“咯喽——”。这一切使月子里的女人心神不宁。她的男人老实木讷,火上房都不着急的脾气,除了在生产队上工,回到家里便什么都不管了,灶膛里的火着出来,都不会帮着往里填一把。生孩子当天,接生婆帮着煮一碗粥,第二天她就得自己下地做饭了。这倒也罢了,她毕竟年轻,身体壮着呢,要命的是,随着满月的临近,家里断粮了。
吃了两天野菜,女人发现奶水见少,心里一着急,更下不来奶水了。婴儿的哭声已喑哑无力,她再也忍不住,早起对男人说:“你出去借点粮食吧。”
男人嗫嚅着:“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断顿的也不是咱们一家,去谁家借啊?咱们还是挖点野菜吧。”
“孩子吃不下啊。”
“再不,你出去借?娘儿们家好开口。”
“我还在月子里,按礼不能进人家的门,站在门前人家都嫌晦气。”
男人垂下头不吱声,她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晌午时雨停了,天空明亮起来,隐隐地看见太阳在云层里穿行,甚至在灰黄的云彩缝里看见一丝碧蓝的天。不远处传来公鸡嘹亮的啼叫声,女人惊喜地说:“这是要晴天了吧?”
男人倒比她在行:“这是亮晌,看这云彩,怕是后晌还得下呢。”
女人不吭声了。
到了后半晌,老天忽然又暴躁起来,电闪雷鸣,大雨瓢泼似的,残存的那部分院墙稀里哗啦成了一长溜儿的石头堆。一个时辰后,山坡上下来的狂傲的洪水,终于冲刷净屋子后墙根的泥土,水流从墙缝喷涌而入,在屋地上打着旋儿地往上涨,女人并排放在炕沿下的一双鞋,像两只小船一般,水涨船高地漂在水面上打转,女人手疾眼快,一伸手,食、中二指同时勾住两只鞋后帮,把鞋捞上炕来。地上的水没在屋里停留,夺门而出奔向灶间,从屋门流走了。
好在老天也累了,雨越来越小,黑天的时候,终于停了。女人下地,踩着泥水到另一间屋,从炕上抱来以前备好的柴火,蹲到灶前点火。虽然没被雨水淋到,柴火在潮湿的空气里也变得软耷耷的,火柴也不干燥,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把火点着。她把笼筐里的野菜倒进水盆里,筐底露出一个鸡蛋大的土豆,她想起来,前晌她出去找野菜,路过李家兄弟俩的菜园,看见李老二这边的园墙边,有几棵马齿菜贴着地皮铺展着,便打开树枝编的园门走进去。李老二这半边园里的土豆已经收过了,每走一步,泥水都会没到腿肚子。她光着的脚踩到一个圆乎乎的东西,直觉不是石头,猫腰用手摸上来,就是这个珍贵的土豆。当时她攥着土豆愣了一下神,想起自己家的园子,也栽种了好几垄的土豆,园子靠近河边,早在一个来月前被洪水连土都冲走了。虽然队长说明年再给补一块园子,今年的收成毕竟没有了。
这个土豆的出现让她欣喜,第一反应是把这半个园子踩个遍,或许还会有收获。可隔着一条窄窄的水垄沟就是李老大的园子,土豆还没起出来,被雨淋得翠绿的秧子还长在地里,要是被人看见从这园子里往外拿土豆,起了疑心,自己就说不清了。人活一辈子,咋也得有个好名声啊,现在有了这个被自己叫作明珠的女儿,更要为她着想,不能在人前留下短处,让孩子长大直不起腰来。她转身赶紧离开了。
盆里的野菜有好几个种类,苣荬菜、婆婆丁、羊犄角、刺儿菜、马齿菜、苦菜,一齐洗净切碎倒进锅里,煮开了撒把盐,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了。她没把土豆一起煮,怕野菜的苦味浸润到土豆里,而是把它塞进灶膛里靠边的位置,热火烤着,热灰煨着。吃饭时把野菜捣烂喂给怀里的女儿一点点,小孩儿毫不犹豫地用舌头顶了出来,啼哭不止。她把土豆从灶膛里扒拉出来,用手一捏,感觉松软,心知是熟透了,噗噗地吹去沾着的灰,两手倒着,忍烫剥去外表那层薄皮,也没舍得扔,随手塞进蹲在一边的男人嘴里。捏开热腾腾的土豆,香喷喷的气息扑鼻而来,夫妻俩同时咽了一口口水,土豆闪着绵白糖的光泽,她笑着说:“嘿!你看,又甜又面又起沙!”
土豆放进碗里捣碎,兑上几滴开水,调成糊状,女人伸出舌尖试试不冷不热,洗净手,用右手的食指肚挑起一小团,轻轻地抹进婴儿的嘴里,那小嘴吧嗒几下,竟然吞咽下去,不一会儿就把土豆喂进去四分之一。女人不敢再喂了,怕撑坏了这个小人儿。这一夜孩子睡得很实,三个时辰后亮天了才醒,女人积攒了一夜的乳汁,刚好让婴儿安静下来。
明天是月子最后一天,后天便可以到别人家借吃的。去谁家呢?娘家不能去,从小父母便不在了,哥嫂也不亲热,两年前为了二百块钱的彩礼,把她嫁给这个比她大六岁、窝囊得不能挑家过日子的光棍男人。婚后才知道,婚事是他的娘舅张罗的,彩礼钱都是拉的饥荒,得他们小两口慢慢还。
还没等人们吃完早饭,天又下起了小雨,婴儿也伴着雨声哭起来,把乳头送进小嘴里,吸吮几下没有奶水,便用舌尖顶了出来,接着哭。喝了两三天野菜汤的她,短时间内无力聚积出奶水,只好下地把昨天晚上剩下的土豆糊蒸热了,喂给婴儿三分之一。她想,剩下的够晌午喂一次,后晌喂一次,那么明天呢?明天一天怎么熬?
雨是中午停的,下午甚至还出了一会儿太阳,男人趁机挖了些硬泥,掺杂着野草堵上了屋后的漏洞。黄昏时,北方的天空又墨一般黑,隐隐传来雷声,婴儿又开始哭,怎么哄都不好,知道是饿的,可土豆糊已经吃没了。她左胳膊抱着婴儿,右手揉搓着自己干瘪的乳房,希望感受到奶汁涌来时从两腋下直至乳头的酥麻,但是她失望了。
天很快黑透了,一道道闪电撕裂着北方的天空,闪电消失的时候,天空更加黑暗。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小,却没有停下来,男人坐在湿漉漉的门槛上,垂着头,一言不发。女人眼泪流了出来,她想:“要是泪水能变成奶水就好了。”抱着婴儿炕头走到炕梢,炕梢走到炕头,来来回回地走。好不容易睡着了,刚放到炕上,马上便又醒过来,接着有气无力地啼哭。她待到确认睡着了,屏住呼吸放到炕上,还没等抽出手,婴儿又咿咿呀呀地哭。如此几次,女人精疲力竭。快半夜了,北方的雷声由远而近,窗外传来了雨声,想起还有一天多的时间没有吃的,她再也沉不住气,放下婴儿,下地穿上鞋,拎起一个小柳条筐跨出门去,却又回身脱下鞋放到门里。男人颤抖着问:“这么大的雨,你上哪儿去呀?”
女人说:“看明珠吃得下土豆,我再去李老二园子里踩踩去。”随即消失在雨里。
雨越下越大,一个个霹雳在头顶炸响,男人看着哭哑了嗓子的婴儿不知怎么办好。他想抱起来,可她那么小,身体软软的,让他无处着力,只好把她放在被子上,他拽着被子满炕转。
不知过了多久,天亮了,女人却还没有回来。他笨拙地用衣襟兜着婴儿,站在洪水过后一片狼藉的村道上,看见他的人都问:“你这是干啥呢?你媳妇呢?”
他说:“她半夜就出去了。”
“半夜?大雨泡天的,出去干啥去了?家里还有月窠儿孩子呢。”
“说是踩土豆去了。”
“踩土豆?一宿没回来?”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嗯”了一声。
“那你还不快点儿找去,在这儿站着干啥呀?”
人们纷纷四下寻找,整条山沟找遍了,没有人影,只发现李家菜园树枝编的园门上,挂着一个小柳条筐,男人认得是自家的,里面有一个鸡蛋黄大的土豆。住在菜园后面的老夏说,他半夜起来站在窗前看水,打个闪的工夫,看见李家菜园门口有个人影倒下去了,也没看清男女,还以为被闪晃花了眼睛,莫不就是她?又有人说,咱们这儿是天黑才下的雨,北边都下了老半天了,洪水是从北边下来的,水老大了,水里死猪、死鸡甚至檩子、房梁都有。
人们往水流的下游沿村寻去,后晌传来消息:女人的尸体在十几里地外的河边找到了,一个早起的农妇,发现了赤身裸体仰面朝天的她。围观的人们,谁也不知道这个看起来还很年轻的女人是哪个村子的,但毕竟一丝不挂有碍观瞻,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就地铲起一锹淤泥,盖在她的小腹下。
女人下葬了,人们淋着雨为她挖的墓坑,天上下的雨,土里渗出的水,很快积满了长方形的坑。薄皮白茬的棺材下到坑里,水花四溅,浑浊的泥水里,再也看不见棺材的影子。
村里人认为,她是雨夜去偷土豆被洪水冲走的。三亲六故口口相传,十里八村的人都听说,雨下得最大的那天夜里,有一个还在月子里的女人,偷土豆被水冲走淹死了。此地民风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并不在意她的死因,他们帮男人照顾那个可怜的婴儿,李老大出土豆的时候,挑大的送来几个。哺乳期的妇女,碰见男人抱着孩子,会接过来奶上几口,手巧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用旧布对付件小衣服给她。
婴儿最爱吃的还是土豆,她妈是为土豆死的,人们想不起她妈给她取的名字,连她爸也想不起来,干脆便叫她土豆儿。也许生来就是顽强的生命,在那样一个家里,她居然无灾无病地一天天长大了。她模样像她妈,清爽秀气,虽然说话、走路都比别的孩子晚一些,头脑却格外聪明。以她爸的条件,自然是续娶不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七岁上,她就能踩着小板凳够着刷锅做饭,操持家务。人们看着心疼,往往会叹口气说:“这个苦命的孩子啊,她妈要不是黑天半夜出去偷土豆,也不至于被水冲去啊,撇下这小可怜。”
她仰起脸看着说话的人,一开始听不懂,随着年龄与智力的增长,她终于明白,妈是为了给自己偷土豆让水冲走了,从此,对那个一点儿印象都没有的亲妈,又恨又疼,恨她偷东西,死了还让人家笑话;疼她竟然在水里活活淹死,那得多难受!她变得孤僻,暗暗地在心里起誓:不做妈那样的人,一辈子不拿不是自己的东西。
土豆儿长到八岁,正赶上村里小学这年招生,她也去上学了,老师讲的课,她接受得很快,一点就透,考试成绩总是排在第一。但沉默寡言,从不敢举手回答问题,老师叫到名字,她站起来一声不吭。老师生气了,故意不说坐下,她便垂着头站一节课。她不和同龄的孩子嬉戏打闹,大家喧闹着做游戏的时候,她便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是,头上有了几丝白发。
到了三年级,村里的小学合并到外村的总校。有一节是算术课,老师出了一道应用题:“小明一家人一起收土豆,爸爸、妈妈各收三筐土豆,小明和哥哥各收一筐土豆,全家人共收了几筐土豆?”
几个和土豆儿同村的孩子,在四处吃吃地笑起来。下课后,关于土豆儿的故事便传遍了全班。放学的时候,几乎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了。孩子们回家同大人讲起,大人们又回忆起当年的事情,孩子们把听家长说的与同学们交流,连细节都那么详尽。以后除了老师,再没有人叫她的学名,都叫她土豆儿,她感觉到背上有目光射来,针刺般的疼痛。
一天,当着她的面,一个刚上一年级的小男孩问他上五年级的姐姐:“为啥土豆儿她妈偷土豆不穿衣服啊?”
“穿衣服不得让雨浇湿了吗?回家就没啥穿了,她只有一身儿衣服。”
“可是她没回家,被水冲跑了呀。”
“那是老天爷惩罚坏人。你记住,千万不要做坏事啊,偷别人家土豆的人不是被淹死了吗?”这个称职的姐姐,对弟弟的思想品德教育很重视。
这时的土豆儿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学习成绩也不再拔尖了。
土豆上五年级时,正好本命年,又是多雨的龙年。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功课不再优秀。期末考试前,班级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男生的钢笔丢了。这支红色的钢笔,是城里上班的叔叔给买的,曾吸引全班同学羡慕的目光,上午还用过,中午回家吃饭回来,便不见了。全班只有土豆儿不回家,她不吃中午饭,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教室里。她不但有机会下手,还有偷窃的遗传基因,当然成了重点怀疑对象。老师翻遍了她的书包和全身,都没找到那支红色钢笔,问她,她不出声,两只眼睛空洞地望着别处。
老师苦口婆心,想挽救这个失足少女:“知错就改,我们还当你是好同学。你要吸取你妈妈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走她的老路啊!你到底把钢笔放哪里了?”
她一句话不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扑簌簌地流泪,老师叹了口气,摇摇头。
从那天起土豆儿便再也没来上学。好像是两三天之后吧,一个风狂雨骤的午后,她在雨中站在河边等着,不久便看见洪水下来了,高高的水头几乎是一个横断面,像一堵墙一样涌来,土豆儿迅速地扯掉身上的衣服,浑身精光,张开两臂迎着水头扑去。少女的身体如一颗明亮的珍珠,投进污泥浊水中,洪水瞬间接纳了她,像一个母亲包裹着初到新世界的婴儿。
魏红莲,辽宁朝阳人,笔名凌珠。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协会会员。做过农民、煤矿工人。在《天津文学》《散文》《散文百家》《芒种》《作家天地》《岁月》《辽河》等期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出版长篇小说《醒心杖》。
责任编辑:艾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