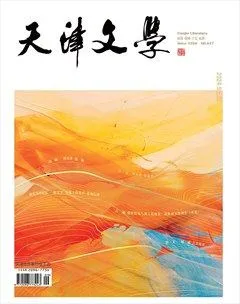义奴
多年以前,我供职的工厂与日本企业合资,中方以51%的股比控股。作为技术人员,我参加了合资公司组织的日语培训。没想到,结业考试后,还拿到了鼓励前三名的奖金。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闹着请客,就在单位旁边的广东菜馆,请他们撮了一顿。
之后不久,我考入一家认证机构,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开始几年还和老同事们联系着,后来听说公司变成了日本独资,有的老同事选择离开了那家公司,没离开的,也都忙着干活挣钱,就慢慢疏于联络了。我也成了认证机构的业务骨干,不是在审核,就是在去往审核的路上,那家企业就更加与我渐行渐远了,以致我都几乎忘了自己曾学过日语。
直到去年回老家,和老父亲拉家常,说起我儿子看同事家养的金毛伶俐,也闹着要养一条的事。我一向认为,乡村平房院落为主的环境才更适合养狗,坚决反对把狗憋屈在楼房里。何况金毛个儿大,洗澡搞卫生的都麻烦。听我念叨这些,年逾九旬却仍精神健旺、耳聪目明的老父亲,便跟我讲起了一段他小时候养狗的往事——
那时咱家院子大,正房、厢房十来间,都是你老老太爷留的家产(家乡话,老老太爷指高祖,即我爷爷的爷爷)。虽然家道中落了,后辈儿孙大都还住这大院里。土里刨食的,打鱼摸虾的,跑买跑卖的,各想各的道。女人们把着自家男人挣来的辛苦钱,赶集上店,总是院里娘儿几个一道,做伴壮胆,遇事也好有个商量。
这天,你奶奶她们娘儿几个从郝镇赶完集,说笑着往家走。你大娘听后面有点动静,回头一看,是只大黄狗,脖子下半圈白,因为脏,也跟身上的黄色差不多了,在她们身后十来步远站着。娘儿几个扭头走,它就跟着,站下看它,它就也站下。两三回后,你奶奶说,这狗别是想跟咱回家吧?那时三天两头有土匪在这带出没,外地来这做买卖的,养只狗看家护院,做不下去走人,撇下狗是常事。你大娘对狗说,你呀,别跟着啦,我们家人多,不养狗。狗不出声,再走还跟着。娘儿几个一合计,虽说家里总有人,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院里养只狗也好,咱这么多家,一家给口吃的就喂了。你奶奶就对狗说,那你跟着我们走吧。狗轻轻摇摇尾巴,一路跟到家。院里在家的人都出来看,说这狗看着挺仁义的,就是一只眼不太好,估计是赶上什么事,被打伤了。
这大黄狗真是好狗。一是护家。它心里有数,是你奶奶她们娘儿几个把它带回来的,院里几家,它都给照看着,打它来了,院里草刺儿都没丢过。天一黑,它就守着院门口一趴,再不出去,没有院里人招呼着,外人晚上别想进门。二是有规矩。不该吃的,没人看着,也不偷一口嘴,从不祸祸人,晚上还不吵。不像前街王老六家的灰狗,天气热时,家里人在院里吃饭。摆上小地桌,女人刚把盛饽饽的浅子放桌上,进屋拿筷子工夫,他家灰狗叼块儿饽饽就跑。晚上街道上走过个人,灰狗先狂叫个没完,给自己壮胆,把累了一天的主人从梦里吵醒。乡村养狗,好狗坏狗,就打这两下里分。时间长了,院里人都打心里喜爱这大黄狗。
那年冬天,咱家东边的赵家失了一次火。他家的两间西厢房和咱的东厢房背靠背,存放粮食农具,也放柴火,防着阴天下雨的。咱家的两间东厢房,那时刚住进聋大姐,是你二爷家的大闺女,小时候得病,把耳朵弄坏了,出嫁后生了个小闺女,那姐夫被抓兵了,她在婆家日子难过,带着两岁多点的闺女回了娘家。二奶奶早没了,你二爷在天津做白铁活,不总在家,她娘俩回来后,就住这两间东厢房了。
冬天黑得早,夜长,赵家的两个半大小子睡觉前饿了,看爹妈都睡着了,俩人一嘀咕,偷偷上西厢房,从炕上靠窗户堆着的粮食口袋里掏出些棒子粒,点着点儿木头,烤棒子花吃。两人吃得高兴,吃完溜回正房睡觉,没想到木头还有余火,时间长了,把旁边的柴火引着了。那时房顶都是木头檩条上搭苇笆,苇笆上再抹泥的,火一蹿起来,就把房顶引着了。
咱院里人是被大黄狗惊醒的。夜里从不乱叫的大黄狗,大半夜叫得像人吼似的急迫不说,还跑到你爷爷奶奶门前,不停地挠门。这狗从来家,就知道你爷爷奶奶是这院里的主心骨。你爷爷奶奶惊醒后感觉不对,赶紧开门出来,才发现:赵家西厢房顶见火光了。
你爷爷赶紧喊,着火了!快起来救火!边喊边拿了水桶,跑回屋,用瓢从水缸里舀了水往桶里倒。那时不像现在有自来水,平时各家吃水,都是上村东南角的井上去挑。日子富裕的人家,有水缸有水桶,像咱那院里,就是一副水桶,大伙轮着使,有的人家没水缸,用个水瓮,也有两家使一缸水的。
院里人都起来了,男人们赶紧拿梯子凳子,上墙上房,赵家两口子也惊起来了,附近邻居也有听见动静起来的,一起忙着救火。冬天风干物燥,赵家这屋里粮食柴火的又有点多,火着得大,人们用盆子水桶从缸里弄水,哪跟得上火的势头,虽说有人开始去井上挑水,终归远水难救近火,赵家的两间厢房烧得落了挂不说,咱家的东厢房也跟着遭了殃,后墙烧塌了,火扑灭后,房顶也塌下来一大半。
那,聋大姐她们呢?我脱口而出。
是呀,父亲说。忙着救火,加上聋大姐回来没两天,一时都没想起来,咱这东厢房还住着耳背的她和小闺女。你爷爷想起来时,头嗡就大了。顾不得危险,赶紧冲进东厢房,没见到人!再冲出来,喊谁看见聋大姐她们了?黑地里听见你奶奶说,在咱这呢。你爷爷赶紧过去,见屋里掌着灯,聋大姐搂着小闺女在炕上。你奶奶说是大黄狗把你爷爷他们叫起来后,竟跑去挤开东厢房的门,叼着聋大姐衣服往外拉,把聋大姐闹醒了。她不知怎么回事,大黄狗一个劲儿拉她,出来一看,原来是后墙紧挨着的赵家厢房着火了,赶紧进去抱闺女出来,大黄狗引着她们,上你奶奶这屋来了。
谢天谢地!我心有余悸地说。
累了半宿的人们回屋睡觉去了,父亲接着说,没想到,第二天天刚亮,就被东边赵家院里女人和孩子的嚎哭声惊醒了。又怎么了这是?人们过去看,原来,烧得落了架的赵家西厢房里,一地都是烧爆的棒子花!夜里黑麻乎眼看不清,心存侥幸、想着还能剩点粮食的赵家女人天一亮就赶紧起来,出来一看,西厢房炕上堆的几口袋棒子粒,全都变成了棒子花,忍不住号啕大哭。赵家男人拷问之下,知道是俩小子昨晚烤棒子花吃造的孽,气得暴跳如雷,抄起根棍子就打。女人又赶紧护着,替孩子们挨了两棍子,大人喊孩子哭的,闹哄成一锅粥。
爷爷他们赶紧上前拉劝。有刚起来还不知道失火的邻居,听说昨夜经过,都感到心惊后怕。有人劝老赵,你就认便宜吧,得亏有人家大黄狗,要不火烧连营不说,闹不好出人命呢!老赵扔下棍子,恨恨地说,你们这俩败家玩意,还不如人家大黄呢。
这次救火救人后,周围人都知道这大黄狗的仁义了。下的第一窝小狗,刚能离身,就被街坊四邻亲戚朋友要走了。第二窝下了十一只,还都吃着奶。其中一只小狗,一身黑,只有尾巴尖是白的,看着最机灵。当时我七八岁,最爱这小黑狗,早跟你爷爷奶奶说了,这小黑狗不能给人,我要自己养着。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后院,去看这白尾巴尖小黑狗。你爷爷他们把大黄狗和小狗们安置在后院一间搁东西的棚子里。后院不大,就是正房后面一块地儿,没有院墙,从边上的土坡下去,走不多远,就是通西边村子的土道。前院西北角那有个后门,通着后院,白天打开,晚上睡觉前关上。
那天下午,天还没见黑,大黄狗就把小狗一只一只往前院叼,等你奶奶她们注意到,十一只小狗,都在大黄狗生小狗前常卧着的大院南门口那了。这块的狗窝小,盛不下这么多小狗。你奶奶她们就说,这狗,你怎么把小狗都弄院里来啦?大黄狗不作声。怕这么多小狗夜里在地上冷,院里人把小狗又给抱回后院,大黄狗一声不响地跟着。院里人回屋了,没一会儿,大黄狗又把小狗叼回前院来了。你奶奶她们有点生气,说这狗怎么回事?好好的后院棚子里,都铺好东西了,你老把小狗叼进院里来干什么?又都给抱了回去。我那时小,看着大黄狗一次次把小狗往院里叼,说不出心里什么感觉,就是心疼,恨不得让它们在院里待着,但这种时候,小孩的话没人听。眼看着大黄狗耷拉着脑袋,跟着它的小狗们回了后院。天要黑了,为防备它再把小狗叼回来,你爷爷他们把后门关好拴上了。
夜深了,大人孩子都睡实了。突然,炸了营一样的狗叫声把我惊醒了,一看,你爷爷奶奶也都醒了,正趴在窗户那听。从房后面土道上传来的,一听就不是正常狗的叫声,引得村里的狗都在狂叫。那时兵荒马乱,卫生也差,有的饿狗,不定在野地里吃了什么,就不正常了,经常闹疯狗。疯狗眼神直直的瘆人,伸着红舌头,流着哈喇子,特别吓人。被疯狗咬了是能要命的,见了疯狗,没人敢上前,何况现在是黑夜。你爷爷奶奶这才知道,原来错怪大黄狗了。狗是有灵性的,它们总是耳朵着地卧着,能听出很远的动静,大黄狗应该是听出了远处疯狗的动静,傍晚才把小狗往院里叼。你爷爷奶奶把肠子都悔青了,可除了干着急,盼着疯狗快过去,一点办法也没有。
疯狗声越来越近,很快,后院狗叫声响成一片。有疯狗的叫声,有大黄狗的叫声,有嫩声嫩气的小奶狗们的叫声。昏暗的油灯光在一间间屋里亮起来,院里人都醒了,但谁也不敢开了后门出去。你爷爷急得在地上转磨磨,听着是大黄狗和疯狗掐起来了,想上院里去,又怕让大黄狗分了神吃亏,只能悬着心,支棱耳朵听。村里别的狗这时倒安静下来了,只听见咱们家后院里,大黄狗和疯狗豁了命一般的吠叫撕咬声。
渐渐地,后院狗叫声平息了。不远的郝镇街里,狗开始叫成一片,你爷爷说,疯狗又往镇里去了。
天刚一见亮,你爷爷赶紧去开了后门,院里人都跑后院来了,急忙奔棚子那去看。只见大黄狗趴在地上,浑身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我那是第一次看到狗会流眼泪。被疯狗咬死的小狗,横七竖八,在大黄狗身边倒了一地。别说你奶奶她们娘儿几个,连你爷爷他们都心疼得直掉泪。
我最着急的,是找我要留的白尾巴尖的小黑狗。找了半天,那一地小狗里却没有。再一数,被咬死的小狗只有十只,少了的一只,正是我要留的小黑狗。它哪去了呢?我转着磨磨找,忽然发现,棚子里码着的土坯垛空隙里,小白尾巴尖在轻轻晃动!原来,小黑狗钻进了土坯垛空隙里,保住了性命。它可太机灵了!我喜出望外,赶紧擦干眼泪,让你爷爷他们把土坯慢慢搬开,把完好无损的小黑狗抱了出来。
那,后来呢?我问父亲。
后来,你爷爷他们赶紧上镇上同仁堂药店,买一种叫斑蝥的中药,捣碎了,和掰碎的馒头一起放粥里拌匀了,喂大黄狗吃。那年月,平常日子,谁舍得拿馒头和粥喂狗?你奶奶她们心疼它,也是觉得对它有愧呀!它嘴边都被咬破了,几乎吃不了食,勉强着吃了给它弄的馒头和药,总算保住了一条命。院里人都说,这大黄狗真是太好了,这回治好了,得把它养到老。虽然过了很长时间,大黄狗才恢复起来,但还是忠心耿耿地和小黑狗一起看家,直到老死。小黑狗和它妈妈一样,又仁义又护家,谁见了都夸。小黑狗老死以后,我把它埋在了后院坡下,就是当初你爷爷埋大黄狗的地方。俗话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真是不假呀!
听完父亲的讲述,一个久违的日语单词忽然蹦出我的脑海。
我说,爸,您知道狗在日语里怎么说吗?
父亲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让我想起父亲以前讲过的一些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何况父亲是长子。他十三四岁,就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了。那时日本人已占领华北,并在我们家乡附近修了机场。他们的飞机常低空盘旋,郝镇东面有个村子,一个老太太上院里抱柴火,准备做午饭,被飞机里的日本兵开枪打死了。消息传开,附近老百姓一见日本人飞机飞过来,就都留着心。那天父亲正在棉花地干活,一看有飞机低飞过来,心知不好,赶紧趴进棉花垄里。靠棉花茂密的枝杈和叶子保护,飞机上扫射的一梭子子弹没打到他。这件事以后,爷爷托亲戚找门路,把他送到天津一家洋酒行学买卖,从最底层“跑街的”干起。有一次,日本人在海河东面的一个火柴厂着火了,他们认为是中国人干的。海河桥头,端着大枪、刺刀向前的日本兵把在两边,对过来的中国人搜身,只要搜出火柴,立马挑了扔海河里,附近的河水变成了红色,被挑的人在桥下越堆越多,海河几乎在这断流。我以前的单位刚合资时,日本的管理和技术,日本人鞠躬点头的礼貌客气,让我在父亲跟前说起时流露出赞赏语气,父亲当时很不以为然,说你太年轻了,知道什么。上面这些事,就是当时父亲讲给我的。
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冒失。旁边正好有纸笔,为缓解尴尬,我拿起笔,写了“义奴”两个字,又写了日语“狗”的平假名“いぬ”,对父亲说,日语的狗,念起来就是“义奴”这两个字,平声,“yīnū”,用日语的平假名写出来,跟汉字的“义奴”两个字也差不多,大概是当年来唐朝的遣唐使,学习汉字后带回去,又改良出来的。日语里,平假名差不多都这么来的。也有和汉字形状一样的,但发音和意思,已经和汉语相差很远,比如“邪魔”,我在纸上写下“邪魔”两个字,说,日语发音是“加麻”,意思是“打扰”,这种情况很多。
父亲点点头。忽然问,那,日语的猫怎么说呢?
我一愣,没想到老人又给我提问了。幸好当年培训时,感觉狗和猫这两个日语单词发音有趣,所以让我时隔多年,还没把这两个词还给老师。
我又在纸上写下日语“猫”的平假名“ねこ”,对父亲说,这是日语里的“猫”,发音是“耐寇”。说完就想,父亲可能要当作“爱寇”来理解吧,因为家乡人尤其是老一辈人,总是要把“爱”说成“耐”,比如夸小孩真惹人疼爱,就会说:“这孩子真耐人儿。”
当年还有个小插曲:一起参加日语培训的调皮鬼小汪,在我那次请客吃饭时,说他给一个男同事起了个“耐寇”的外号。我问为啥?小汪笑着说,我一直以为他脸涩,不会笑,后来才发现,他在日方管理者面前,笑得不要太妩媚了。听他这一说,让我想起张爱玲在小说《半生缘》里,形容做投机生意的祝鸿才,“笑起来像猫,不笑像老鼠”,当时就忍俊不禁,差点喷饭,一下子也把“耐寇”这词记牢了。听说“耐寇”后来成了公司高层,不过那是日方独资以后的事了。
听我讲完日语猫的说法,父亲笑了,说,义奴,耐(爱)寇,日本人对狗和猫的这叫法,还真是对呢!
南北萍,女,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写作,作品散见于《中国文化报》《天津日报》《今晚报》《文学自由谈》《文学界》《天津文学》等报刊,2012年出版文集《生命与行走》。
责任编辑:艾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