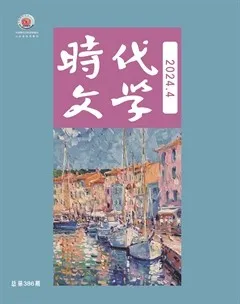西非已昔
一
在乔安去世很多年后,林隐一直想去一趟西非。
去瞧瞧他埋葬的地方,看是否安静质朴;去走走他生前曾走过的路,看是否灯火缭乱;去他喝过酒的酒馆坐坐,看是否迷离摇曳——林隐还无数次想象过,走过那些地方,或许能在某一路口、某个拐角,看到他搂着异国的女子向她走过来,微笑也好,炫耀也好。
当然,那些都是她的想象而已。
她始终没去西非。为什么终未能成行?时间?金钱?勇气……统统不是。
因为林隐实在没有什么很好的身份,即便是想作为乔安的前女友,似乎也远远算不上。乔安去西非之前,林隐被临时抽调到这个小城监管一个项目,初来乍到水土不服,工作压力大且心情不佳,牙疼得连口水都不愿喝。后来,她疼痛难忍,在朋友的推荐下,去乔安的医院里拔了两颗智齿。
乔安特意安排了一下,两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医生对着片子研究了几句,然后俩人围着林隐三下五除二就把牙给敲下来了。因为工作人员不肯收费,林隐就去乔安的办公室面谢一下,正好听见他在问医生:“林隐,男的女的?”
“女的。”她站在高高大大的医生身后回答他,因为打了麻药的缘故,说话不太灵光,听起来像是在说:“吕的”。
他轻轻探身看见林隐,她嘴角还有血丝尚未擦净,脸上尚有劫后余生的慌张,他忍不住笑着起身和她握手说:“快坐下来休息一下,这拔牙肯定把你吓一跳。”
乔安的办公室不大,空间狭长。林隐顾不上客气,大步流星走过去,长长吐了口气,一屁股直接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有南方商人的标配——林林总总的各色茶具,一眼看过去净是尘埃,显然不曾被细心打理过。乔安随林隐坐下,安慰她:“拔智齿最遭罪了。”他取了一个纸杯放在她的面前,“放心,过几天就没事了。忍忍,多喝水,少说话。”
“主要是也说不清楚了。”林隐咬着牙,话说得含糊不清。她脸上强作平静,明显是忍着刚经历的心惊胆战,乔安知道,拔牙真真把她吓着了。
这样一想,乔安忍不住又笑了,指指自己的牙说:“拔牙其实不疼,就是过程煎熬了些。我这儿也有一个,牙根太深,也得攒攒胆子再解决。”他安慰着。几乎同时,两人的电话响起;几乎同时,各自去接电话。这边乔安微微侧着脸,看林隐讲着一口又轻又快的闽南话,有口无心做着应答;那边林隐倒是不见外,担心自己吐字不清,刻意提高声音,她埋着头、皱着眉、思量着、安排着,可能是说话有点儿费劲,忽然一歪头用脖子夹住电话,利落地从身后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啪”地放在桌子上翻开,再次俯下身子三下五除二画了一张图,并和对方一再确定:如果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大事儿,三天就能解决……乔安挂掉手中的电话,趁一个空档,赶紧递给林隐一个冰袋,拍拍沙发示意她坐着稍等自己一下,然后才放心起身,出门去接待来客。
那时是下午六点,乔安的办公室开着空调,暖风吹起了林隐的发丝,她说着话利落地伸手抚平,脸微微低着,神态认真专注,略肿的脸上每一个毛孔都熠熠生辉,显得落落大方。有些许阳光照进来,一直照在林隐的背后,安静地陪着她。过了许久,理完手中的事,林隐挂了电话,环顾四周无人,一下子就把身子肆意地靠在沙发上,伸伸懒腰,想着拔牙真是吓人,再加上麻醉剂的作用,这一靠下去,神经一松弛,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其间,乔安可能回来过,似乎轻手轻脚取了文件又出去了。一直以来,林隐总有这般模糊的印象,但又因它太过模糊以至于她无法确定。仅仅能确定的是,等她真正醒来,已是傍晚时分,外边太阳归山,倦鸟归林。
后来,就是在知道乔安去世之后,林隐极力去回想初次相见的点点滴滴,但那些记忆寥落、轻薄。人常常就是这样,往往是越回忆越模糊。林隐离开的时候,乔安并没有回来。她从他的办公室走出去,关上门,屋子里的空调吹着,落地窗很大,光线不暗,到处弥漫陈茶般寡淡的气息,隐约渗透着莫名的旖旎。
大概过了三四天,乔安突然打电话过来叮嘱林隐:“不要总冰敷了,可以适当热敷一下。”
林隐不胜感激,连声道谢,说:“好的,好的。谢您惦记,改天我得请您喝一杯。”
“不是常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晚,行不?”他问。
当时夕阳晚照,细碎、悠长,叫人难以忘记。如果,乔安还在世的话,关于这一天他必定会说:今日大雪,正是良辰,宜祈福、求姻缘。
据说,这个南方男人来苏苑之前,还有一份姻缘,在北方。
二
北方的青州,有座叫苏苑的小城,正是乔安和林隐相遇的地方。
小城在山上依势而建,蜿蜒曲折、安静古朴却又闭塞落后。没来这儿之前,这里何种何种不好早已知晓。但林隐的老领导、老父亲却执意要把她选调过来,不容她有任何异议。他没给林隐准备一场送行的酒会,没配备什么强大的团队,在外人看来就如同发配。直到林隐到了小城,老父亲才发来信息:这一辈子的路太长,你必须内心足够强大,强大到有这个人很好,没这个人也行。
林隐一字一字读着,看一遍关上手机,打开手机再重复看一遍,皱着眉抿着唇,心里如同装满了隔夜的茶水,凉,苦。是啊,一个30多岁的女人,着实不该让老父亲如此煞费苦心,气着、急着又忙不迭地维护着闺女的体面;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不是应该自动了断那来路不明的情感,披荆斩棘再次启程吗?
所以,这个冬天成了一个分水岭,林隐的过去和现在。“也好,这样也好。”林隐想着,暗自咬着牙,督促自己就此启程。
启程那天正是“小雪”,皇历上说大吉,宜远行、安床和开市。
迎接林隐的苏苑,安静又破败,一座城里一条街,一条街上一个红绿灯,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口音的“淘金客”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对,各路人马齐聚,这儿像英雄集结的龙门客栈;来来往往,这儿又像美国曾经蛮荒的西部——大家都自嘲是怀揣无数理想又寂寞无边的“过客”。只有乔安不这样说,他说这个小城朴实,真真切切地叫人心安,自己也没什么事业,不过就是一个打工的。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稍稍有点儿沙哑,南方口音倒是不太重。
“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过路的,有来时,有归期。”她笑着接他的话,往椅子上靠了一下身子,向寒凉的空气里轻轻吐了一个烟圈。
“不一样的。”他看见她随意放在桌上的工作胸卡,拿起来看,上边有林隐的工作照,努力微笑,目光谨慎,端着一股子自信满满的劲儿。他轻轻读着照片左边的字:“工程师,林隐。”他赏识地说,“看看,30多岁的工程师,你是正经来干事业的啊。”
林隐不置可否,淡淡地说:“小时候吧,跟着我爸去单位,看别人喊他林工林工的,觉得挺好!就想着,以后我最差也得混成这个样儿!”她说得不以为然。的确,这些年来,除了自己那份来路不明的爱情,林隐觉得自己一切尚可,拔个头筹向来不是难事儿,所以,无论说起学业还是工作,难免有遮不住的点点得意。
那时,她尚且不知,面前这个男人,多年来就是一辆车一个行李箱,随时准备着从一个地方再去另一个地方。
那时,她尚且不知,乔安的老板在西非淘金发家,钱多心思大,全国各地到处占地儿。老板在海南开酒店,乔安就去代管酒店;去东北开影楼,乔安就去学摄影管影楼;在加纳开护照代办公司,乔安就在西非各国替人跑腿办事儿。
现在呢?
现在,是智慧小城的建设时代,他就被安排过来打造一座互联网医院。“你看,我不过就是一个打工的。”他笑呵呵地说,做主为她点了鸡蛋羹,倒了一杯清茶。
林隐微笑,想说谢谢,没说出来,只能再报以一笑,把手随意搭在桌上,向乔安晃了一下手中的香烟,问道:“不介意吧?”
两杯热茶混着烟草的气息氤氲,在两人之间缭绕、盘旋。他望着她,良久,突然探了一下上身,自然而然地伸手把她手指间的香烟拿掉,说:“吸烟的时候,口腔内是一种负压的状态,这样就容易造成血凝块脱落而引起出血,甚至造成创口感染。所以,这个,拔牙以后三天内都不能吸烟。”他神色认真,说着把烟轻轻平放在旁边的烟灰缸上,任其慢慢自燃。
“我不吸烟。”乔安抬起头看着她说,“但并不介意。”他神态自然,如同同友人一般寒暄。
乔安离开小城的那天晚上,林隐从梦中醒来,突然就想起这一天,好像山里的风吹进来,把寒意带到了小城的上空,他们的房间骤然变得清冷无比。那时林隐心里还惦念着旧日的过往,心不在焉,不曾留意自己遗忘了香烟、胸卡,更不曾留意桌子上的餐具和美食。当然,她更不知道,当时的一时清欢,竟是对面男人所钟情的一切。
可是,是清欢一时,还是一世清欢?乔安还顾不上去好好琢磨。他也忙着,智慧医院的建设速度很快,不断有各路资本进来,口腔、妇科、医美齐头并进。乔安关于互联网运营的知识和技术着实有限,所以一旦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总是去向林隐求援,不管是硬件配置还是软件处理,林隐就是这个小城的“大拿”,这点不用怀疑。
“知道了,晚点儿会安排人过去。”每每林隐都会这样回复他。
果不其然,下班后,就会有年轻技术人员速速赶来,憨厚的北方小伙儿见面就说:“哥,我姐说不是大事儿。”“哥,我姐让今天晚上给您捋清楚!”“哥,我姐说……”小伙儿连夜加班的时候,林隐会提着大大的外卖袋子过来给自己的员工加餐,素面朝天,头发些许凌乱地收拢到耳后,灰色大衣紧束着腰带,一路轻盈地走上楼来,简直就是天边飘来的云朵。
她拒绝别人去接她手中的袋子,连连摆着手说:“我来放,我来摆。”就是这样,她似乎沉迷于摆放那些大大小小的快餐盒子,整齐有序地一一摆开,随后拍拍双手,头也不回地喊:“来,可劲儿造。”而后,她会走到电脑面前,一边从兜里拿出一个夹子,三两下把刘海捋上去,露着光洁的额头,一边将身体微微向前探着、研究着工作的进程,那神情认真、执着,仿佛万般笃定。
乔安呢?
乔安轻易不会走进来,工作中的林隐自律,严苛,不喜有人打扰。所以,他就开着办公室的门,透过会议室的玻璃看她工作,她的眼睛紧盯屏幕时,脖子不由自主地向前伸,瞪着眼睛,拧着眉头,姿势大大咧咧的,不怎么优雅,神色倒是颇为认真。
林隐从来不吃那些宵夜,偶尔喝杯咖啡或者茶,吸着烟。其实也不对,林隐根本不怎么吸烟,不过就是爱随时随地手里拿着一支烟,如同握着一粒救命的药丸。有时乔安送她下楼,一到门口,她就会停下来,低头先点上一支烟。他们常常走着回去,一路上那烟在林隐的指间燃烧,深邃、慵懒、温婉。不期而遇,来日可期,不言而喻,如约而至——这些世间的美好,乔安曾几度觉得可能真的会突然来临。
当然,关于这些,林隐都从未知晓。
三
的确,那些,林隐都从未知晓。
她没那个时间和心情,她忙碌而努力,一心想着把工作铺排满当,想尽办法远离那曾经不舍的过往。小城冬夜常常雾气氤氲,清冷且潮湿。林隐尽量试着喜欢这里,成年人的世界里,即便失望也是淡淡的那种,毕竟那种风里狂奔、雨中狂喊的痛哭流涕不过是电视剧糊弄那些年轻人的。所以,忙碌之余,她努力让自己愿意和乔安沿着古巷老街的石板路慢慢走,走过望月门、山间会馆、老宗祠、小书院……有那么一次,在书院门口,林隐看到石桌上的喷水鱼洗,把手中的烟交给乔安,搓搓双手放在嘴边哈了一口气,然后将手掠过水面,再把手放在铜把手上摩擦,盆内水波荡漾,瞬间又水花四溅飞起。林隐则微微昂起头,笑出了声,朗朗笑声穿过午夜的老街,飘着飘着,久久回荡。
忽而,小有得意,林隐回望身边的乔安,他一手替自己拿着烟,一手自然垂下来,目光穿过淡淡的烟气看过来。也许是夜太深,也许离得太近,那对视的目光中分明有种许久未见的款款情深,入骨,入髓。
又迎小年到,人间小团圆。小年夜来了,一时兴起,林隐想去逛逛小城的午夜集市。长街上,集市正热闹。林隐点上一支烟,裹紧大衣,兴趣盎然地走过那些各具特色的小摊儿,那些新疆的大枣、陕西的苹果、景德镇的瓷器……它们都带着浓郁的地域气息,穿插在造型不同的大红灯笼中间,展现着辞旧迎新的欢喜。吆喝声此起彼伏,人群嘈杂又川流不息。但不管人群怎么拥挤,灯火怎么明暗不定,兴高采烈前来赴约的乔安一眼就看到了林隐。乔安大步走着,想着这是天赐良机啊,他想一路跑到林隐身边,轻轻搂住她的腰,自然而然地说:“这么好,喊我来过小年。”
可是,即将到达她身边时,乔安却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早他一步,一个男人已经来到。不必猜测,这男人还能是谁?无非就是林隐的爱而不得,无非就是林隐的朝思暮想。这男人身材奇高,手里捏着半支烟站在林隐面前,头稍微低着,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说话。
林隐呢?她微微抬着头平静应答,同时第一时间将手中的烟一下子全攥了起来,硬生地攥在手心里。那时,烟燃得正欢。
长街上通明的灯火照着他们,俩人自始至终保持着客气,都那么谦谦有礼。最后,林隐和旧爱没有不欢而散,他们在欢声笑语的集市里挥手告别。分别时,林隐也没赌气地表示并非非你不可,就是努力让自己微笑、再微笑,娇柔和平静交杂得恰到好处,没一点儿恋恋不舍的神态。
从始至终,林隐不曾发现,不远处的乔安双手无力地垂下去,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从始至终,她都暗自得意,因为一切深藏不露。似乎,她已经能掌控生活,生活给了一把比较体面的刀,自己已能手起刀落,尽管心里有万般不舍。
得意的那一刻,她不自觉地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环视四周,看见乔安那一瞬间,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所以说,那时的林隐还是年轻,不曾注意到乔安苍白的脸,更不知他内心正计较那些细枝末节:他们说了什么?到底说了什么?曾经的一餐还是一宿?过去的吵闹还是依恋……即便乔安知道,在自己之前,这个男人早已存在。
可是,爱来了挡也挡不住,无处可藏。
他们保持沉默,一路上忽快忽慢地走着。一离开拥挤的人群,乔安一把搂住林隐的腰,把她揽入怀中,然后急切而小心地掰开她的手指,拎出那支烟,直接甩了出去。
那天,回去的路上,他们没有再谈及这事儿。毕竟是两个成年人,面子工程得做得上台面。况且,乔安深知,有时候不说比说更能说明问题。倒是林隐在上楼之前,扭过头突然来了一句:“信不信?我不是算不清账的人。可是——”林隐突然就笑盈盈的了。她的眼睛不大但细长,笑的时候眯得弯弯的,干净又鲜活。
乔安措手不及,他低了一下头,躲开林隐的目光,人像突发了疟疾,心里忽冷忽热地胶着,难以名状。只有这一次,他接不住她的笑,也接不住她的话,放在林隐腰上的手轻轻地拍了一下,催促她上楼休息。
林隐在“可是”什么?
不言而喻,林隐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时间,来安置一下自己的过往。明知她需要时间,可这个男人的到来,又着实让乔安心里一哆嗦。男人再成熟,沉稳,到了这事儿上也逃不出忐忑的定律。实在没什么好办法,用大白话说这就是遭遇了该死的爱情吧。所以,乔安不知到底该如何是好,搓着手看着林隐上楼,心率加速,跳得七上八下,脑子里东想西想,以至于林隐上了楼,他才想起对着她的背影喊:“我明天飞西非,去加纳。我老板喊我过去,办完事很快就回来。等我啊。”
“又去淘金啊!”林隐听了,转过身来回道,“不错啊!”
楼道门口挂了迎接春节的红灯笼,偏偏那天灯泡坏了,一片幽暗,乔安根本看不清林隐的脸,只能听到她轻而快地说:“乔安,新年如意啊!”就这么一次,林隐喊着他的名字和他讲话,听得他一愣,却不知还能说什么。尽管万般纠结,但乔安还是得按照自己的行程出行。毕竟,生活不单单是风花雪月,吃喝拉撒都是必须,来日方长,速去速回,不过短短几天而已。
就是此时此刻,两个人来时的长街上,不知谁家的烟花腾空而起,如雨般迤逦铺叠、绽开,然后慢慢散落、散落……
四
多年以后,就是乔安去世多年以后,林隐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但她还清楚地记得乔安的西非。
关于西非,关于加纳,乔安和林隐说过一次,他喜欢加纳,喜欢那里的啤酒、音乐、舞蹈、黄金海岸和那些独特的生死观。
“我在加纳参加的第一个聚会,是个葬礼。他们的葬礼要请摄影师、调酒师、保安、化妆师、厨子等。死者亲属要请乐队伴奏,敲非洲鼓,为死者灵魂祈祷、跳舞和歌唱,那真是彻夜狂欢啊。他们说这是守灵,这样死者的灵魂才能快乐地前往另一个世界。对了,那儿有一句谚语说——人活一世,最后的奖励就是死亡。其实,也挺好,他们觉得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新的开始。”乔安说,那时他还年轻,还曾对同行的友人说,如果自己死了,也要举办一个这样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葬礼。
不想,一语成谶。
离开林隐的乔安,到达加纳的第二天死于一场金矿抢夺的混战。他躲过了出没无常的鳄鱼、到处乱窜的巨蛇,终究没有躲过突然而至的劫匪。据说,是矿上花重金请的保镖与当地的劫匪内外勾结,他们扛着枪一路杀来,一枪致命。乔安砰然倒地,没有遗言,捂了伤口的手摸摸索索地拿出了林隐的胸卡和一封手书,握住,尽力握住,以慰藉最后一口气息。
据说,他的葬礼没有家人出席,只是老板出钱请了当地的葬礼师完成,是否如他年轻时所说的那般热闹,是否有人为他跳舞歌唱,这些也无从可知。后来,乔安的一个小老乡整理他的遗物,按着那张胸卡标注的公司,一路查询到中国的总部、分公司、驻站工程办公室,最后终于查到林隐确有其人。所以,在乔安去世很多天之后,才有一封信从西非出发,漂洋过海寄到林隐工作的总部,再从集团总部发至分公司,而后辗转送到小城。那信到达林隐的办公桌上时,春天已经过去,小城的夏季正明媚。
夏至,将至未至。
林隐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外边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时而传来三两声清脆的鸟鸣。她丢下手中的笔,拿起信件小心剪开一张工作胸卡“啪”地滑落在桌上,她迟疑地伸出手拿起来,那上面的血迹已凝固良久,颜色黑红。她全身的神经一紧,迟疑了一下。没错,是自己丢失许久的那个胸卡。
是否,当初失意的林隐将胸卡遗落在餐厅?是否,乔安随后返回去找到就此私藏?是否,那一刻他就怀揣了隐秘又志在必得的情愫?遗憾的是,关于这些,已经早已无人可问上那么一句。
林隐再去翻看,还有一封没写完的手书,开头笔迹整齐,看得出相当认真和用心:
宝贝,老爸今天回加纳。大概三个月后我就能去美国看你,陪我宝贝过18岁生日!你一人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读书。在吃上不必节省,也不要减肥。我的宝贝马上要18岁了,肯定也会有很多男孩子来追。宝贝,你一定要记得。你内心要足够强大,强大到有这个人很好,没这个人也行。你要尽可能让自己优秀和独立,这样真正爱你的男人不会太差,因为他会考虑与你的人生势均力敌。宝贝,在苏苑,老爸就见过一个这样的姑娘,我看得出,她竭尽全力地让自己过得漂亮,尽可能地实现你们年轻人说的那种又美又飒。她说:一个人也要过得活色生香。是的,宝贝,虽然过日子要棋逢对手才有趣,可生活还需要你知道,如果没有合适的对手,自己也要过得活色生香……
林隐看着手中的信笺,明显有话未写完,字迹却越来越乱。她此时还不知道,信写到此处,乔安的飞机已经到达西非上空。而看到此处时,她不知道乔安其实并不愿提起这些,因为男人更愿意把喜欢的女人放在心灵深处,暗自窃喜。信写到此时,乔安满脑子都是林隐,细腰,薄肩,香烟,总是努力微笑的双眼……乔安的手有气无力地搭在自己额头,一想到林隐,他就好像没了脊梁,没了底气,笔在信笺上胡乱挣扎,以至于字迹越来越混乱。
没办法,林隐将信笺尽量凑近自己的脸一点点去辨识那些字,也一点点回想着,自己是在何时,又是在何地和乔安说过那些话。窗外,雨突然大了,远处的树木、房子开始模糊。她不得不起身去关窗,回头想想那些过往,稀疏又恍惚,竟未能留意狂风骤起裹着冷雨扑面而来,雨水拍在脸上,有些疼。对,对,是有那么一次。
林隐在长街的一家火锅店吃夜宵,恰巧乔安在楼上请人吃饭。送走客人,他不请自来,端着茶在林隐的对面坐下。他说:“这个热腾腾的锅和这满桌子的菜,你一个人看起来过得真是热闹。”
林隐看见他,笑了,赶紧放下手中的烟,说:“一个人也要过得活色生香,过日子不就得这样?”
那天的乔安似乎喝多了酒,话多,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拿走林隐面前的酒杯,把脸转向窗外,突然说了一句闽南话。林隐听不懂,但听清楚了一个“烟”字,她呼吸猛然停了一下,心像被猫抓了一把。
知道林隐没听清楚,乔安转过脸来看着她,用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说:“你喜欢抽烟,因为你怀念一个抽烟的男人。”
林隐的笑容凝固了,埋头去拿烟,手伸得太快,手指一下子就碰到了燃烧的烟头。没办法,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无法掩饰,咳嗽和爱情。的确如此,离开迷恋多年的男人后,林隐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夜,桌上总是堆满东西,凌乱、拥挤,笔记本电脑、断铅的铅笔、没电的台灯、喝水的杯子、挂耳的咖啡、开封的茶叶和挂在椅子靠背上的耳麦,统统都带着油腻的手印,一看就是主人没心情来好好打理……怎样才能回到最初?她曾反反复复地想,就是想不明白。为了能够让自己平复下来,她允许自己抽烟。可是,关于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始终都不曾找到答案。
是的,她特怀念一个抽烟的男人。
即便乔安这样说出来,林隐倒也不想去否认。
其实也不是YuF7uV1TR7wegrur6XBzjw==不想否认,只是那刻,她连否认的力气还没攒好。只能埋头无声地继续大口吃饭,努力拦着眼泪,不想它们落在面前的盘子里,纵然心有万千沟壑。
“过日子嘛,总有些磕磕绊绊。”乔安转开脸,不看她,继续说,“你看,那边。”他指着楼下街上做姜糖的夫妇,“其实日子能过成他们这样,平常夫妻,相依为命,也是种造化。”
林隐看着那夫妇,男的在案头埋头揉、搓、撵、压熬好的姜糖,他弓起来的身体像个大虾,心无旁骛,高高起身,重重落下,双臂似乎将全身力量都揉了进去。而他一旁的女人一只手抱着个暖水袋,另一只手不紧不慢地往盒子里摆放着切好的姜糖,一块两块,一排两排——“您这话说得,好像我家老爷子。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想的?”林隐伸手去拂了一把玻璃上的雾气,那时她对面前的乔安尚且无所知,不知他在妻子去世后曾酗酒好几年,可是,后来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养活自己和闺女。
“因为见过生死,明白得失,接受因果,知道生活是个什么东西。”乔安认真地回答,“姑娘,人这一辈子这么长,即便失去点儿什么也是正常。是不是?还有,以后,人生和阅历会告诉你,那些难过不会突然消失。吃喝拉撒会告诉你,生活事无巨细,你只能一个人去一一承担。比如生病了,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坐在那里打吊瓶,眼睁睁地看着瓶子里的液体何时能滴完。这样的难过得需要多长时间结束,取决于你调和所有事情的能力,包括与对待生死别离、至爱的人及情感幸福的定义。”
他的回答,过于认真,着实在林隐意料之外,她甚至不知话题该如何继续,只能微微抬头报以赞许的一笑。却不知,那一笑,不过是强作的欢颜。乃至,乔安在离世前,想到林隐的悲喜,就会焦虑、无措。在这世间,有人可以替你吃苦受累,有人愿意替你翻山越岭,但就是无法替你爱恨悲欢。可惜啊,这些,林隐并不知道。
林隐还不知道,乔安在离世的那一刻,一遍遍回想自己这个醉酒的夜晚。他第一次陪着她走过长长的老街,一路走过望月门、山间会馆、老宗祠、小书院……那真是个令人沉醉的夜晚啊。的确是有那样的一个夜晚,林隐终于想起来,酒醉的乔安走在自己左手边,突然说:“听话,林隐,把烟戒了。”
她很意外,转脸看看他,眼里带着疑问。
乔安向林隐迈近了一大步,伸手拿了她手中的半支烟,俯身凑近她的耳旁用闽南语飞快地说了一句话。林隐侧耳认真去听,根本听不懂。乔安离得她太近,浓烈的酒气和恍惚的目光让她心一软,慌不择路的她向后退了一步,胡乱回应着:“这么大的事儿,得容我想想。”
“真的?”他追问,轻轻吐了一口气,语气里有显而易见的急切。
“真的。”她说。
五
多年以后,就是乔安离世多年以后的一个夜晚,林隐陪着新婚的爱人参加一个聚会。席间,一男子突然把一个女孩唇边的香烟抢了过去,嗔怪发狠地说了一句闽南话。
坐在女孩身边的林隐听到了,突然心一疼。
那句话,曾几何时,她一定听过,尽管她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问:“他说什么?”
女孩任性又娇羞地一笑,用普通话在她耳边回道:“他啊,他说他家不让娶抽烟的女人。”
林隐右手抚在心口,努力呼吸,左手拿着酒杯起身,走出去。是,她得在眼泪流出来之前,走到阳台上去。身后,酒桌上的人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吵闹嬉笑,并没人注意她,包括她的爱人。
一朝一夕一刹那,情像雨点,似断难断。
有谁知道?
那句话可以永远不懂,可以一直高高搁置,但那就是林隐生命的一部分。
有谁知道?
尽管生活在继续,一切依旧活色生香,但能与乔安相见,仍是一个心愿。
阳台下,是那条刚刚翻新过的长街,急匆匆回家的自行车铃声从这头一直传到那头,悠悠不断;不远处的集市正热闹,架子鼓跟黄梅小调搅在一起,从那头一直传到这头,忽而抑扬顿挫,铿锵动听,忽而款款情深,幽怨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