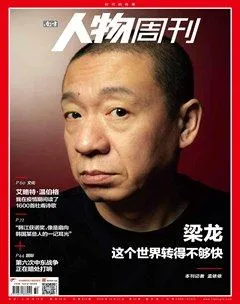出什么道,我们就出来混

人:人物周刊 梁:梁龙
咱们不就还落个仗义嘛
人:“摇滚运动会”最后办成了吗?
梁:我们北方的线演完之后资方就撤资了。当时还能拉到投资,三百多(万)吧,我全给他们结了,咱们不就还落个仗义嘛,我也没要求任何一个乐队给一个友情价。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聚会,也萌生了我后来做《艺术唱片》。因为在“摇滚运动会”开幕式结束的时候,大概有十几支乐队,我们在一个小花园里一块儿聚餐。我觉得大家都过来一块儿玩,挺开心就好了。这时候CMCB乐队的主唱鸥子说,龙,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我说怎么的?他说,你说大家为什么这么高兴?我不知道。他说这样的聚会有些年没有过了。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认知改变了,还是说真的像我所说这些年的摇滚乐事件、浪花一样的东西少了。对,我的画面就是,浪花越来越少,这鱼也蹦不上去。
以前有新乡摇滚音乐节,早些年还有个词叫“摇滚专列”,一群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要看他们最喜欢的音乐现场、最喜欢的乐队,包括贺兰山音乐节、雪山音乐节,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会背着一辈子的一些有趣的音乐事件。就是这样的东西,是支撑着我们内心走了很久的东西。
人:做那些项目的时候你不管账,不担心出问题吗?
梁:不说结果的话,我觉得做事的习惯到现在我还是要跟一个人合作,就得信任他。即便是遍体鳞伤,即便大家会有误解,我从来不认为这个世界上错只在一个人。大家有纯粹的那个时光,就很好了,那只是没做好嘛。
(目的不纯的人)肯定有。但我保证我们这个初始者能纯点就行了。如果我自己的心态不够纯粹,我怎么去跟人家一块儿探讨纯粹的事,对吧?
人:像“摇滚运动会”、《艺术唱片》最后没有做下去或者效果不尽如人意,但那几年你还是在不停发起项目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梁:很多时候音乐是挺无能的,在很多人的世界里面,它只是声音。其实很多音乐不只是音乐,音乐是载体,它表达的力量非常庞大,或者非常抽象,甚至非常先锋,会给人很多的不同的情趣。所以我一直希望,能把这样有价值或者有力量的音乐在另一个维度上进行解读。
我之前讲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年去德国参加世界音乐节,我去买德国战车的专辑,在摇滚乐那栏儿挑了半天没挑出来,最后一问,人说在古典乐里边。我到现在也说不清这些,我个人起码认为有力量的音乐让它有一个该属于它的货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是最好,但觉得应该做这样的事,要不然音乐好像只是你手机里的MP3,我知道,当然不仅仅是。
人:你现在会想起前几年做的那些事情吗?
梁:不会特别故意,但你说看到摇滚火锅,能不想这件事吗?路过798,看到那个已经物是人非的店,你不想吗?不可能的。甚至在我们家里开过会的所有的朋友,现在天各一方,甚至有的不联系了,你不想当时你们共同奋战过吗?那种起出了“如你所愿”的名字高兴得直击掌,那怎么可能去忘。
而且没必要去忘,无论结果怎么样,过程的一刹那,记住它就好了。

我想保留原始的冲动
人:当你发现你的听众在发生变化时,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梁:没有。唯一影响我的创作的就是精力不够我就写不出来。创作是没有办法随波逐流,即便你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你能写得出来吗?或者,你为什么要写一个年轻人想要的呢?我觉得都没必要。其实是此情此景下你看到了什么,按你的表达去写就好了。
人:你的创作习惯是什么样的?比如很多创作者会保持一个日常练习,像锻炼肌肉一样。
梁:我的创作没有肌肉记忆。(笑)我不练琴,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讲,练琴是对创作最大的伤害。我也爬不了格子,到现在为止我几乎没有一场演出是按一个标准把我的琴弹完整的、没有错的,到现在为止。所以我觉得“就不刻苦”,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方式,我不是那种典型的刻苦的路线,也算给自己找个理由。
人:那就要对自己感受的东西更自信是吗?
梁:所以风险很大。我不敢说全是情绪,但是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我想保留这种原始的冲动,它是双刃剑,如果过于精细、专业的话,原始的冲动也不存在,但如果只靠冲动,那可能也只是个冲动,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控。
人:近几年的创作里,无论是专辑《冰城之夏》,还是专场演出“小野练歌房”、“龙门秀”,包括电影《大命》,都是带点回顾式的、私人的、内向的,为什么这个阶段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梁:我一点也不规避,这可能就是四十多岁的我,对故乡这个土地的新的情感。它可能是来自于所谓的离别的眷恋,也可能是出走了二十多年之后的新东西。它不是多新鲜,但在这个时候我需要跟自己、跟这个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有这样的对话。那天我们聊到说“小野练歌房”意味着什么,导演也这么问我,我说我现在回答不了你。过了几天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是自己和另一个自己一场有预谋的谈判吧。
我不知道目的,就要去做这个事儿。
人:也是一种,感受先行?
梁:现在可以回答你了,在此时此刻,我可能想通了。可能这种回顾就是为了出走,再次出走。只有当你出走了很多年、突然开始回顾的时候,才能更明确再次出走的意义。
人:在这种回顾和出走、现在和过去的交叠过程里,你会反观自己的成长过程吗?比如越来越多受专业音乐教育或者从小接触到非常丰富的音乐的年轻人出现,你会觉得自己原先的基础并不牢固,甚至成为创作的限制吗?
梁:也分时代。我们那个时代上学的也不一定比不上学的强。我在齐齐哈尔搞乐队的时候,有个女孩过来帮忙弹键盘,就见过那么一面,弹了一半就搁那深沉地发呆。我说咋的?她说我从小到大弹钢琴,弹到现在,所有大曲我都会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应该去创作。
但像现在这种多元的音乐教育,我当然嫉妒啦。如果我曾经有这样的机会,当然希望是这样的。但我们那个年代,在小城市,从小到大没一个老师聊创作,也没啥太大意义。
人:后来你接触到了更多音乐种类,有像学摇滚那样去学吗?
梁:从来没干过。你要看哪个报道这样说,肯定是假的。你问我爵士、蓝调,我真不懂。
前两天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大家选的歌是个摇滚乐队的歌,其他人都不是搞乐队的,他们就问我说,梁龙,到底摇滚是个啥?我就说了一个最基础的感受,对于摇滚乐的唱法,可能“不修饰”是它的表达方式之一。他们的经验里没有这个概念。然后有一天呢我给队友听赵老大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因为他喝多了,琴弦也不准,说话都费劲,有气无力地在那唱歌,每次我一听都想落泪。那个录音我十年前第一次听,在我家厨房,特别清楚,我听完之后把厨房门关上,把啤酒拿出来蹲在地上一直喝了10瓶。但有些人就会无感。但难道是那个哥们不懂音乐吗?还是说赵老大真的唱得一塌糊涂?都不是的,其实是我们都没有过对音乐真正的学习和阅读,所以我们有很强的壁垒。
这个也不能全推给教育,多元文化的普及未必在教室里,它是一个社会多元的推介,只有多元的推介,大家才能理解更多,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再选择他认为有趣的。但是现在说实话,让我一个可能也算从业者,稍微还是有点难过的,我觉得现在还是偏单一,比我们那个年代丰富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开心就玩,难过就走吧
人:二手玫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梁:我们走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节点,每个人生活变化太明显了,对接下来的一些音乐表达分歧比较大。
比如像鼓手孙权,觉得摇滚乐就是那种不变,一个劲玩到底,没错。姚澜偏创新派,休假前觉得还是要多变一点,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不能有断层,我们毕竟是一个舞台上的动物,不能在情绪的自嗨里。或者有人觉得,活着就得吃好点穿好点,这都很正常。
这时候其实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果我们还想去把二手玫瑰继续玩的话,那什么是我们现在大家觉得又有价值、又都认可的东西,这很重要。
人:所以可能这个阶段大家能缓一缓,想一想……
梁:不是个坏事。因为对外从来没说过,那天我在北京演“小野练歌房”,一个老朋友来,我们聊,他说梁龙刚才你在台上说的无论是姚澜需要休息,还是乐队之前的成长经历,都对,姚澜需要休息,说明他认知上出现了疲惫,休息是好事。孙权怎么办呢?就主动给他一些节奏,让他听一些东西,告诉他你现在生活已经固化了。
人:做了这么多年乐队,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来维持它、让大家一起走下去,你觉得是什么呢?
梁:可能昨天我还在鼓励年轻人你们要怎么团结,怎么坚持下去,但今天我不鼓励,维系也好什么也好,都没必要,实话实说,这就特别容易僵化。开心就玩,难过就走吧。
大家都觉得二手老顺利了,现在小孩叫“出道”,我们出什么道,我们就出来混,说我们2000年到北京,2003年就北展做个唱,一路都辉煌这那个的。我说拉倒吧,哪有那么好的日子。
说到现在,我希望大家变得更放松。忙完这段之后,无论是我要开始自己的电影,更实验、更主观化一点,还是乐队开始真正向市场推介“龙门秀”,大家就放松地去玩。你们调整好你们的心态,我调整好我的节奏,尽可能彼此不打扰太多。既然我们都知道目前乐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大家把它呵护好。
人:2023年《乐夏》之后你说并不想做馆级演唱会,那时候乐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梁:就是忙忙叨叨的,上《乐夏》都这样,在市场上得到一些放大,大家可能接触到一些之前没有的生活,比如拍杂志、参加盛典,我们又接了广告,什么二手电器。乐队的情绪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方面觉得很新鲜很过瘾,恨不得多拍才好呢,另外一半可能太疲乏,如果再这么下去,会不会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乐队该做的事?
但我没觉得严肃到得去博弈的状态,远不及。说实话,我也知道不会一直是那个节奏,火一段就拉倒。忙过那半年就没广告了,现在还有吗?是不是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