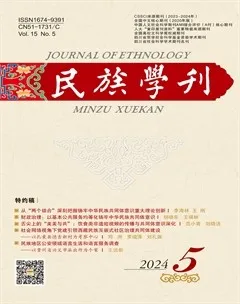从“两个结合”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理论创新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赋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是“两个结合”的典范。一方面,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分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这个“中国具体实际”,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从根源上讲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性和客观实在性。既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也避免陷入三重“困境”,即共同体理论唯心史观窠臼困境、“只讲民族之分,不讲民族之融;只讲差异性,不讲共同性”困境和“为少数人服务”困境。另一方面,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的活力和魅力。
[关键词]
“两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4)05-0001-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重要论断,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予以系统论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14-15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2]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结合”是从整体上关乎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的一个重大论断;[3]“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延伸和拓展,是“第一个结合”发展的必然结论。[4]
目前学界关于“两个结合”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截至2024年2月14日,在中国知网搜索主题“两个结合”并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章共有10条记录;主题“两个结合”并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章共有12条记录。金刚、哈正利认为“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阐述“两个结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5]周鹏、王晓森从马克思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两个结合”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严庆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注利益,有助于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6]邹诗鹏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辩证的观点以及实践的观点有益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7]尹茵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q9AZXMF7AwsZLH1xEXchYA==源泉和价值归旨。[8]
总体而言,目前从“两个结合”的角度综合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有很深的拓展空间,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宏阔视野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笔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结合”的典范,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底色,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可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宏阔理论视野深刻洞察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体现“第一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这体现“第二个结合”。
一、第一个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分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
(一)辩证唯物主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1.世界物质统一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以世界物质统一性作为理论基石。
首先,世界物质统一性为从唯物史观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理论前提。关于共同体理论,绝大多数学者从唯心史观出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就是一个个“共同体”并建立在“善”的基础上,“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9]1在中世纪,教会就是“信仰者共同体”(universitas fidelium)。[10]761在近代,马基亚维里揭去了共同体的神秘面纱,处于价值中立性之中,这也让霍布斯看到,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缔造“人造共同体”(artificial community)亦即“契约共同体”,[11]25洛克、卢梭同样以霍布斯契约共同体为进路,康德的“新共同体”思想和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伦理共同体”也始终无法超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后来滕尼斯和安德森也同样如此,滕尼斯从意志来分析共同体,认为意志的有机结合就是共同体,“共同体的理论是从‘人类意志的完美统一’这一设定出发的”;[12]76安德森更是把民族共同体视为“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是被“创造出来”。[13]7-8概略而言,这些共同体理论回避了共同体的“客观特征”,将物质性孤悬于共同体之外。
其次,世界物质统一性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即突出意识主观能动性和重视物质基础性辩证互动、相互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第一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第二性的,是由前者派生而来的。”[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五个认同”;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主观性,但在实际的活动中,它在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对物质现实的改造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15]
2.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相互依存,在共同发展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的联系当中,普遍联系进而导致了事物的变化发展。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6]2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1]17进一步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各民族意识都处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之中,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
首先,事物的普遍联系是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哲学基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7]520中华各民族在地理、气候、生产力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恰恰是导致民族之间普遍联系、普遍交往、相互依存的因由。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联袂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四个共同”“四个与共”,既“精炼概括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18]也充分彰显了中华各民族普遍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史实。
其次,对立统一矛盾运动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在中华广袤大地上繁衍生息,虽然存在一定竞争、对垒和冲突,但交流和融合始终是主流主线,伟大的中华民族、气势恢宏的中华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中国各民族由湿润的中国东南部、干旱的中国西北部和南北水田农耕、旱地农耕以及游牧、狩猎三个发展带组成共生互补的地理与经济单元,所以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总的民族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19]266。
再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本格局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共性和个性是相互依存的,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也离不开共性。列宁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无论怎样)都是一般。”[20]558中华各兄弟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密切,有分有合,分而未断,合而未化,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所组成的有机整体,中华民族的疆域、历史、文化、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实际上,中国众多民族的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和演进,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全过程”,[19]96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体现。
(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存在的第一性,阐明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物质性和客观规律性,也表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逐渐萌发、觉醒、强化和铸牢。“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科学揭示了民族是一种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水平对民族的形成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21]
1.从社会存在第一性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确保其真理性和科学性的同时,避免陷入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困境。
首先,从根源上看,社会存在第一性保证了共同体基础的物质性,而非精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来自于物质生产、物质交往,来自于生活。“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7]525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纠正了摩尔根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认为古代的共同体是由两种生产所导致的,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这样就纠正了摩尔根唯物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原始社会建立在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的基础之上”[22]4-5。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从社会存在出发分析共同体,避免了陷入“人造”的困境,停留在思想层面,没有分析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以往的共同体理论,其理论根基大多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正如前面所述的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共同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中华各民族人口等社会存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进程中,自然地理环境是客观前提,生产方式起着基础及决定性作用,政治的上层建筑与观念的上层建筑交相辉映并转化为巩固经济基础的物质力量。”[23]
其次,从发展动力看,生产力、经济基础等客观因素推动并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特征和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共同体因生产力而产生,并表现着生产力,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指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有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观的生产力,也有客观的生产力。”[24]495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同体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25]148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自在、自觉、自强的过程,从根源上讲,也是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既是中华民族自身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产物,也是整个人类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综合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7]540-541
2.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且各自具有历史继承性为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哲学依据
思想观念来源于物质生产,但是思想观念的产生和物质生产并不是相互分离的两个过程,而是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7]524
首先,中华各民族、各民族意识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中华各民族由于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等因素,产生了具有一定个体性、独特性的各民族文明,即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也是中华文明多样性的根基所在。中华各民族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了相应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也产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7]52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26]6
其次,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决定了中华各民族意识之间必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且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中华各民族文化都具特色,并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化同向同行,“我国各民族的特长荟萃,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缔造,我国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各民族特点与特长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发展,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19]128“中华文明不是单一的文明,而是由儒教文明、道教文明、汉传佛教文明、藏传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一些早期宗教文明整合而成的文明。”[27]32
再次,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各民族文化也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在相互影响中承继发展。封闭自守、坐井观天,追求本民族文化所谓纯洁性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历史的经验千百次地证明了:乐于接受其他民族的特长,兼容并包,是有利于本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闭关自守、坐井观天、孤芳自赏,追求本民族文化的所谓纯洁性的任何幻想,都只能是一种抱残守缺、甘于落后的表现。”[19]136
(三)坚持人民至上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观基础
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少数人服务。马克思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究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为全人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28]8从价值目标上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是人民至上、为人类求解放在中国场域的具体呈现。
1.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立场、理论品质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旨趣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并非价值中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价值立场。”[29]143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致力于“为人类求解放”“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28]8的马克思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相遇,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成为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0]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二者互驱互策,相互辉映,共同托起中华民族的崛起”[31],皆以中国人民幸福为旨趣。
2.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深刻揭示“四个共同”的史实,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主体性问题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毛泽东同志也讲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2]1031从成员数量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体,既有当前全体中国人民的现实维度,也有历史长河中曾在中华大地上生产生活的中华各族儿女的历史纵深,“是由长期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的互动往来而成的人群共同体”。[33]从形成和发展上看,中华各族儿女在物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断演进,共同开拓了中华民族的辽阔疆域、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培育了伟大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方面是对狭隘民族主义有力的反驳;另一方面厘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列宁曾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34]18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唯物史观不能片面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要重视精神现象对经济、物质生产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各族人民亲如一家,需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30]246
二、第二个结合:创新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凸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精神和时代精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不断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给予系统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彰显了中国精神和时代精华,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活力魅力,“中国古代哲学重合一、重整体,世界在道的通性上感通为一、一心体天地万物之理;其‘以道观之’‘和而不同’的主张则成为共同体存在的精神根源;其成己—成人为一体、立人—达人为核心的主张亦足以成为共同体实现的价值基础。”[35]
(一)深刻总结“一”与“多”辩证关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华民族的“一”和各民族的“多”,或者是共同性和差异性的问题。“一”与“多”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伴随着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内涵、外延、指代、理解等方面呈现出层次有别、形态多样的历史风貌。中国传统哲学“一”与“多”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既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演变,也作为一种基本的逻辑框架,浸润着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涵养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1.“一”和“多”辩证统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往往作为一种本体存在,而“多”往往作为“一”的派生物或者现象UnkGYusZalHhPsoBEk1XVg==存在,穿梭于中国传统历史时空中。《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里,“一”相当于“道”,而且作为一种本体的存在,进而和“二”“三”“万物”表现为“一”和“多”的关系,其内在逻辑正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朱熹的“理一分殊”可谓“一”与“多”的典型代表,体现儒家探赜道体的重要思维。少数民族哲学家也认为“一”作为世界的本体,是一切事物的来源,没有“一”便没有“多”,如明代王岱舆的“独一互尊”的本体论和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的“无称”的本原论等。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和“多”关系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本格局提供基本理论逻辑。
2.“一”的本体性、本原性和根源性,促成了各民族政权以“正统自居”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求
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以炎黄华夏为核心,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配合四方的“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在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在汉族人民和汉族统治阶级根深蒂固,进而为各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视统一天下为己任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中国的大一统是各民族的大一统,大一统思想体系是各民族共同创建与不断充实的,它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理论基因和历史基因。”[36]
(二)充分发挥“多元和合”凝聚性作用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是核心概念、核心思想,并以“中”“中庸”“中和”“中道”“和谐”“和合”“共处”“合作”“和平”“共生”等形态出现。“多元共在、多元和合、和处和谐、合作和平,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根本性的思想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37]和合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涵养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对各民族团结奋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凝聚性作用。“民族团结的‘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合’形成的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高级阶段。”[38]
1.“多元和合”铸就了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史,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
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强调“一”作为本原性的重要作用,但万物的生成却是“和”的功能所致。西周史伯《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和”是把多种事物、多种因素糅合在一起,彼此相济,促进万物生长;“同”是缺乏多样性的同一,无法促进事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6]7中华各民族的“多元”是基础,为“一体”提供基本元素。“和合”是形成“一体”的手段和方法,对“多元”进行“和合”从而达成“一体”,“‘和合’是中华文化处理不同思想立场、群体、文化体的理念与思维方式。”[39]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儒道互补、道法结合、儒佛相通、佛道相融、以儒释回等已成为常态;在中华民族边疆史上,“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各民族胼手胝足、浴血奋战,共同保卫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
2.“多元和合”造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成就了精彩纷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主要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多元和合”的理念。这种思想理念导致在文化上,各民族秉持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而丰富充实或者改进本民族文化。比如,维吾尔族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吸收了中原文化,“古代维吾尔族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大约成书于1069年),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该书的形成受《论语》《大学》的影响很大,在益智增知、养德修善和治国方式等方面,基本上与《论语》《大学》等经典相同。”[27]35又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集儒、释、道思想文化及伊斯兰宗教文化于一身”[40]。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像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哲学家,以儒释回、“二教同源”的哲学思潮。
3.“中和”思想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概来对待多样性,成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重和去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41]293这种“中和”“和合”思想,促成了以礼仪道德的方式平等对待各种文化,而不是非此即彼,为创新性营造良好氛围。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哲学思想的创新大多是多文化融会贯通的结果,比如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无不是吸收其他学派、其他文化融汇而成,既是一种融合,也是一种创新。
(三)科学阐发“以人为本”主体性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人本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高度契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这种人民性与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或“修齐治平”的情怀不期而遇,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
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特色,并摒弃了其唯心史观的局限性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41]290中华传统文化人本主义,从质上讲,就是摆脱神圣性的束缚,赋予人的本体地位,“其根本观念特征是消解神圣的外在超越者,而赋予人以本体的地位。”[42]约而言之,人本主义的落脚点在“人道”或“此岸”,而非“天道”或“彼岸”。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87a90c138aed6329efc2c7455c220bb0华传统文化人本主义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确立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不懈奋斗,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从自在、自觉到自强的历史进程,既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贯穿其中,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接续和一脉相承。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唯心史观桎梏。中华传统文化中人本主义有其历史局限性,无论是天道规范人事,还是人事鉴识天道,皆以唯心史观为基础。譬如西周时期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周书·泰誓中》)。天命和民意是相关的,天命是通过民意来显示的,只有“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再如春秋战国,墨子的“兼爱”,鬼神色彩十分浓郁;儒家“仁者爱人”,虽然一开始“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之事存而不谈,但后来董仲舒“天人感应”、程朱理学始终无法超越唯心史观的桎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和其他人本主义有着明显区别。
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扬了“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现实维度
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浓郁的家国情怀。在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度以及“家国同构”,汉儒编撰的《大学》突出了修齐治平之道,也就是“八目”,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古代中国,可以说是家国天下的连续体。在某种程度上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这种情怀的延续。“从家国情怀的实践逻辑看,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应当像家庭成员那样彼此拥有情感依恋的心理基础,共同生活在尊重信任的社会条件之下,把互助合作作为一种手段,以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度。”[43]首先,从“修齐”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个体拥有自我意识,即归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成员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存在,“成员承载的共同身份属性是中国国民,也就是国内各族人民,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是成员对国家身份与公民身份的辨识确认。”[33]其次,从“治平”角度,要求个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当共同体深陷困境中,成员应挺身而出,甚至做出牺牲。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目的皆在于“救时之弊”,具有浓厚的救世情怀,“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44]31近代以降,为民族独立、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二是建设更加美好的共同体。北宋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是需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总而言之,“修齐治平”要求个体与社会、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融为一体,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表现为“四个与共”。
三、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纲”,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赋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个结合”的典范。“第一个结合”,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分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这个“中国具体实际”,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从根源上讲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性和客观实在性,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既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也避免陷入三重“困境”。其一,以往共同体理论大多数无视共同体的“客观特征”,将物质性孤悬于共同体之外,如城邦共同体、契约共同体、伦理共同体等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唯物史观出发,坚持社会存在的第一性,避免陷入共同体理论唯心史观窠臼的困境。其二,科学揭示了中华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以及内在发展规律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从理论根源避免“只讲民族之分,不讲民族之融;只讲差异性,不讲共同性”困境。其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了人民的价值立场和动力源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昭示着“四个共同”的史实,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主体性、动力源和价值旨趣,从根源上避免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困境。“第二个结合”,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的活力魅力,使其成为“现代的”。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共性与个性、批判与建构、事实与价值的有机融通中推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是“两个结合”的典范,要从“两个结合”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3-10-29.
[3]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93-105+164.
[4]李毅.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2):1-11+149.
[5]金刚,哈正利.以深化“两个结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理论学刊,2022(02):5-14.
[6]严庆,余金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论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24-32.
[7]邹诗鹏.试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推进民族理论研究之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05):56-65.
[8]尹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文化根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S2):31-35.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英]伯恩斯.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年至1450年[M].程志敏,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1]马俊峰.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4]白屯,张利国,徐丽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点[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0(04):294-298.
[15]李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基础性问题与当代价值[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6):17-23.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赵天晓,彭丰文.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及其重大意义[J].民族研究,2022(02):36-47+139.
[1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20]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1]张新.论习近平关于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特征和原创性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04):46-55+155-156.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3]ea8e4cc4789993238d935f4add398fc5b78bce6adc455ab24994189537355bc2刘丽萍,林春逸.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解析[J].学术探索,2023(06):125-132.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7]何星亮.中华文明·中国少数民族文明(上、下)[M].福州:海峡出版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2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9]徐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哲学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0.
[3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31]马俊毅.试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方位[J].民族研究,2022,(05):15-25+135.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06):1-14+123.
[34]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5]荆雨.道通为一:中国哲学之共同体观念及其价值理想[J].社会科学战线,2019(12):16-23.
[36]武沐,冉诗泽.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J].民族研究,2022(01):110-125+145-146.
[37]罗安宪.多元和合是中国哲学的根本[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03):9-15.
[38]陈坤,唐加军.“和”与“合”:论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系[J].民族学刊,2023(03):33-40+145.
[39]景怀斌.中华文化的终极情感价值及其共同体意识传播[J].民族学刊,2021(01):57-65+90.
[40]徐其超.自然人性的发现和表现——李贽“童心说”与欧洲人文主义比较[J].民族学刊,2011(04):74-84+95-96.
[4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2]黄玉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J].学术界,2020(02):68-76.
[43]陈纪,章烁晨.家国情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北民族研究,2021(03):17-27.
[44]胡适文存(卷二)[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收稿日期:2024-03-02责任编辑:贾海霞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儒学通论”(20&ZD031)、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生态保护案例的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18YJC73000)、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底蕴”(21GTYBC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海林(1981-),男,广东汕头人,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民族学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王刚(1995-),男,四川攀枝花人,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Li Hailin1, Wang Gang2
(1.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2.School of Philosophy,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610041,Sichuan,China)
JOURNAL OF ETHNOLOGY, VOL. 15, NO.05, 01-09, 2024(CN51-1731/C, in Chinese)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4.05.001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refers to an integration of Marxist principles with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as well as it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model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Breaking it down, the “first combination” can be defined as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oncrete reality” and the regions 5,000-year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viewed through the lenses of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articularly from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is theory has clarified a scientific basis and intrinsic valu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plained materi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underpinn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lai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 coherent perspective on the state, history, country, culture, and religion. I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hile avoiding a triple dilemma: Firstly, starting from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it insists on the first nature of social existence to circumvent idealistic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ty theories. Secondly, it scientifically reveal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emotional familiarit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o prevent focusing solely on dissimilarities and not commonalities. Thirdly, it conceivably clarifies the subjectivity, power source, and value interes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decidedly avoid the dilemma of “serving for the minorit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an be described by a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Marxist principles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hancing the latters vitality and charm. To illustrate, this combination deeply outlin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many”, and it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is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s well as a remarkable continuity and u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apparently has served as a basic logical framework that has infus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Secondly, it evidently has given full play to the cohesive role of “pluralism and harmony”. This culture of harmony ha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nurtured the outstanding innovation, inclusiveness, and peaceful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as been playing a unifying role amidst the struggle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rdly, it has scientifically expounded the “peopleoriented” subjectivity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ghlighting the realistic ideal personality of “selfcultivation aimed at achieving the ultimate goals of peace under heaven”, integrating the individual with society, the state, the nation, and all of humanity. This integration is currently manifested in the “Four Shared” principl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short,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an be viewed as a novel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serving as a model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thi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hould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s”;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arxist Community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