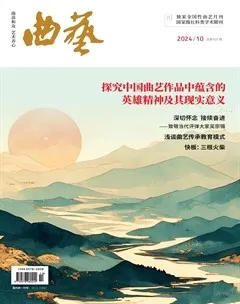浅谈曲艺传承教育模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可见,培养一支强大的文化人才队伍已经成为新时代文艺的迫切需求。文化人才队伍的壮大离不开传承教育,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艺艺术,在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进程中,有着独特的传承教育模式。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是形成了传统的师徒制与现代的曲艺教育并存的多元传承模式,二者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共同担负起培育新时代曲艺人才队伍的历史重任。
一、传统师徒制和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
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传统曲艺在早期传承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正规且系统的科班传承体系,而是像很多旧社会行走江湖的杂耍艺人一样,遵循着拜师收徒的行规艺俗,形成了行业内完整的拜师程式和较为严格的师徒契约,以及至今传留下来的较为完整的师承体系。这就是曲艺行当传统的师徒制。师徒制是曲艺行当传统的传承教育模式,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来进行艺术传承,课徒授业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依然是曲艺的主要教育传承方式。这种投门拜师的形式,既是行业自我保护的主要手段,也是维系艺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途径,更是有效维持自身行业健康有序传承的有力保障。师徒制的存续,对推动曲艺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曲艺艺术历经百年沧桑仍然盛开在中国的艺术百花园中。
有别于传统的师徒制,现代的曲艺教育开启了传承新模式。它不再订立严苛的师徒合同,对于拜师的各种仪式、礼节等形式亦有所简化乃至改变,关键是其教育方式也不再限于师徒之间的口传身授。影像技术以及电话、手机、网络等通信手段等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极大地拓宽了老师的授业途径和教学手段,同时也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方式方法。曲艺班、“团带学员”、少儿曲艺教育、院校曲艺高等教育、网络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形成了现代的曲艺教育模式,让曲艺传承教育走上了全面化、专业化、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之路。
二、从传统的师徒制到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的历史沿革
清代中晚期,曲艺开始兴盛,很多穷苦的底层市民生活窘迫,为了养家糊口,他们纷纷投入到杂耍行当中,从而极大地壮大了曲艺人才队伍。同时,为了生存,艺人开始探索一条艺术传承的道路。师徒制不仅适应时代艺人的生存环境,同时也符合曲艺行业的艺术特性。拜师不仅是为了投师学艺,也是为了在行业内站稳脚跟,得到同行的认可。所以,“摆知”也是很多艺人都要经历的拜师仪式。当然,师徒制在旧社会也存在着类似于卖身契的“师徒合同”,养子养女制等种种弊端,这都是封建社会残留的陋习恶俗。但不可否认,口传心授的传统师徒制式以契约的方式有效地维系了曲艺的传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传承方式。
除此,杂耍行还出现了班社和社团组织,二者不像北京的富连成、天津的稽古社、上海的厉家班等戏曲科班,曲艺班社多以社会救助的形式培养艺人,让其能够以技谋生,如天津的“盲生词曲传习所”、成都的“慈惠堂”、山东邹县的“盲人词曲学校”等。社团组织与班社有相似的性质,除了教习艺人外,也向社会做公益事业,各地最普遍的社团有“三皇会”“长春会”等,也有诸如天津的“艺曲改良社”、北京的“评书研究会”、苏州的“光裕社”等当时著名的地方社团组织。
另外,这一时期各个阶层的曲艺爱好者多有“下海”者,于是,出现了曲艺教师,如天津的花桐春、刘万逵、王亨锟、邱玉山、王宝寅、陆桐坡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曲艺教师。他们为曲艺演出输送了许多出色的人才,对天津曲艺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曲艺教育体系较为单一,但为曲艺在未来的传承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艺术已然走向成熟,曲艺艺人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从养家糊口的街头艺人,一跃成为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拜师收徒的传统形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师徒制摒弃了不合理的师徒合同、养子养女制等封建糟粕,新中国的艺人们开始不断探寻曲艺传承的新形式,他们试图打破师徒制这种单一的教育方式。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地方戏曲学校纷纷开设曲艺班,如河北、上海、江苏、吉林、河南、广东等省市的戏校都开办了曲艺班。20世纪50年代末期,又出现了“团带学员”这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很多专业曲艺团体如天津市曲艺团、北京市曲艺团、上海人民评弹团等大型曲艺团体开始招收青年学员,以老带新,使曲艺在百废待兴的困境中开花结果,成为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
无论是“学员队”,还是“曲艺班”,这种相对新型的传承教育已经不再只针对专业进行教学授课,同时还有意识地为学员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虽然还不够系统和规范,但是大大弥补了当时艺人的文化缺失,提升了艺人的综合素养。这种传承教育模式的突破,既解决了当时演员数量匮乏的问题,又培育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他们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曲艺舞台的中坚力量。
直至1962年,苏州评弹学校的成立让曲艺有了自己的专业“科班”,曲艺教育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让曲艺教育开始走向了规范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艺人群体的大量流失,曲艺传承愈加紧迫,很多刚刚恢复的曲艺团体继续恢复并延续了“团带学员”的传承模式,同时还出现了院校曲艺教育、少儿曲艺教育等新模式。其中,1986年成立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培养北方曲艺表演人才为目标的综合性中等专业学校,开启了全新的曲艺教育模式,是曲艺传承教育的一座里程碑,开辟了曲艺传承的新途径,它标志着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开始走向成熟。此时期,很多地方曲艺团、群众艺术馆乃至区县文化馆等单位也纷纷组织开展培养曲艺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曲艺骨干。
进入新时代,新型的曲艺院校教育更加如火如荼,随着中国曲艺家协会、辽宁科技大学组织编写的曲艺类高等教育专业教材的问世,终于在2022年,经过几代曲艺人不懈的努力,曲艺被正式纳入本科专业目录,这也预示着曲艺被赋予了更优质的文化标签,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迈上了新的台阶。与此同时,师徒制也有所创新,如2013年,曲艺作家、理论家高玉琮开始了曲艺作家和理论家的收徒;2016年,曲艺理论家、评论家孙福海首次采用“网络摆知”的形式,开创了曲艺拜师的新形式。这些都为未来的曲艺传承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三、传统的师徒制与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各具优势
不能简单地判定师徒制和现代的曲艺教育哪个更有利于促进曲艺的传承,曲艺人才队伍的建设,既脱离不了传统的师徒制,也离不开现代的传承教育,虽然二者都带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各具千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负着各自的责任。
传统的师徒制更能有效地培养曲艺的行业精英,同时也能繁衍出更多曲艺精品。作为专业曲艺人才,肩负着曲艺艺术本体传承与发展的重任,而只有传统的师徒制才能延续更纯正的艺术血脉,真正地让曲艺舞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纵观中国近现代曲艺史,其中每个历史时期的精英人才几乎都有清晰的师承关系和门户脉络。另外,曲艺作品的传承离不开口传心授。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影音技术不发达,很多曲艺作品只能通过师徒之间的传授才能得以保存至今,为曲艺留下了一大批经典的传世之作。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优秀曲艺作品也是通过曲艺的精英群体进行艺术创作与再创作才得以传承。
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更有利于拓展曲艺在社会层面整体的普及范围与认知度,极大地壮大了曲艺人才队伍。将师徒之间点对点的传授形式变为以点带面的授课模式,扩大了曲艺的受众群体,开阔了曲艺的艺术视野,让大众对曲艺艺术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解和认知。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提高大众的曲艺审美水平,提升大众的曲艺审美能力,强化大众的曲艺审美需求。“三俗”问题一直是困扰着近20年曲艺界的一个“心结”,而这个“心结”正是业内外对曲艺本体的引导能力不坚定和具备的审美水准不统一导致的,所以,只有让社会整体对曲艺有了正确客观的了解,这个“心结”才能被解开。
传统的师徒制更便于传承曲艺行业最核心最本质的技艺精髓,激发曲艺本/TeYYGvtFyd+UUPxozgw6iEs6LY7ejYG119pGbGdSuU=体的创新与发展。在曲艺繁杂的表演技艺中,有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独特技艺和技巧,即我们常说的“绝活儿”,出于行业自我保护的需要,这些技艺的传承很多都来自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只有这种关系才能更加完整地系统地将其保留下来。而许多没有经过师徒关系的“行外人”,即使观摩习学多年,可能也无法得到“真传”,进而获取其艺术的核心价值。除此,曲艺本体的发展核心是演员和作品,只有演员和作品得到了良好的传承环境,才有可能带动曲种本身的发展,或是艺术风格的创新。
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可以促进曲艺的全面提高和发展。新时代的曲艺人才队伍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演员群体,它还包括了曲艺组织管理、曲艺创作研究、曲艺市场经营、曲艺教学培养等重要群体。所以,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曲艺舞台演出实践教学,同时还涉及曲艺创作、曲艺研究、曲艺出版、曲艺教育、曲艺鉴赏、曲艺美学、曲艺管理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的形成遍布且服务于曲艺传承过程中所必需的每一个环节,进而提高曲艺表演人才的艺术综合素养,让曲艺行业传承链更加完善和规范。
不难看出,师徒制的优势正是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的劣势,相反,现代的曲艺传承教育的优势也正是师徒制的劣势。所以,只有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弥补、相互促进,才能不断壮大曲艺优秀人才队伍。
作为新时代的曲艺工作者,更应该在新征程、新使命的伟大感召下,秉持着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的新思想新理念,开启曲艺传承的新篇章。新时代的曲艺需要更多崇德尚艺的明师和追求不懈的高徒,切不可让传承教育变质,沦为“身份的象征”“赚钱的工具”“流量的渠道”,要切实让教育成为曲艺有序健康传承的重要途径,只有打造一支庞大的优秀的过硬的曲艺人才队伍,才能让曲艺艺术真正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全民族。
(作者: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