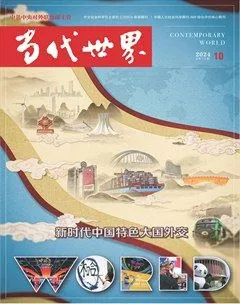“政党国家”视域下的现代化与世界体系变革
【关键词】政党国家形态现代化世界秩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变革的最大动力之一是政党,政党通过组织国家和发展国家而改变了世界秩序。然而,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政党只是宪政、政府下面一个类似利益集团的二级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鲜有一席之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背离,无疑会让那些习惯了西方理论的人看不清现实,更难辨未来走向。比如,全球化到底是在退潮还是在以一种新的模式涌现?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的方向,那么自然就会认为自由主义的退潮就是全球化的逆流。但是,如果审视政党改变世界秩序的历史与现实,就会更好地理解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正在掀起一轮新型全球化浪潮。
政党与国家形态塑造
传统视野下,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是国家,因此外交哲学中对国家行为的研究和理解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作为国家主权代表者的政府首先要维护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这是新旧现实主义以及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然而,如何维护国家利益,“认知”又很重要,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又一宗派,即建构主义思考的重点。这些都是传统视野下的国家。
文明脉络上的国家,国家利益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但是,如何看待尤其是如何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不同文明脉络上的国家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在社会史即“多统”势力共存并奉行丛林法则的文明体系里,竞争性、对抗性争夺资源就是其与生俱来的政治观或者文明观,诞生于这种文明体系中的国家如果主导世界并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样的世界必然是不安宁的、战争频发的世界。相反,在政治史即大一统的文明体系中,致治、民心是最高法则,治平世是其初心,其政治观完全不同于社会史形成的政治观。
文明基因意义上的国家在近代演化成不同的类型,在西方形成了著名的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基因色彩较重。然而,在国家建构进程中,政党作为国家组织者出现了,从而赋予国家新的形态。
在新文明形态中的国家,国家既是利益的代表者和表达者,也是文明的传承者。但是,“文明”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发展的、动态的,新文明观会赋予产生于古老文明的国家以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和政治理念,使古老文明焕发青春活力,使诞生于不同文明体系的国家可能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和政治追求,进而改变世界政治的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新文明观,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这样一类新政党,赋予产生于东正教文明的俄国和产生于中华文明的中国新的精神气质和政治追求,政党在改变国家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秩序。“政党国家”相对于“民族国家”更具文化根性和使命属性。
政党与现代化模式创新
现代化浪潮是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大转型,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现代化波次中。第一波现代化发起者无疑是掀起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其推动力量是商业集团,到19世纪末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化。第二波现代化的发起者则是追赶英国的德国、日本等国家,其推动力量是以官僚集团为主的国家力量。从发展的社会科学体系看,这两波现代化过程分别催生了反映资本家利益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以论证其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性。
与德国、日本同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还有俄国(始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中国(发轫于洋务运动)。1894—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证明两国的现代化模式无效,两国有识之士迫切寻找新的现代化模式,即如何将国家更有效地组织起来。最终,俄国和中国都走上了政党主导的现代化道路。
为什么是政党?首先,这两个国家的商业非常落后,商业集团担当不起组织者角色;其次,国家处于失败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强力部门不再服从政府的调动,而中国自北洋政府成立不久就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在这种态势下,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者去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政党”是时代的呼唤,列宁系统阐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原理和政党组织国家的理论,相比于此前的组织国家的君主制模式、贵族制模式和宪政主义模式,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并组织国家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和全新的模式,所以亨廷顿极为推崇列宁,认为列宁才是真正的权力大师和政治学鼻祖级大师。[1]
为什么是列宁主义政党?从一开始,世界上大多类型的政党都是利益集团式的交易型政党,这样的政党无法有效组织国家,也无力推动现代化。1800年美国的选举活动中,政党第一次以组织选举的力量出现,由此拉开了世界性政党政治的帷幕。服务于选举的政党难免沦为掮客型政党,它是宪政主义体制下的一种交易型政党。这种政党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越来越普及。不同于掮客型政党的利益交易,以《共产党宣言》为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开始就是一种使命型政党,其长远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但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党因长期浸泡在议会政治中而出现“修正主义”,从使命型政党蜕变为交易型政党,它们无力也再无愿望去解放全人类了。在与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列宁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一度困扰苏共,争论的答案是肯定性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苏共走上了被后人诟病的“斯大林模式”——集权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有目共睹,但一个常识是,不能简单把苏共领导等同于“斯大林模式”,如果没有苏共有力领导,苏联能否实现现代化?不能实现现代化的苏联能否存在并继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段历史虽然充满争议,但确实是历史前进的重要阶段。苏共首先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并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镜鉴。
苏联解体是苏共的失败,也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半途而废的镜鉴。苏共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没能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长期的、过度的集权化抑制了社会活力;在寻找出路时走上西方政治道路,将使命型政党演变为交易型政党,实行党争民主;党争民主招致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合法化,国家因此四分五裂,苏共也失去执政的合法性。
同样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1921年成立时的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也可以说是苏联推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解放全中国”只是使命型政党的初级目标,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建设新中国”。而在中国大地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又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中华文明的一个优秀政治传统就是治国理政上的贤能主义。“德才兼备”是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比如,组织部门选拔干部的基本原则是德才兼备,统战部门则负责联络党外的贤能人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汇聚了党内外各界别的贤能人士共商国是。贤能主义赋予使命型政党以动力,使其使命能达。没有各层级、各方面的贤能人士,再伟大的使命都难以落地。
贤能主义的价值关怀是民本主义,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优秀传统。民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具有极高的契合度,从而使一个使命型政党不可能脱离人民群众。事实上,“群众路线”体现的是根源于民本思想的民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力保障。民本思想虽然有几千年历史,但说到底只是一种思想,最多是一种关怀民众的政策,比如轻田赋。在民本思想中,“人民”永远是一种政治客体。但是,群众路线则是一种决策和工作方法,最后演变为制度,并催生了若干体现人民群众主体性的“人民群众团体”,诸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科协等群众团体,使各层次、各方面的群众关切都能得到有效回应。回应性是衡量民主程度最没有争议的标准。这样,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的人民民主有了几千年文明基因的滋养,中国的民主模式堪称“民本主义民主”。[2]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有了贤能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历史文明基因作为丰厚土壤的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才有可能。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明相结合的生动实践,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有着悠久传统文明的国家以新动力新活力,有着深厚传统文明的中国因马克思主义而大放异彩。国家是文明的最重要载体,如果国家羸弱k21aQiZxeG4apxllmQbpUyJ89Zt8T9tCYZdBCBLxzg0=,再伟大的文明也不会被尊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以诠释为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才有中华文明的重焕荣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仅把民众从客体变为主体,而且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使传统政治文明都得以更化。可见,在国家—政府—人民的几个根本维度上,中国共产党赋予中华文明新活力新气象。正可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改变国家,并通过与世界的互动逐渐改变世界面貌和世界秩序。
政党与世界体系变革
工业革命是世界政治的分水岭。约1700年前,尽管有大航海带来的贸易“全球化”,但世界政治依然处于“多中心”状态,诸如东亚的儒家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和大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工业革命很快将“多中心”的世界政治演变为“单一中心—半中心地带—边缘地带”,而且“中心”的属性发生了质的变换,从“文明中心”演变为“资本主义中心”。[3]按照《资本的年代》作者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到1875年,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胜利,即《现代世界体系》作者沃勒斯坦所定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言之,彼时世界体系的属性是资本主义的。
世界体系演变路线图大致可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单中心世界体系形成期(1700—1900年)、世界体系剧烈动荡期(1900—1945年)、世界体系二元对立期(1945—1990年)、世界体系的单极期(1990—2010年)、中国步入世界体系中心地带时期(2010年至今)。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变革,往往充满战争与革命、霸凌与反抗的腥风血雨。在世界体系演变的关键时刻,无论成败,表面上是国家,其实都是政党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一,十月革命与世界体系的重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早已形成。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组织体系,有效率但也极度野蛮和不平等,因此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中,最为有力的资本主义批判者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还建立了改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推动的以“阶级”为主体的工人运动,但是“阶级”的宏大性和模糊性意味着组织“阶级”的行动是极度困难的事,而列宁则通过政党实现政治目标。
列宁主义政党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世界历史的里程碑事件,它根本性地挑战了经过两百多年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围追堵截和无情打压。一战后,代表自由主义的“威尔逊十四条”虽然也主张民族自决,但关键时刻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把德国在中国青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中国。只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受压迫的非西方国家伸张正义,主张真正的“民族自决权”即民族解放。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受压迫、被支配的穷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也是属于穷人的。穷人的国家为穷人代言,可谓天经地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巨大示范效应。有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形成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苏共失败与单极世界体系的再现。如果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那是因为苏共的政党能力。同样,苏联解体也缘自苏共的执政能力出了问题。比如,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教条主义状态,习惯于从经典作家那里寻章摘句而论述现实中的问题,与民众的心理认知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长此以往,党员干部群体心理麻木。这就是为什么在苏共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苏共党员普遍处于观望状态,任凭苏共这条大船沉没。因此,苏联解体其实是苏共失败的苦果,苏共的失败才使得世界又回到单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即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时代。
第三,政党主导式现代化与世界体系的巨变。世事无常,单极霸权仅仅在20多年之后,就难以为继,原因在于世界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变局无疑与中国有关,中国以发展自己而改变了世界。中国的发展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导式现代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再次改变了世界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以民族独立为现代化的起点,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主体都是政党,比如印度的国大党等。只不过,因政党类型不同,能改变世界体系的也只能是使命型政党。
政党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政党在国家建设、现代化进程和世界体系变革中如此重要,但政党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则处于边缘位置。比如,在西方的本国政治研究中,政党的地位同利益集团一样,是一种“社会”力量而非“国家”力量,“政党”被淹没在社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之中。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虽然有亨廷顿这样的政治学巨匠发现了权威性政党的重要性,但主流政治学依然是呼唤“回归国家”而不是“找到政党”,“政党”被淹没在国家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之中。虽然政党事实上改写了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连政党的影子都没有。理论和历史、理论和现实之间是如此遥远,让我们如何把握世界走向?
作为“舶来品”的政治学亟待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国家的政治领导力量而非西方式政党的社会力量;国家不会自动地自我组织,而是政党将国家组织起来,没有强有力的政党,很多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国家自主性”,谈何“找回国家”!现实问题应该是“找到政党”而非“找回国家”。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两大知识体系即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理应有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4]
作为政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必须赋予政党应有的地位。如果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民族国家”,那么“政党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概念也必须建构起来,但是“政党国家”的位置在哪里?这些年中国兴起的世界政治学给“政党国家”留下了空间和位置。世界政治学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场而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制度变迁和改变的大国关系及世界秩序,“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是世界政治学的两个研究单元,它们分别是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的放大。换句话说,看起来无比宏大的世界政治学,说到底还是以原子化的个体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学的实存性和科学性。世界市场直接换算为国家利益,背后的力量是商业集团以及作为商业集团工具的国家;政治思潮则是社会性政治观念推动的政治运动,其最大推手无疑是政党,尤其是使命型政党。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西欧传播到俄国、再由俄国传播到中国乃至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也离不开相关政党的推波助澜,比如从美国的“茶党”到法国的国民联盟。这样,国际关系研究就不能不关注到对象国的政党政治。

光伏发电设备的发电参数和性能。
政党塑造了国家形态,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使沙皇俄国更替为苏维埃国家,无论俄国胜败,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亚洲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带来的世界秩序的变革。这个事实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是,阶级分析及相应的政党研究应该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但阶级分析并没有获得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那样的学术地位,更看不到政党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不仅如此,政党的历史文明属性也深刻地影响着政党的民族性质并由此影响着国际关系。比如中国共产党,其不仅是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还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中华现代文明的塑造者,具有巨大的包容性、适应性、稳定性和统一性。文明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政党,具有极强的政治韧性和自主性。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意味着,其可能会适应环境的变化,但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解自我。如果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大概不会搞什么“接触”政策,即通过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而改变中国。大概是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2018年后美国又对中国搞起“脱钩”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必然会让“脱钩”失效。
可见,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虽然是“国家”,但国家背后是“政党”,政党不仅有阶级性,也应该有文明性和民族性。以“国家”为主体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民族国家”,并由此形成了影响最大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国家如果演变成“政党国家”,政党的信仰和文明基因,必然使这样的“政党国家”具有超越现实主义的气质。比如,新中国刚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工业化国家,客观上苏共这样的使命型政党提供了巨大助力;同样,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胸怀天下,推动“普惠包容的全球化”,这是因为其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也是“天下观”文明的传承者。因此,“政党国家”应该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而进入国际关系研究场域。
在研究国家建设和现代化模式中笔者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那么,作为内政延续的外交领域研究诞生的应该是“政党国家”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党和国家”已经习以为常,而英文的“party-state”翻译为“政党国家”比“党国”更好。无论如何,中外文都有“政党国家”之说,而这个实践性常识的“说法”应该成为一个理论上的描述性概念。这不但更有助于厘清国家史、国家关系史和世界政治史,更有助于人们把握现实中的国内外政治,从而发展出更符合事物本身情况的对外关系。
当然,正如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概念的“民族国家”不能诠释很多国际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要指望“政党国家”去解释所有国际问题。但是,没有“政党国家”视域,当今诸多国际问题就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也难以看清世界政治的基本走向和未来趋势。
[1]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286页。
[2]杨光斌:《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表述问题》,载《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16-20页。
[3]释启鹏:《作为世界秩序“底层逻辑”的世界市场——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济基础》,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第93-109页。
[4]姚中秋、朱怀洋:《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方法》,载《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5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