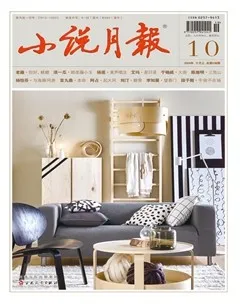大街
大街。
他再次看到了这条大街。
此时,他坐在家中客厅的窗边,漫不经心而又怀有虔诚地望着窗外的大街,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时刻。他想,时时刻刻。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无限期和无目的地坐在这里,望着窗外的大街。所谓“再次看到了这条大街”,不过是内心与上一秒目光之间存在着感觉的断裂而已,也可以说是由于新奇,眼睛发现了某种不可知的事物变化和延宕。是的,每一秒之间的事物是有差别的,哪怕是凝定不动的景物。六十多岁了,他觉得自己似乎很老了,而且觉得自己越活越胆小,要缩到一个盒子里才行。但他又很害怕一些盒子。这仿佛是一个悖论。他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者是消失)存在着好奇和绝望。在他书柜的一角,安放着一个自鸣钟,这个自鸣钟不是纯粹的摆设,也不算古董,它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的上海“三五牌”黄油木质座钟,是他父母留给他的。当然他小时候,也亲自给它上过弦。在这个世界里,几乎每一处的时间都是需要看的,但他的时间是可以听的。那是属于他的时间。每一天,每到整点,这个座钟仍旧准确敲击和报时。他沉溺于时间的提醒,但又无所事事。
这条街道,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市郊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如今它显得过时。无论是街道两旁的建筑的样式,还是它外面墙体的颜色和材料,都显得跟眼下流行的风尚格格不入。许多建筑已经矗立四十年,竟然没多少变化。比如,当初最高的大楼是五层楼,如今还是五层楼。它当初是一家大商场,后来变成家具店,再后来又变成工厂,现在几乎废弃了也未可知。他多年再未走进去。也许它变成了居民楼?偶尔,夜晚,他会发现大楼的窗户里,零星会透出灯光,白天,会看到斑驳的墙皮在风中兀立。
在目力所及的一角,北边的方向,有一条横着的街道,当然那条街道是另一个名字,也更窄些,叫南通街。它与他所处的街道形成一个“T”字形。楼下依旧是车水马龙,只不过它们比记忆中节奏更慢,影子更模糊。他记得年轻时,远处有一座教堂,它不在面街的位置,是在街后,远远地可以看到它的尖顶。街上还有一家出名的雪糕店,经营它的是一对母女,都很胖。他经常走到那里去吃一根。回到家里,他隔着玻璃窗,哪怕是夜晚七八点钟,仍旧可以看到在那家店子的门前,站着许多人,排队等待吃雪糕。那时候,市郊只有这一家雪糕店。雪糕店的旁边是一家冷面店。有的时候,运送垃圾的车,或者邮政局的绿色汽车,因为装卸或搬送,堵塞了街道,会聚起许多人、许多自行车,就跟有人打架被围观一样。
他在这条街道和楼里住了快三十个年头(之前,他在另一处房子里,度过了他漫长的少年时光)。三十多年前,有一个画家,曾给这条街道画过一幅油画:一些梧桐树,混杂着比较年久的杨树,可以看到天际线和排排门店的侧角,以及远处的教堂尖。那无疑是秋天。一九八六年还是一九八七年,毗邻的某栋楼里,发生过一起火灾,当时整条街道几乎被封了。如果没记错的话,街上的许多门店也停业了。
他现在比较喜欢喝咖啡。速溶的或现磨的、进口的或国产的,都无所谓,手边有什么就喝什么。还有就是香烟,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乏力,他一直想戒,但是没成,也就罢了。客厅书柜的一角,还放着他太太当初给他买的戒烟贴,已经泛黄了,也过期多年了,但他没舍得扔。他觉得自己挺可笑。
这座房子就是一座时间的博物馆,里面的每一件物品都会引起他长久的回忆。只要天气晴朗,他隔着窗户,就能望见远处大地深处房舍的炊烟(他想,在如今,还能望见炊烟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啊),他会突然闻到童年时糖果的味道。那种熟悉的幸福感,是从后脑勺和膝盖的部位开始弥漫的,就好比被阳光或初恋的女友抚摸到那里。他此时再次感觉到膝盖的微微颤抖。
他还保存着一支小时候家庭里用过的老烛台。这支老烛台就立在玻璃窗下面的窗台上。它的底座是被加工成菱形的绿色的玉石,竖起来的柱子是铝的或锡的,柱子最上端是一根坚硬的铁刺,那是用来插蜡烛的。
这支烛台是什么时候来到他家里的?记不清了。他只记得,停了电的漆黑夜晚,妈妈让他点燃蜡烛,他小心翼翼地划着火柴,将蜡烛燃烧后熔化的蜡油滴在木板上,有时候会滴在手上,烫得很痛。蜡烛被蜡油粘牢在木板上,竖立起来。他把它端给妈妈。妈妈往往正在缝纫机前忙碌,隔壁的房间会传来爸爸的咳嗽声,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也有的时候,一支蜡烛会燃亮在他和哥哥姐姐们居住的小居室里。姐姐在墙角的小木桌前看书,他和哥哥早已躺下了。说是早已躺下,其实也不早,夜里九点,因为第二天还要上课,除非是周末。如果是周末,他还能听到姐姐在临睡前给他和哥哥讲一个故事。爸爸会偶尔进来,问他们饿不饿,他刚刚烤好了几个土豆,他是趁着厨房的灶膛里还有木炭的余温。爸爸关门离开的时候,门框会发出被老式的、镶着四块玻璃的木门关合的清脆的声响。
爸爸在他的房间里写稿。县里的广播电台经常跟他约稿,通常,他会写一些诗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爸爸的案头出现了那支玉石烛台。有一天,他一个人在炕上玩,头上的广播喇叭(那时候,每个家里都安有一个小小的广播喇叭)突然响起爸爸朗诵他写的诗歌,多少年过去,他只记得一句:“你大义凛然啊——”应该是讴歌张志新。那个“啊”字他记忆犹新,因为带着爸爸蹩脚的乡土口音,并结合着时代化。一个人的作品能像虫子一样钻进房子里,对他来说,是一件多么新奇的事!
在姐姐讲述故事时,他快睡着了。但是他又舍不得睡。于是在蒙眬中,他看到脚底下的墙面上,映着爸爸房间里投进来的摇曳的蜡烛光影,有时候是一列火车,有时候是一个人,它们伴着姐姐的故事,后来终于令他睡着了。
没事的时候,他会到大街上走走。他穿的那件藏蓝色的老式坎肩有些旧了,右边的下摆处沾有一小块绿色油漆,不知道哪年弄上的。每年在清洗的时候,他都会停顿一下,想这块油漆是怎么出现的,结果总是以叹气告终。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戴墨镜,有时候墨镜被早晨的冷雨蒙上了雾气,他也会掏出手帕来擦一擦。他的衣柜里还有件米黄色的风衣,不过他很少穿它了。
没错,他二十多岁时,是街里出了名的能打架的人。不过他很少欺负老实人。谁欺负他,他就以牙还牙。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朋友,也算大哥,叫丁峰。不知从哪年开始,他经常会想念这朋友。丁峰留着短胡子,个头比他高,他一笑就会露出一排整洁的牙齿。打架时,丁峰的出手敏捷以及有力,完全与他平时的低调温和不成正比。
“嗨,骡子,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
“嗨,骡子,你把摩托车的后视镜弄歪了。
“哎,骡子……”
丁峰为什么叫他骡子?也许是笑话他打起架来像头骡子。骡子笨吗?他不知道。他和丁峰从小就认识。丁峰的右眼皮那里有道疤痕,是他给留下的。读初中时,他们和邻居几个小伙伴在附近的山上,坐着吹牛,喝那种劣质的啤酒。就在他无比投入地讲着什么的时候,坐在身边的丁峰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的脚下说:“你看——嘻嘻。”他一低头,发现丁峰在他吹牛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用手里的刀子,把他的皮鞋割开了,皮鞋底几乎要掉了。那是父亲给他买的一双新皮鞋,是他已经读到初二时,人生第一次穿的皮鞋。他当时就把手张开,惊讶得大叫一声,没承想,手里的烟头一下子拄在丁峰的右眼皮上,那里就此落下了疤痕。
丁峰左肋那里也有道疤痕,不是他给他留下的,是丁峰为他而留下的。在录像厅里,别人故意把痰吐在他后背上,引起了争执,他和丁峰跟对方五六个人大打出手。在追逐中,一个人朝他捅刀子,丁峰从中阻拦,死死地抱住那个人,没承想,另一个人用断裂的啤酒瓶,直接刺向他的左肋。那是夏天,大家都穿短袖衫。
丁峰说:“当你深呼吸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充满力量。”难怪每次打架前,丁峰都那么沉静,他是在做深刻的呼吸吗?他记得还有一次,群殴,七八个人对七八个人,他的脑袋被狠狠地撞在墙上,鲜血汩汩地流,他倒在地上,感觉真的要死了,丁峰跪在地上,抱着他,大声地喊:“深呼吸!深呼吸!”
后来他活了下来。
随着天气的阴晴不定,他身体的疼痛也时好时坏。岁月流逝,这就是老了。他今天故意穿着邋遢,帽子也没戴,一眼可见花白的头发,走在大街上,以显示自己身体的脆弱,跟世界达成和解。但谁又认得他呢?这不是四十年前,那时候,只要走在大街上,谁不认得他啊?“骡子来了。”大家小声议论。“骡子”是丁峰最初给他起的外号,后来就传开了。
看了一眼远处的那座五层大楼的楼顶,他想,他不是不想通过用力呼吸取得力量,是身体衰老了,呼吸自动减弱了。
这两年,他经常想起丁峰。他已经离开十多年了。他在一次划船中,不慎失足落水。他走得就像水痕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被抹去了,再也不见。
丁峰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话语,也没有任何物品。丁峰带着他给他留下的两处疤痕,走了。
街边的一家五金店还开着张,门口堆满了杂乱的钢筋和轮胎。他摸了一下下巴,就近踅进去看看。
他吓了一跳。五金店内还是那么肮脏、昏暗,像是地下室一样,连空气中弥漫的锡焊的味道都让他仿佛如昨。一张老旧的木桌旁,坐着两个人。他以为是老肥和他的儿子,怎么会呢?老肥抬头看了他一眼,没作声。
他这才意识到,不对,时光过去了几十年,眼前这个人,是老肥的儿子。他长得跟当年的老肥几乎一模一样:体重应该有二百多斤,头发卷曲,戴着眼镜。那么,坐在这个老肥的儿子面前的年轻人,应该是他自己的儿子——就像当年那个老肥领着他坐在五金店里一样。
“要买点什么?”老肥的儿子问。
“你爸呢?”他脱口而出。
老肥的儿子——当年的小青年——现在也有五十多岁了吧,懒洋洋看了他一眼,低头摁了一下桌子上的计算器,在账单上写着什么,然后说:“走了快八年啦。”
老肥死了。他想。他又暗暗想了一下,老肥若是活着,也该八十多岁了。他望了一眼远处的货架,密密麻麻的,摆满了各种锤子、钳子、胶圈、灯泡,还有镐头。其中有一种扳手,一下子让他想起了从前——如果不是在这里见到,他一辈子都想不起来,但是既然见到了,他觉得竟然那么亲切,并且为此感到羞愧。那是一种花式扳手,薄薄的一张铁片,镂空出好多不同形状的孔洞。现在竟然还有人卖这个!他记得,那是小时候,家里修理自行车时经常使用的工具,用它来拧不同大小的螺丝帽。这让他一下子就想起了他的父亲。他人生第一次跟劳动和机械打交道,就是他父亲用这个来教他如何修理自行车。现在,他早已不买任何工具了,他的生活里没处去使这些东西。以前……那是太久的以前了。
他默默地退了出来。阳光一下子刺得他睁不开眼。一个女人从他眼前经过,他不经意地就看到了她闪现着的乳沟。因为她离他太近了,开领又比较低。他怔了一下,望着那个女人离去的背影,感觉她应该很年轻。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默默地掏出一根香烟,送到嘴边点着。他吸烟的姿势和表情,无比决绝,仿佛是刚刚主动跟那个女人结束了一场恋爱一样。他觉得他应该大哭一场。
他站在街头宽阔的“T”字形路口,尽量让目光变得飘忽。这路口太阔大了,两边的建筑因为低矮和绵长,竟然显得有些变形。有一瞬间,他感觉置身于中世纪的古罗马斗兽场。从这里,可以望见他家住的楼,以及他四楼房间的窗口。是的,他曾无数次站在那个窗口,向外眺望。他记得那里住着一个单身男人,他太太走了很多年了。他每天早起后,洗漱,刮胡子,在涂满剃须液的脸上,端详一个被岁月抛弃的男人的面庞。有时候他走到窗口,向外无由地探望,却又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就像现在,他望着那里,就像望着一个替身。猛然地,他再次想到了老钟。
他掏出手机,给老钟打了个电话,约他吃饭。
老钟乖乖地来了的时候,他再次发现自己是那么讨厌老钟。当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拿学历,也为了找工作,在县城读夜大的时候,丁峰、老钟和他在一间宿舍里住着。老钟总是在房间的窗帘下放着一个带铁丝把手的尿罐,他说他肾不好,半夜时不时地就要起来解手,可是旱厕在很远的户外,他说自己又胆小。他说自己胆小的时候,丁峰总是狠狠地骂他,怀疑他是因为懒。因为房间里放着个尿罐也就罢了,他和丁峰经常在夜色昏暗和熟睡的迷蒙中,听到老钟窸窸窣窣地起床,接着就会听到哩哩啦啦的尿尿声,可是不管天多么白,老钟从来不会自己倒尿罐。老钟的尿罐十有八九是他去给倒掉的。老钟还有个让他瞧不起的毛病,就是从年轻时候起,喜欢跟人借钱。老钟也曾无数次地跟丁峰和他借钱,当然一次也没还。就在去年,老钟还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跟他借了三千块钱,当然至今也没还。
他固然也不好意思要。如果他每次都好意思要,老钟也不会这么乖乖地前来。老钟是吃准他了的。
老钟跷着兰花指,坐在西餐桌的对面,端起酒杯说:“敬你。”
他自顾呷了一口酒,白兰地。他嘴里弥漫着一种沉木的香气,只不过稍微有点苦。
“后来丁峰跟我说你说的没错,胆子确实小。”他说。
“嘿嘿。”老钟笑。
他指的是有一次,在宿舍里,隔壁几个人为了一点什么事,跟他们约架,他和丁峰甩掉拖鞋,弯腰正在地上换球鞋,老钟坐立不安,说:“我去趟厕所。”
结果直到他和丁峰把对方砸得落花流水,老钟才装模作样提着裤子回来,说:“啊?这么快打完啦?”
丁峰就笑。他笑起来仍旧露出一排洁净的牙齿。
几乎每一次都是,他约老钟见面,吃顿饭也好,谈个天也好,话题总是从丁峰那里谈起,并且几乎每次,都是由他起头。他感觉老钟其实不喜欢丁峰,而他也不喜欢老钟。不过,许多事情就像上瘾一样,每当他怀念丁峰的时候,他就只能见见老钟。就像在无数个薄暮时分,他坐在自家窗前,看着夕阳被融金的云彩一点点吞噬掉,最后消失不见的时候,他还能知道落日的方向在哪里。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能使他回忆起与丁峰的往事的,在他所有的朋友中,只剩老钟一个人了。老钟是他当下跟丁峰的一个纽结,这没办法。
他跟任何一个人谈起丁峰,他们都不认识他。或者只是听说过他,但没法跟自己做更多交流。丁峰就像一个生命中的抹布,被随意地丢弃了。
有时候他想出趟门。比如,他收拾好了行李箱,把它放在简陋的通往门厅的走廊,甚至他连钥匙都交给邻居了,请他们帮助他定时浇花。可是当他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却又打消了这念头。他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他望着那个走廊,想起某年,或某日,在一门之隔的外面,抄表员曾给门上贴过欠费的条子。那一张条子,就让他觉得仿佛欠生活许多。他还想起在走廊内,他和太太刚搬进来的时候,他俩在走廊里做爱。他的太太带着一点小心,脱了一只鞋子,后来不脱了,他们用双脚的不规则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不,他不认识丁峰,为什么即便在他感觉生命最酣畅的顶点的时候,他要想起丁峰呢?他想起丁峰为他挡过一刀。那也许是生活中的一把刀子。他还想起,在他跟太太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她多么年轻啊),她妩媚、从容,跟谁都充满亲和力,身上仿佛贴着一层海绵,与人为善,当然也吸收外界传给她的能量。那一次,夜大毕业之际,同学们组织去郊区远足和旅游,他带了未婚的太太去。在旅途中,同学们不断埋怨和咒骂活动的组织者,选了一个什么破地方啊,虽然有林荫,但是到处都是沟壑,简直是一群农民被号召上山劳作。他落在队伍的后面,尽管所谓的队伍,也是七零八落了,变成三三两两。在一处溪涧面前,他看到未婚的太太不敢过,于是身边的丁峰拉起她的手,扶着她跨过去——那一幕,他恰巧看到了,也恰巧丁峰看到他看到了。他们的目光对峙了一下,然后他们彼此温暖地笑了。不过从那以后,丁峰再也没接近过他的太太,哪怕是许多年后。丁峰毕业后,甚至四十多岁,也没有处过女朋友,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苏伊士运河是哪年开凿的?”
“什么?”老钟正吃着一块甜点。
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话。他的脑海里还是当年读夜大时的课堂。考试的时候,他急慌慌地抽出事先藏好的小纸条,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抄写的答案:“一八五九年。”
“这个东西多少钱一块啊?”老钟问。
“什么?”他诧异。
“这个,”老钟说,他仍旧跷着兰花指,把手里的多士甜点转圈翻着,“这个。”
他讨厌死了老钟。但是他仍旧笑着,耐心地说:“大概二十块钱一块?我猜的。”
“嚯,嚯,好贵。”老钟说。
老钟吃掉那块多士,连纸巾也不拿,直接用两只手搓了一把脸,目光瞥向别处,似乎在想着什么。
他静静地坐着,不去打断老钟。他觉得老钟也陷入了回忆。
他觉得老钟也老了。两鬓不仅白,而且鬓毛稀疏。他的嘴角一边是翘着的,一边却又是耷拉着。他希望老钟能主动跟他攀谈些什么,但是老钟沉默了片刻,突然说一句:“我肾一直不好,下个月还得去治疗一回,你借我两千块钱好吧?”
他起身,用手机给老钟的信用卡里转了一笔钱,然后告别。
他发誓再也不找老钟了。
但是事实是,以上镜头,不过是他后续不断在重复的一个场景而已。他的生命里不能没有老钟,不能没有这个令人极其讨厌的人。他在生活里的某一时刻,总是会有“咔嗒”一声,仿佛定时闹钟,他想,完了。
有时候,他会跑到南通街,在他楼下不远处拐角的那条街道,去看看丁峰住过的地方。那里快要动迁了。这条在本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市郊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的毗邻街道,住过一个叫丁峰的大哥,他要随着街道和岩石、墙皮、钢筋一起消失了。无数个夜晚,他和他走在路边的灯光下,彼时也谈起过未来。有时候,兴之所至,丁峰会邀请他到自己家里,他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后来,他黏在太太身上的时间多了起来,直到丁峰一个人去了另一个地方。
假使,生活中有一种意外,开始的时候就是结束,那他还值得为此去过吗?他摇摇头。不知道。他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太太、父亲、母亲、姐姐。他们给自己讲故事,哄他长大。他太太的头发是棕黄色的,发梢在枕边的时候显得透明,他抚摸它们。他也抚摸她结实而富有弹性的乳房,他用自己的顽强解除她的一切矜持,就像下雨时,他们彼此围拢着一把伞,而这把伞是他给她的。他一遍遍地给她穿好衣服,又一遍遍地脱掉。还有那只仍旧放在走廊处的未被拎起的行李箱,他们一起旅行时用过它。“我的丝袜,”她说,“我的丝袜忘拿了。”坐在车厢里,她随着车轮的颠簸,晃动着身子。他有时候觉得,他父母给予他的生命,就是为了他去忘记一条丝袜。仅此而已。
这个夜晚,他睡在床上不久,就感觉自己发烧了。他不知道抽屉里还有没有药,他懒得去拿。他在想,他能不能在痛苦中,也感觉出快乐。他的头也痛得很,身体像是麻袋浸满了水。朦朦胧胧中,他听到楼下有人打架,一个少年和一个中年男人,争吵中有摔碎酒瓶子的声音。
他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但是超出他的判断,殴打声竟然越来越大。他扭开灯,想了想,又本能地关闭掉,勉强自己的身体,在夜色笼罩的房间里移动到窗前,望向楼下。他看到一个少年,被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殴打,少年极力挣扎和反击,但是无济于事。
大街上围了一些人,但是没人敢去阻拦。一种力量立刻在他身体里升起。他跌跌撞撞地挪动到厨房,费力地弯下腰,在最下面一层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只生锈的大开口水暖扳手。它沉甸甸的,他感觉胳膊在传达一种久违和颤抖的膂力。妈的,他想,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和一个叫丁峰的人。他许久不默念自己的名字了。
他向门口走去,只不过摇摇晃晃。他觉得他有冲动和力量去拉开门,走到大街上。没想到的是,走廊里的行李箱绊了他一下,他迎面扑倒在门框上,失去了知觉。
etzjZqdCGiszZJd0dkxZJOS1bETmz/b8Afie86yyIN4=现在,他仍旧坐在阳台的窗边,看着对面的街道。那条叫南通街的街道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比他居住的楼房还要高出几十米的楼。楼下依旧是车水马龙,只不过它们比记忆中节奏更慢,影子更模糊。他还能看到远处的教堂,以及它的尖顶。与以往记忆不同的是,他第一次看到那里落满了冬天的积雪。
那次摔倒,使他拄上了一支可折叠的电镀拐杖。他经常不用它。因为他出门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他会想起一句话、一个故事,是不是小时候在烛光下听过的,他不记得了。也有的时候,他会想起遇过的一个女人,她年轻,仅仅是跟他笑了一下。他的房间墙壁上贴满了自己写下的纸条:“早晨,空腹,恩替卡韦片,含服,每日一次”“早晨,中午,晚上,洛索洛芬钠片,每次一片,每日三次”“卡托普利,每日一片”……
这一天,他自感心情不错,在房间里,他竟然抛弃了拐杖,慢慢走到盥洗室,剃了胡子。有没有仔细端详自己的面庞他不记得了,他擦干了双手,迫不及待地给老钟打了个电话。他想约他见个面,吃个饭。
电话响了许久才接通。对方是一个女声,他不熟悉。
“我找老钟啊。”他说。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充满了深情。
“老钟,他走了。”
“啊?走了多久了?我怎么不知道?”
“走了三个月了。你是谁?”
对方问他,可没等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对方就已经把电话挂了。
他缓缓地把目光看向那支倚在墙角的拐杖,他已经不用它了。它孤零零立在那里,像是一把脱落了伞骨、准备被主人丢弃的雨伞。
原刊责编 李锦峰
【作者简介】于晓威,1970年生,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鸭绿江》杂志主编。在《收获》《上海文学》《钟山》《作家》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著有小说集《L形转弯》《勾引家日记》《午夜落》《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长篇小说《我在你身边》等。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作品被翻译成日本、韩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多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