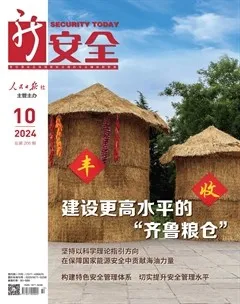内事文而和 外事武而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攻伐纷争不断,事关国家安危、战争成败的内外因素,就受到广泛重视。《逸周书·武纪》提出,“凡建国君民,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讲的就是建国治民,内政要使用文德达到平和、和谐,外事要讲武力做到恰当、正义。这句话体现了治国理政的两个统筹:统筹治理内容“内事”与“外事”;统筹使用治理方法“文”和“武”。“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反映了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家生存安全,既要重内也要重外。可以说,这是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五个统筹”一脉相承的传统安全文化思想,具有内外兼顾、综合施策的重大现实意义。
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不少朝代因统筹内外安全而盛,亦有不少政权因偏颇内外安全而衰。以唐朝为例,出现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盛唐景象,与统治者妥善统筹内外安全密不可分。唐太宗在国家安全上采取内外兼修战略,强调“治安中国”而后“四夷自服”。一方面,就“治安中国”而言,唐太宗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法治、经济和军事建设上。在法治上,以奉法为治国之重,编纂施行“以礼入法,得古今之平”的中华法系代表之作《唐律疏议》;在经济上,强调轻徭薄赋,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在军事上,强化军队力量,指出“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另一方面,就“四夷自服”而言,唐太宗主要以文德服人,指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反对与周边少数民族相隔,并给予归顺少数民族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同时又进行征讨高句丽、攻灭高昌国和平定吐谷浑等多次边境防御和反击战争,巩固了唐朝的疆域和统治地位,奠定繁荣稳定基础。可见,“治安中国”是“四夷自服”的基础条件,“四夷自服”是“治安中国”的必然结果。唐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了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并采取恰当战略举措,成功维护了国家安全稳定,不仅推动了唐朝的繁荣发展和声名远播,更对后世的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与唐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朝。宋朝的经济、科技和文化极其发达,但却是中国历代中发展与安全反差最为强烈的一个朝代。宋朝虽然名义上终结了五代十国的乱世,但从未真正统一过中国,始终在少数民族政权夹缝中求生存,外患尤其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军事、注重外部安全本该是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但由于宋太祖系以陈桥兵变建立王朝,加之对前朝武将乱政“余悸犹存”,因此他对军事力量有着天然的猜忌与不安,以至于矫枉过正、重文抑武。“杯酒释兵权”后,宋朝实行“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更戍法”体制,同时安排文官将兵,忽视练兵备战,淡化军事力量建设。殊不知,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保障,否则来犯之敌就会肆无忌惮。宋太宗却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宋朝“守内虚外”,实行消极防御政策,致使辽、西夏、金、元屡次侵犯,宋朝腹背受敌却无还手之力。重视内部安全固然重要,但凡事过犹不及,尤其是当外患尤为明显之际,仍为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置外部安危于不顾,可能会导致国家走向灭亡。宋朝的科技、文化和艺术水平均处在顶峰,但当朝君主却对危害国家安全内外部因素的认知错位,内外安全统筹失衡,导致王朝灭亡。

回望朝代的兴衰成败、更迭消亡,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经验教训的独特视角。从内部来看,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从外部来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变乱交织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我们应汲取“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的智慧,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总结历史上维护国家安全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更好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内要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努力推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努力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对外坚定不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责任编辑: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