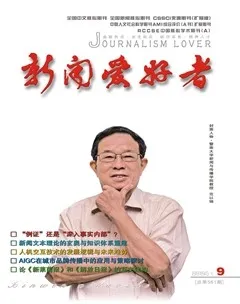媒介供给与文化记忆: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的醒狮意象与故乡情结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众媒介的有效结合,能够传承故乡记忆、增强社会凝聚力。醒狮作为岭南特色的传统文化,是粤籍移民思乡之情的具象表征,其通过黄飞鸿电影为人们展现出记忆中的故乡影像。随着时代的发展,醒狮意象从具象民俗沦为奇观展演,再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折射出故乡情结由显至隐,最终升华至家国之思的转变。在故乡记忆与故乡情结显隐的过程中,电影这一媒介的作用从展演故乡影像发展为建构影像故乡,观众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体能动性,故乡意象的达成有赖于电影制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流动协商。
【关键词】醒狮;黄飞鸿电影;故乡;记忆;媒介
迁移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环节,现代人也无可避免地在迁移中逐渐失去归属感,此时,故乡记忆就成为心灵的乌托邦,而故乡记忆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托大众媒介对传统文化的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铭刻着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通过大众媒介为中华儿女提供“故乡”的归属感。醒狮作为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广东、香港等地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亦是营造中国传统节庆氛围必不可少的因素。醒狮舞动之际或能激发全球粤籍人士对于儿时故乡的回忆,或能唤醒海外华人每逢佳节的思亲情结,亦能见证中国万家灯火的团圆时刻。醒狮之所以能够激发观者的怀乡情结与故乡记忆,固然与人口流动有关,但亦不能忽视大众媒介的作用。醒狮文化正是借助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勃兴与发展,打破时间界限和空间区隔,成为故乡记忆与家国情怀的承载者。
一、黄飞鸿电影:大众媒介、醒狮文化与故乡记忆的交融
从1949年第一部黄飞鸿电影诞生至今,香港地区有超过100部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面世,并催生了“黄飞鸿电影”这样一个专有名词[1]。醒狮与电影的结合是黄飞鸿电影的一大特色。醒狮文化与黄飞鸿电影在学术研究中有强烈的依存关系,黄飞鸿电影是研究醒狮文化的重要文本[2]。学界既有研究表明电影不仅是记忆的表象也是记忆的建构过程[3],因此黄飞鸿电影中的醒狮不仅是制作者与观众故乡记忆的体现,也影响着观者对于故乡的记忆。由此,黄飞鸿系列电影成为大众媒介、传统文化与故乡记忆之间的交叉点。
从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起,后续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范式,记忆研究均与媒介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基于此,本文依托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发展脉络,结合电影的生产场域,以记忆相关理论分析醒狮这一传统文化是如何通过电影这一大众媒介,从具象表演变为故乡记忆和家国情怀之意象,如何表现并影响故乡记忆的传承。
二、文化传播中醒狮意象变迁与故乡情结显隐
在百余部黄飞鸿电影中,几乎每一部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醒狮表演,或作为背景或构成情节。黄飞鸿电影系列的发展大致分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70年代后期、20世纪90年代三个时期[4],伴随着电影本身的发展转变,影片中“醒狮”的文化内涵也从具象的民俗表征成长为家国民族的象征符号,而醒狮意象的流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粤籍移民故乡情结显隐的重要反映。
(一)具象民俗——作为“镶嵌物”的醒狮与暂离的故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飞鸿电影大多由胡鹏执导,粤剧演员关德兴扮演黄飞鸿。在这一时期,电影中的主人公被塑造为一个以广州为活动中心的市井英雄,而舞狮通常是主创刻意安排,事关武馆声誉的比拼[5],并有着十分具象化的展现。《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作为黄飞鸿电影的开篇之作,开场便是一段长达六分钟的醒狮表演。其后,在关德兴主演的60余部黄飞鸿电影中,醒狮也是不可或缺的场景。这一时期,醒狮成为黄飞鸿电影中的镶嵌物,有时甚至并不参与电影情节的推进,仅是制作团队精心设计的表演[6]。创作团队在醒狮这一民俗的应用上完全是出于自身对于广东的了解,因为醒狮是创作者与观众共同的“家乡特产”,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艺术加工就能唤起观众的共鸣。“《黄飞鸿》能够屡创粤语片的最高卖座纪录”[7],也从侧面证明醒狮表演符合观众的文化基础和地缘情感。
对于在港粤籍人士而言,即使20世纪50年代,故乡成为暂时无法返回的物理空间,但广东在许多人的回忆空间里依然是种种具象的事物,因此他们自然而然能够理解电影中的广东意象。黄飞鸿电影的“井喷”也从侧面证明广东移民与故乡之间的联系正在薄弱,因为“只有当现代人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家或失落了家园时,谈论家的意义才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8]。故乡的影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他们与故乡物理连接中断的缝隙。更重要的是,只有观者与故乡产生过实质性接触,电影才能通过展演广东意象发挥故乡记忆的黏合作用。
(二)奇观展演——作为电影噱头的醒狮与远去的故乡
20世纪70年代,黄飞鸿电影开始走向衰落,不仅数量锐减,电影的主创团队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大致发展出两种方向。一种是以《醉拳》为代表的颇具喜剧色彩的电影,虽以黄飞鸿为主角,但与醒狮无甚关系;另一种则以刘家良执导的《陆阿采与黄飞鸿》《武馆》为代表,虽依然保留了醒狮这一岭南特色,但影片中呈现的醒狮表演难度却远超作为常规民俗的醒狮表演。这类影片中醒狮与其说是黄飞鸿武学造诣和处世哲学的具象表征,不如称之为创作团队以醒狮这一器物创作的奇观表演。
电影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独特的香港地域文化已在形成[9]。此时,黄飞鸿电影创作者所面对的观众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大多出生在香港,甚少与广东产生过实质性联系,黄飞鸿生活的广州于他们而言只是父辈口中“远去的故乡”。为了迎合新的消费潮流,电影创作者试图通过侠客的成长故事吸引年轻的电影观众,醒狮在黄飞鸿电影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只是,此时走进影院的观众更追求视觉上的刺激性,醒狮意象沦为电影中的一个奇观化的精彩“噱头”。这一时期黄飞鸿电影的萧条产量说明迎合观众喜好改造的黄飞鸿与醒狮并没有引发年轻观众的直接追捧,电影的创作者没有为醒狮增添新的文化内涵,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一代观众与醒狮这一传统岭南文化之间的联系。
(三)睡狮惊起——作为民族符号的醒狮与情感中的家国
1991年,由徐克执导的《黄飞鸿之壮志凌云》上映,黄飞鸿电影沉寂多年后,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此后徐克又担任导演或监制,制作了六部“叫好、叫座”的影片。在徐克的电影中,“醒狮”元素被保留下来,但醒狮意象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态。徐克对鸦片战争等近代中国历史事件的调用,使这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黄飞鸿从“市井英雄”转变为“民族英雄”,影片中醒狮场景也从广州街市转移到近代中国与殖民者的冲突现场,醒狮意象开始具有民族张力。同时,“狮头不落地”这一醒狮传统规则也被反复提炼,转化为中国人顽强不屈民族意志的象征[10]。徐克电影中具有家国色彩的“醒狮”与中国近代发展史中的“醒狮”形成共振,使得“醒狮”作为家国意象的民族文化表征更为深入。电影的票房则证明了徐克对于黄飞鸿和醒狮的阐释符合观众的集体情感需要。
三、文化传播中的媒介意象供给与故乡记忆维系
醒狮是粤籍移民故乡记忆中的一部分,坚持醒狮这一传统既能维系其与故乡之间的联系,又能标明自身的地缘身份吸引同乡,使故乡记忆在同乡之间的日常交往中得到巩固。但是关于故乡醒狮的情境记忆需要依托媒介才能实现稳定与传承。
(一)故乡记忆的媒介依赖与流动协商
记忆在媒介中出现后便能够独立于人的认知系统而存在,“社会的记忆和遗忘能力,必须归结为文字、印刷媒介,以及后来的整个大众传媒机器”[11]。电影在记忆传承与延续中尤为重要,年轻一代“是把影片中的画面当作对历史本身忠实模仿而加以感知的”[12]。对于早期的粤籍移民而言,故乡记忆是清晰的,因而只需要电影展现故乡之影像即可。当原始记忆淡化2723d92bf74bb9e7874f2bae038d6c31之后,电影中的场景也就从故乡之影像变成其故乡记忆的影像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开始兼具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含义,人们可以怀念空间意义上远离的故乡,也可以怀念时间流逝中远去的故乡。故乡记忆的媒介依赖性随着时间流逝和空间距离加大而逐渐增强。
在黄飞鸿电影中,醒狮意象是不断流动的,从具象民俗沦为奇观展演,继而又在下一个发展期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一流动过程既与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之间的意象协商有关,也与过去和当下之间的记忆协商紧密相连。醒狮意象的变化意味着电影制作者与观众之间处于不断流动的协商过程,二者对于醒狮意象的理解并不总是趋于一致,不同的理解既与个体经历有关,也与一个时代的经济水平、文化形态、集体情绪紧密相连,只有在不断协商的过程中,电影制作者与观众之间才能对醒狮意象代表的故乡记忆达成一致性理解。更重要的是,记忆也是“一种流动的协商过程,一方是当下的欲望,79310abee4d5bff270d6ffbbfafe23dc另一方是过去的遗产”[13]。社会发展的需求和集体情绪的变化影响着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对醒狮意象的意义赋予与解读,醒狮所代表的故乡记忆因而在过去传统与当下现实之间不停流动。
(二)大众媒介的意象供给与受众的主体能动
大众媒介不是纯粹的中介,它对内容的呈现受到大众和自身媒介特性的双重影响。鉴于电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其供给观众的记忆意象能够一定程度上参与观众故乡记忆的建构,但是作为记忆主体的观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倾向于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意象进行记忆生产。
黄飞鸿电影的出现与发展正值香港电影腾飞的时代,因而黄飞鸿电影几乎独揽了醒狮意象的供给。电影“为行动者提供了充分结构化的符号学事件,行动者可以出于各自的生平背景,用这些东西来生成意义、知识或者价值评价”[14]。在早期的黄飞鸿电影中,观众因为与制作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情感导向,自然能够将电影中的醒狮理解为故乡意象。但是,媒介对过去的再现只是“决定着谁的特定记忆场合和阐述将被视为具有相关性、何种记忆供应有机会得到社会的接受”[15],电影制作者与观众之间并不总能达成意象一致,20世纪70年代后期黄飞鸿电影的消沉便是证明。20世纪90年代的黄飞鸿电影赋予醒狮意象以家国内涵,使其从简单的故乡怀想成长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新的醒狮意象符合观众的集体情感,继续在故乡记忆的生产与传递中发挥作用。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之所在,也是唤醒精神“故乡”的不二选择。从黄飞鸿电影中醒狮意象的作用与衍变经历来看,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备凝聚共同体的力量,而且能够根据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进行合理的内涵扩展,发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能够发挥凝聚作用的民族集体记忆,但集体记忆需要在媒介中被使用才能走进现实,因此需要在合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充分调动媒介的意象供给能力。故乡终究在物质层面一去不返,故乡的影像是难以真正重现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提供的是故乡的意象,这些意象通过大众媒介的再现功能,以熟悉的场景、人物、风俗搭建出符合现代人情感与记忆的影像故乡,为现代人提供归属感,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助力。
[本文为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项目“郑成功形象海外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研究”(JDGTT20211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彭伟文.从市井拳师到武术家的理想代表:早期黄飞鸿电影英雄形象的建立与其社会背景[J].民俗研究,2013(6):10.
[2]姚朝文.黄飞鸿叙事的民俗电影诗学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65.
[3]李娟.中国电影记忆与国家形象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姚朝文.黄飞鸿叙事的民俗电影诗学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47.
[5]姚朝文.黄飞鸿叙事的民俗电影诗学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89.
[6]彭伟文.从具象到抽象,从市井到民族:民俗元素在黄飞鸿电影中的记忆建构作用[J].民俗研究,2015(6):57-67.
[7]刘郁琪.想象的救赎:香港武侠电影的叙事演变与文化转型(1949-1997)[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0:16.
[8]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0.
[9]赵卫防.香港电影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扫描[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5):31-36.
[10]吴匀.通俗叙事与喻象符号:《黄飞鸿》电影中“国家形象”的考察[J].当代电影,2009(1):100-103.
[11]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232.
[12]哈拉韦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6.
[13]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198.
[14]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246.
[15]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504.
作者简介:张姣,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广州 510000);吴万昕,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广州 510000);曹轲,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000)。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