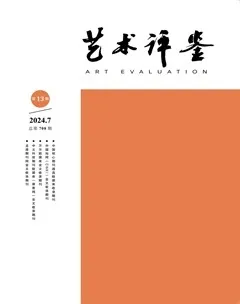从《潜伏》《孤战迷城》等谍战剧看时代巨变下的角色塑造
【摘 要】影视作品需放置于真实的时代背景下,以增强剧本的张力和吸引力。谍战剧主角通常被塑造为具有坚定信仰的地下工作者,但这种模式可能导致剧情单调和观众审美疲劳。《潜伏》中的主角余则成展现了从懵懂青年到成熟地下工作者的转变,而《孤战迷城》的主角欧孝安则因脑部损伤而产生身份怀疑,相较之下,后者的处理显得较为刻意。谍战剧中人物信仰具有多样性,除了坚定的信仰者外,还有像《潜伏》中的谢若林这样只信仰金钱的角色,以及吴敬中这样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们的行为超越简单的阶级立场或政治信仰。谍战剧不应仅仅展现坚定信仰之间的对抗,而应更多地反映利益、人性、政治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博弈。现代谍战剧《对手》则将间谍放在日常生活中考量,反映国安部门如何将境外间谍绳之以法。人物信仰的转变往往受到个人经历的深刻影响,伴随着内心的挣扎和彷徨。谍战剧通过展现信仰的多样性和人物的多面性,为观众提供了更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关键词】谍战剧 角色塑造 人性抉择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4)13-0146-06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影视作品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传递历史信息、反映社会现实,以及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谍战剧这一类型,以其紧张刺激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塑造,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然而,谍战剧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以及如何在展现人物信仰多样性的同时,深刻反映人性复杂,成为创作者们不断探索的问题。本文主要探讨时代巨变下谍战剧中人物角色的塑造,揭示人物信仰的多样性和人性的彷徨与抉择。谍战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反映,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真实的背景和架空的人物
近些年来的影视剧有一个趋势,就是尽量不出现真实的人名、地名,不光现实题材为了避讳真实地名带来的一些不必要麻烦,历史题材,尤其是近代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也开始架空和虚构。《潜伏》中直呼其名的“戴笠”“毛人凤”,在近些年影视作品中多用其他名字代替,或者如《孤战迷城》中只出现“戴局长”之类的称呼,而避讳全名。真实的历史事件,除了抗日胜利、解放全国这些人尽皆知的大背景之外,许多社会背景也存在架空的情况,不似《潜伏》里从余则成口中和广播电台里都可以不时听到例如某某国民党将领投诚等,这些新闻事件也为整部剧集的时间脉络提供了非常真实的锚定,让有心的观众可以按图索骥地厘清故事时间线。
《孤战迷城》开篇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这是为数不多展现抗日期间国民党军队赴缅甸抗击日寇的场景,反映缅甸远征军的影视作品非常稀少,一方面是战场远离中国本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或许是构成远征军的都是国民党部队。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志不能出现,如电影《八佰》中部分镜头被删减或许就有类似原因,而其他剧集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帽徽也只能模糊处理,或尽量少出现。《潜伏》中就不乏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背景的角色,但无论其身份为何,身在何处,在抗日期间的目标是一致的。一部好的谍战剧,它的主角和部分配角是可以架空的,艺术高于生活,角色的构成也应该是对大量真实人物的提炼,但故事必须放在更为真实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让观众感受到时代巨变带来的剧本张力,也更能促使观众在波诡云谲的历史迷雾里探寻线索。
在谍战剧的创作过程中,将真实背景与架空人物巧妙结合是吸引观众的关键。近年来,随着影视制作技术的提升,以及观众审美的多样化,谍战剧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更加细腻和立体的趋势。谍战剧的创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艺术加工,使他们既能展现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又能展现个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谍战剧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好真实与虚构关系的挑战。如何在保持历史真实感的同时,让观众感受到故事的张力和人物魅力,是谍战剧创作者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一方面,创作者需要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力求在细节上还原真实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增强故事吸引力和可看性。谍战剧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加工,塑造出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是谍战剧赢得观众喜爱的重要因素。
二、坚定的信仰和彷徨的人性
在讨论影视剧人物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人物的成长。谍战剧主角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一般都是共产党安插在敌对阵营的地下工作者,许多影视作品也会把主角塑造成信仰坚定、身手了得、机智过人的形象,但观众在看主角克服了若干个难题、打败了若干个对手之后,不免有些无聊,因为观众知道主角肯定不会死、任何困难主角也都能过得去,顶多就是看他怎么过,中间再穿插一些爱情、喜剧、惊悚元素,这便是不少谍战剧的标配了。
2023年的《潜行者》几乎是全方位模仿《潜伏》的一部作品,从名字到人物,同样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敌对阵营,也同样是乡下来的老婆和高学历、高智商的男主角共处一室后闹出诸多误会和笑话,但关键是《潜行者》里黄晓明饰演的方嘉树除了有过人的身手和超人的智力之外,他的人物在整个剧集中几乎没有成长线,只能用不可思议的道具(如假死药)和开挂一样的剧情来推动故事往下走。这种高智商特工加莽撞村妇的人物组合,在其他影视作品中并不鲜见,如果只是想通过这类人物形象上的冲突来制造喜剧元素或营造悬疑气氛,用过一次两次就不再新鲜,也很难撑起一部三四十集的优秀谍战题材剧。
反观《潜伏》,余则成从一名懵懂青年到军统特务,再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其具有清晰和完整的人物成长线索。他被军统派去刺杀投靠汪伪政府的叛徒李海丰时,他对军统的认识还停留于抗日救国,后来诸如戴笠利用军用船只运输个人走私物品、军统站内从站长到科长人人贪污营私等事实,让余则成对国民党逐渐失去信心,转而弃暗投明。他的信仰始终是为国为民、抗击外敌,但其面对初恋女友左蓝奔赴延安、上级吕宗方被证实是共产党等现实,他是有过彷徨和犹疑的,不过后来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更加坚定了余则成的信仰和立场。
《孤战迷城》里,主角欧孝安也有一个从军统特务向中共地下党转变的过程,同样也是有一个地下党的上级被杀,对其思想有所触动,但这个过程中因加入欧孝安被日军人体实验后头脑不清带来的记忆混淆情节,使其对自身身份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来自人性本身的发端,而是物理层面的脑部损伤,这在某种程度上相较《潜伏》中余则成的内心挣扎,就显得有点刻意,甚至狗血了。尤其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反复纠缠于军统重庆站里黎少堂和苗江二人的日本间谍身份,相较于前半段的情节显得拖沓啰嗦,如果能少注水一些,40集完全可以紧凑到30集内。最后的结局又是以欧孝安开挂加超人的主角光环设定,个人英雄式地挫败了日军所谓的“落樱计划”,抗日神剧中任何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的夸大描写都是对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艰苦卓绝赢得最终胜利的一种亵渎。而这个萦绕在整部剧集中的中日多方聚焦的宏大计划,竟然只是日本战败后在胜利庆典上释放毒气弹,以期毒杀国共多位将领。且不论这个计划真的实施能够带来多大杀伤力,仅以当时日本已然战败的背景下,这种无法扭转战局的破坏行动有何重要意义可言,又何须之前费如此大的周章来铺垫这个“落樱计划”。
三、矢志不渝和多头下注
无论是《孤战迷城》《潜行者》,还是近几年其他谍战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人物角色的信仰光环放得非常大,不光是主角如此,其他配角也类似,即好人、坏人的分别太过清晰,而且他们的动机也很明确,分属国民党、共产党、日本等不同阵营。2013年有一部谍战剧《风筝》,讲的是国共在对方各自安插的一个间谍,剧情很吸引人,但同样的问题在于这两位主角的立场太过清晰,他们在各自敌对阵营潜伏多年,甚至到了解放后,他们的行为与其自身信仰都发生某些背离,但结局仍然清楚地告诉人们,他们的政治理念从来没有改变。
回看《潜伏》发现,虽然也有李涯这样的死硬分子,他不像军统里其他人那样贪得无厌,唯有盯着余则成偶尔不经意露出的小漏洞,死缠不放,但有几个细节很可能是后来的许多影视作品都回避或者没能表现出来的,即贪婪本性许多时候是超越阶级立场或政治信仰的。典型的就是《潜伏》里谢若林这个角色,他自称“没有任何信仰”“只信仰真金白银”,谁给钱他给谁办事。他提到,当时在重庆、上海等地,都存在情报交易场所,有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以及其他人等,他就是一个情报掮客。这虽然听上去很匪夷所思,但却是最符合当时的历史。尤其是在上海这个地方,各路势力汇聚,情报贩子手拿不同国家、渠道得到的情报互相交易,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形。这些情报交易场所不光是掮客们热衷出入的地方,不少真正的间谍,甚至这些间谍背后的政治势力也都在进行交易,比如把低等级的情报拿去换取对于自己更重要的情报、把盟友的信息去换取敌方的情况等等。
不光谢若林这类贪财之徒,即使是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不也是一门心思捞钱、转移财产、为战败之后如何身退做打算么。吴敬中对余则成的信赖和偏爱,一方面固然有余巧思计谋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吴就算嗅到余身上的中共气息,也不免暗里思忖是否可为将来留一条退路,毕竟说起来余是自己的学生。而最后他执意带着余则成飞赴台湾,更让人觉得不单纯是喜爱这个学生,更可能的是退守台湾之后,万一将来退无可退,学生余则成是不是会念在多年师生故旧的情分上,保自己一下呢?
从更高的维度来看,余则成之前被举报调查过这么多次,国民党高层难道就没有怀疑?从各国谍战历史来看,有些时候明知此人是间谍,也会留着不动,有些是怕打草惊蛇,有些是想引蛇出洞。同时,间谍在被敌人识破抓获之后,有些人当然会选择自杀,如果自杀不成,有些情况下间谍是可以有选择性地透露一部分情报,但一般需要扛住一段时间的严刑拷打,让自己的队友能够撤离或者销毁资料,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一点一点地往外吐情报。这从侧面也反映了谍战本身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坚定信仰之间的对抗,更可能是利益、人性、政治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博弈。在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最后和曾经逢场作戏、暗恋自己的晚秋在台北成为夫妻,而王翠平只能抱着余的遗腹子站在土坡上遥望夫君不知何时归来,确实有一种命运弄人之感。
最近仍在热播的《孤舟》,虽然剧情有许多可商榷的地方,比如主角顾易中只是个刚刚受训完成的菜鸟特工,却能够把老江湖周知非玩得团团转,几次经历枪林弹雨、生死大劫,都能够毫发无伤,张颂文扮演的周知非有一句台词:“所有的特务工作都是为政治服务”,《潜伏》里没有明讲的内涵在这句话里被挑破了。而周知非本人身体力行,他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叛变到中统,也可以从中统叛变到汪伪政府,他是一个没有“主义”的投机分子。这一点和谢若林倒有几分相似,只不过是在求财和求权方面略有差别。同时,既然是为政治服务,无论是周知非、谢若林,还是周的老情人中统派来劝降的特务区昕萍,都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随时可以被舍弃或交换,区昕萍带来的王牌杀手完成任务后却饮弹而亡就是最好的例子。周知非只是一个为了生存和利益而不断变换立场的投机分子,正如政治棋盘上的棋子,随时可能被牺牲或交换。这种剧情设置,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也让观众对那个时代特务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四、地理空间和时间跨度的拓展延伸
大部分的谍战剧,包括以上提到的几部,多半会将时间聚焦于抗日和解放战争时间,尤其设置于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同时这也造成题材在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孤舟》就把地点搬到苏州,不再是耳熟能详的七十六号魔窟,而是汪伪政府在苏州的九十号特工站,剧情还在徐徐展开,但以吴侬软调为背景的苏州评弹确实让谍战剧迷耳目一新。
上面提到的谍战剧都是年代剧,若干年前的《琅琊榜》和《风起陇西》让人们看到把谍战元素放入古代背景中的常识,并且事实上获得了非常好的艺术成就和观众口碑,甚至在评分上远超许多经典谍战剧,可见跨界和交融也是谍战剧未来自身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2024年另一部年代戏《天行健》选取清末宣统年代,即清朝即将土崩瓦解的这个很少被触碰的年代,而且也融入谍战、武侠、罪案等不同元素,收获很高的点击率和好评,同时,也为谍战剧在概念创新上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天行健》从剧情来看非常有吸引力,但也有着之前提到的类似问题,比如:几个角色的主角光环太强,怎么打都死不了,但到了最后为了追求悲剧效果,在最后一集里让所有角色都一个个惨死,逃出生天的男女主人公也被安排以字幕的方式交代死于战场的结局,这样的安排可以视为编剧对个人归宿的无奈,但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显得过于刻意和不符常理。
在谍战剧中,大多数是年代戏,有一部为数不多的现代戏《对手》,很值得一提。近些年的现代戏为了避嫌,几乎都对地名做模糊化处理,《对手》也是将背景设定为“厦州”,不过可以一眼看出来是厦门,因为出现了厦门的若干地标,比如南普陀寺等,故事讲的也是台海之间的间谍战,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国安部门如何一步步将境外间谍绳之以法的过程。现代谍战剧《对手》,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将间谍放在日常生活中考量,脱离了许多谍战片中主角无所不能、同时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错觉。郭京飞和谭卓饰演的一对夫妻,是中国台湾在十八年前派到大陆的间谍,当时绑架重要科研人员的任务失败,二人就在原地潜伏,后来假戏真做成夫妻、生了女儿。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继续执行任务,丈夫开出租、妻子做老师,表面看来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也面临着其他家庭的日常问题,比如中年危机、女儿学业情感问题等。在二十来岁刚被派来的时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坚信自己可以完成任务、回到对岸,但在十八年的岁月蹉跎中,柴米油盐、鸡飞狗跳的生活消磨掉任何意志。这部剧可以被看作是穷人版或日常生活版的《史密斯夫妇》,难能可贵的是《对手》这部剧里主角几乎没有开挂的技能,而且经常迫于微薄的收入,陷入人生的困顿中,令人不免唏嘘间谍也可以如此囧破。
《对手》中的间谍夫妻一直在面对人性抉择上的挣扎,而且越是陷入生活的泥沼,这种挣扎越是剧烈,但美中不足的是,剧中国安部门的人员都是正面形象,而且和许多罪案和公安题材的剧集类似,颜丙燕饰演的副处长段迎九为了工作不顾家庭、不顾孩子,同时自己也身患重疾,这样的处理当然有其原型,但也不免脸谱化。剧中唯一一个被塑造成赌球成性、以泄露机密消息换取金钱的角色黄海,最后也被证实是段迎九有意为之的诱饵,这反过来更加凸显了一种悲苦的刻板印象,就是为了完成工作,必须不惜欺骗妻子、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人见人恨的赌棍,观众可能会惊叹和赞许,但很难共情,这不是说无法理解段迎九的付出,而是几乎没有人想成为段迎九,或者是成为她的丈夫。这类国产剧中正面形象人物的处理其实都忽略了普通人对其的关照和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产剧,包括像《对手》这样的现代谍战剧,反面人物更容易获得观众共情,更容易留下深刻印象,也更容易让角色在表演上出彩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人物的信仰往往受到其个人经历的深刻影响。例如,《潜伏》中的余则成,他的信仰转变是基于对共产党理念的逐步认同。人物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的信仰。而对于如《对手》这样的现代戏谍战剧,在剧情的处理中不免会面临许多掣肘,一是正面人物的坚定信仰和道德品质需要一以贯之,以此衬托反面角色的卑劣和龌龊,二是反面角色虽然可以处理得更加多样化一些,但由此导致的问题往往就是反派比正派在角色演绎和人物塑造方面要更出彩。
人物在信仰转变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内心的挣扎和彷徨。这种彷徨可能源于对现实的困惑、对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落差,或是对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在谍战剧中,人物的信仰转变可能涉及政治立场和道德判断的冲突。一个人物可能因为对某个政治团体的失望而转向另一个团体,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面临道德上的自我审视和质疑。
人物的信仰转变可能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在谍战剧中,有些人物可能因为利益的诱惑而改变自己的信仰,或者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进行投机。人物的信仰转变也可能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如:亲情、友情、爱情等。这些情感关系可能会对人物的信仰选择产生深远影响。谍战剧中的人物往往具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之间的冲突和交织使得信仰转变过程更加复杂。人物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现出不同的信仰和行为,这种多面性使得信仰转变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通过这些方式,谍战剧展现了信仰的多样性,使得剧情更加丰富和引人入胜,同时也让观众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时代背景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高源.电视剧《潜伏》人物改编策略[J].戏剧之家,2020(19):116-117.
[2]舒雅.现实主义视角下当代谍战剧的“反类型化”表达——以《对手》为例[J].声屏世界,2023(10):36-39.
[3]涂彦,谭佳名.建构模式·叙事功能·美学特质:谍战剧中“假夫妻”关系的戏剧性营造[J].视听,2023(01):50-53.
[4]魏凯端.浅谈国产谍战电视剧的类型化构建——以电视剧《潜伏》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22(23):164-166.
[5]武兆雨.论新世纪初期国产谍战剧的三重叙事维度[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98-102.
[6]夏亦舒,邓冰旎.探究我国谍战剧的人物塑造策略[J].戏剧之家,2024(15):156-158.
[7]肖军,陈鹏.近年来我国谍战剧的创作新意与价值体现[J].电影文学,2022(16):45-50.
[8]曾凡忠,毕蕾.新世纪以来国产谍战剧的叙事突围与审美变革[J].当代电视,2022(12):43-49.
[9]侯玥.从《潜伏》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电视剧途径[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
[10]郑丹.新世纪国产谍战剧英雄形象嬗变与叙事重构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3年.
[11]张翼.谍战题材电视剧的新突破——电视剧《潜伏》创作研究[D].上海:上海戏剧学院,2011年.
作者简介:沈启容,男,博士研究生,上海开放大学普陀分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影视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