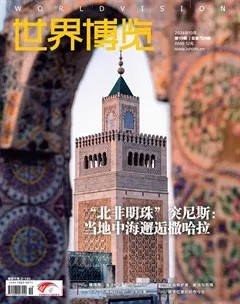德雷福斯案:世纪冤案与“知识分子”的诞生

德雷福斯案发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法国,是一桩名副其实的“世纪冤案”。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深刻影响了法国的历史。
无法判定的字迹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年10月9日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大区的一个犹太家庭。1893年,他进入法国陆军总参谋部,任见习上尉军官。然而一件小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对德国特别警惕,十分注重对德的情报搜集工作。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女特工巴斯蒂安以清洁工的身份暗中搜集德国的机密情报。1894年9月26日,巴斯蒂安在垃圾篓内发现了一些写给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的未署名备忘录的破碎纸片,上面列举了法国陆军参谋部的5份军事机密清单。很明显,法国军队里出现了“内鬼”。
法国陆军参谋部得知此事后,立即展开了清查,很快将怀疑目标锁定到了德雷福斯身上,除了他的字迹与备忘录上的字迹相似外,还因他是犹太人。10月15日,德雷福斯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被逮捕。12月19日,由7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进行了秘密审判。德雷福斯被定罪的唯一证据就是那份备忘录,陆军部便请笔迹专家前来鉴定。法兰西银行的专家鉴定后认为其中存在重要差异,但巴黎警察总署的侦探学家得出了两者吻合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后者具有反犹倾向。
笔迹鉴定结果相互矛盾,德雷福斯坚称对备忘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但为了坐实他的“罪名”,陆军部部长梅西耶将军竟然授意属下伪造证据:亨利少校称,有可靠消息来源称德国间谍就是德雷福斯,但又不说出具体来源,只以军人的名誉发誓,即被法庭接受;迪帕蒂上校则编造了一份“秘密档案”,记录了德雷福斯从事间谍活动的事迹,还在德雷福斯的律师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偷偷交给法庭。
审判结果可想而知,德雷福斯罪名成立,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至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1895年1月6日,他在法国军事学院被“拔阶”。德雷福斯的军服被扯掉,军刀被折断,这是对军人进行的公开羞辱。
尽管大革命期间,法国成了首个授予犹太人公民权的欧洲国家,但国内仍有十分强大的反犹浪潮。普法战争后,法国与普鲁士签订了屈辱的《法兰克福和约》,全国上下仇德情绪空前高涨。德雷福斯正好撞在了时代的枪口上,成了替罪羊。


左拉的“我控诉”
德雷福斯被流放后,法国的军事机密仍在泄露,军方内部不禁怀疑内奸是否另有他人。真正让该案水落石出的是乔治·皮卡尔上校。1895年,他成了陆军情报局新任局长,有次他得到了一封国外特务写给埃斯特哈齐上校的信,继续展开调查,发现埃斯特哈齐的笔迹与那份备忘录上的字迹十分相似,就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军方高层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挖根刨底,重审此案,还将皮卡尔调离参谋部,派往突尼斯。
皮卡尔担心此行一去不返,便在离开法国前将这个发现告诉了他的朋友、律师路易·勒布卢瓦。勒布卢瓦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德雷福斯的家人也将案件具体情况广而告之,一时间法国社会再次热烈讨论此案,要求重审的声音也愈发高涨。另外,当时一位银行家发现,德雷福斯家人公开的备忘录上的笔迹与他一位客户的笔迹一样,此人就是埃斯特哈齐上校。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898年1月10日,军方对埃斯特哈齐进行了秘密审判,结果却是无罪释放。法国社会沸腾了,除了民众上街游行,很多作家、艺术家和媒体界人士也站在了时代潮头,批评政府和军方制造冤案,掩瑕藏疾。在这些大声疾呼的人当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
1月13日,左拉在法国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报纸《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信》,这一标题被当时的副主编乔治·克里孟梭(绰号“老虎”、后两度出任法国总理)改为了《我控诉》。
除了左拉,还有其他著名人士也参与了进来,比如阿纳托尔·法朗士(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莫奈(印象派领导者)等。德雷福斯案成了法国民众街谈巷议的司法案件,社会分裂为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权联盟”派和反对德雷福斯的“法兰西祖国联盟”派,还在欧美国家引发了强烈关注,成了一场国际瞩目的政治事件。

军方颜面尽失,1898年2月以诽谤罪的名义对左拉提起公诉,法庭判处左拉1年监禁,并罚款3000法郎。为此左拉只好流亡英国,坚称德雷福斯无辜的皮卡尔上校也于2月被革除军职,并于7月被逮捕入狱。
1899年,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的费利克斯·福尔在任上去世(在其葬礼上,“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还发生了冲突),2月,支持重审的埃米勒·弗朗索瓦·卢贝当选为总统,启动了重审程序,为彻查此案提供了转机。军方也重新调查此案,亨利少校被逮捕,承认了做伪证的事实,并于狱中自杀。牵扯进此案的多名陆军部高官被迫辞职,埃斯特哈齐则逃亡到英国。5月,最高法院主审法官认为“备忘录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齐所写”。6月,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判决无效,将该案发往军事法庭重新审理。此时,左拉回到法国,皮卡尔上校获释出狱,德雷福斯亦返回巴黎,一切似乎预示着云开月明。
1899年8月7日,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审理过程持续了一个月,但9月9日,法庭以5∶2的投票结果仍判决德雷福斯有罪,将刑期减为10年。这一结果再次激起了公愤。

在司法救济无果的情况下,卢贝总统只好给予德雷福斯特赦。一番考量,德雷福斯接受了特赦,同时发表了“清白宣言”:“共和国政府给了我自由。但若不恢复我的名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从今天开始,我将坚持为推翻这可怕的司法错误而努力,我仍然是这个错误的受害者。”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1903年,在总理埃米尔·孔布、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的支持下,德雷福斯案再次启动重审工作,而且这次交由最高法院而非军事法院复审。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院撤销了1899年的判决,宣布德雷福斯无罪。次日,法国众议院收到一项议案,请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军职,并授予其荣誉军团十字勋章这一最高荣誉。这项议案顺利通过。而那位追求真相的皮卡尔上校,同样被恢复了军衔,并且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同年10月,乔治·克里孟梭出任政府总理兼内政部长,皮卡尔被任命为陆军部长。
1930年,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的回忆录《德雷福斯案件真相》得以出版,书中说埃斯特哈齐就是真正的间谍,而埃斯特哈齐已于1923年客死英国。
一股新力量的形成
遗憾的是,左拉没有等到德雷福斯案昭雪的这一天,他于1902年9月28日与世长辞。
1998年1月,在左拉发表《我控诉》100周年之际,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发表了一封致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裔的信:“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它是个严重庞大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了国家的原则。可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因为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而且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爱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国与自己和解……”
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一词,很多人认为诞生于左拉发表《我控诉》的那一刻。在1898年1月23日的文章中,克里孟梭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形成了,“所有这些来自地平线上各个角落的知识分子,难道不是围绕某个理念团结在一起的标志吗?”
(责编:刘婕)

在《我控诉》这封公开信中,左拉以悲愤激昂的语调写道:“我控诉迪帕蒂·德·克拉姆上校,因为他是这次误判的始作俑者……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在这一桩堪称本世纪最大的司法不公事件中,也许是因为软弱,成了同谋。我控诉比约将军,因为他握有证明德雷福斯无罪的铁证,却加以隐瞒,从而与全人类、与正义站到了对立面……我控诉第一次军事法庭,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律,在不公开证据的情况下给被告定了罪;我控诉第二次军事法庭,因为他们服从了命令,将一个明知有罪的人无罪释放……在做出这些控诉时,我知道我面临着因诽谤罪而被起诉的危险……看看他们敢不敢把我带到法庭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地调查!”
(摘自《官军与间谍》,译者/李昕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