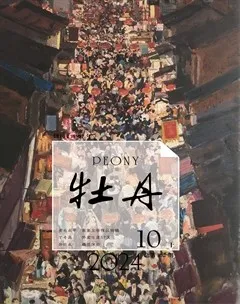客家红背带
邱裕华,江西省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读者》《散文》等报刊。
我是在母亲的红背带上长大的。
我的老家在赣中南的大山里,全村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客家人,落脚于此也不知有多少代了。犹如中国红一般的红背带,在我们那里,每家每户都可以见到。它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挚爱,联结着一个个孩子的幼年时光。
这样的红背带,在客家每一个出嫁姑娘的嫁妆里都有。它的做工很简单,择一块两三米长、一两尺宽的大红棉布条,缝边后拧起来即可,要是手艺熟练的裁缝个把小时就行了。但是,它质量上乘,能用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更重要的是,在这满满的中国红里,盛满了浓浓的祝福:祝福白头偕老,日子长长绵绵;祝福驱邪避凶,日子红红火火;祝福早生贵子,“背带,背带,带子带孙,子女满堂”。
红红的背带,一头连着新娘,一头连着新郎。结婚那天,新郎带着亲友,早早地出发,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来到新娘家。在阵阵唢呐声中,在鞭炮声里,新娘哭着告别不舍的父母,戴着红盖头,穿着红嫁衣,带上祝福,坐上婚车,开始向未来的生活出发。红背带的一头,是新郎幸福的笑脸,真心的承诺。红背带的另一头,是新娘的忐忑与期冀。穷也好,福也罢,新娘把自己的一生和新郎紧紧相连,许下对未来不变的夙愿与美满。
红红的背带,一头连着母亲,一头连着孩子。新婚之后,孩子很快出生了。农村家务活多,家里家外,灶前灶后,样样都需女人到场。襁褓中的孩子没人带,怎么办?红背带从嫁箱里拿了出来,年轻的母亲背着幼小的孩子在厨房里忙碌,在小河边清洗,在菜园里除草,在地里种庄稼,在圩镇上叫卖……初为人母,一开始背的时候,动作生疏,甚至还需别人帮忙,而且两个肩膀酸酸的,胸口也有些闷。很快,她就能熟练地应付了。她把红背带对中从孩子的两腋下穿过,然后微转身半蹲下,两只手各抓住背带的一头,轻轻一用力,孩子就到了肩膀上,然后将红背带从自己的肩膀拉下到胸前交叉,再往后裹住孩子的小屁股,又回到自己的胸前打上牢牢的结。这样,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地,子心贴母背,冷热相依偎。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犹如地里沐浴春风春阳的庄稼,她开心地唱着歌谣:“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唱着唱着,背后的小家伙打着细细的呼噜又甜甜地睡着了。
红红的背带,一头连着艰辛,一头连着希望。鸟儿大了,总要勇敢飞向天空。婚后的男人,理当成家立业。在农村,要是兄弟姐妹多,往往新婚不久,一对新人就需分家立户,开枝散叶。面对简陋的家舍,夫妻两人手握手,心连心,开始小家庭的谋划。红背带,牢牢地拴着一家人。盛夏时节,汗水湿了红背带,湿了母亲的肩背,也湿了孩子的衣襟。到了腊月,寒风吹来,出门时母亲给孩子盖9iryK9uv58sWApmFA7NsqpjGyAgPcdaRs79u5b4TcK4=上厚厚的棉披风。孩子饿了,找个背风的地方,把孩子放下喂口奶,解泡尿。没办法,生活总得朝前走,活儿那么多,日子和希望就在前方,年轻的母亲总要脚步不停息,才能赶上。要是夫妻怄气吵架了,她气不过,背上孩子就回了娘家。孩子他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过个一天两天,记挂着家里的活计,她又背着孩子从长长的山路那头回来了。寒暑交替,在母亲的背上,孩子一天天长大,不再需要母亲背着了。可是,又一个小生命出生了,红背带又出现在了母亲的肩上。
我出生时,我的母亲已经四十三岁了。那时,繁重的家务,让母亲天天都忙碌在生活的经纬线上。母亲是如何把我养育大了,我自然知之甚少。可是,我结婚后,母亲经常向我的妻子重复这么一个细节:冬天,母亲背着我上山捡柴火,等母亲手持柴刀砍好、捆好一大把柴火要回家了,只要母亲把柴火扶立在地上,准备背上肩头时,我总是立马把小小的脑袋偏到一边去,而且一路上都是如此歪着头,没有被那些粗糙的柴火弄破过脸颊。
我的母亲每说一次,妻子就会取笑我一回,说我小时候蛮聪明的。我却笑不出来。母亲捡柴火的山我是知道的,我长大后经常跟她去。在我们那儿,冬天农闲时节每户人家都要到山上捡好次年用的柴火,不然,开春之后没有时间,而且天热了山上也有蛇。那崎岖狭窄的山路,处处都是缠绕交杂的灌木、荒草和野藤,有些地方又滑得很,空手都不好走,母亲背着我,还要背着五六十斤重的一捆柴火,她是用了多大的小心和力气才得以平安地往返一趟趟的?
一条红背带,一生养育情。红背带,就像是第二条脐带,在婴儿出生后又重新把母亲和孩子系在一起。只是,在岁月的洗涤中,它渐渐褪色、破旧,不再那么红艳得如早春的花、深秋的果。随着红背带的褪色,母亲窈窕的身姿渐渐变得臃肿,坚挺的脊背渐渐变得歪斜,年轻秀美的新娘成了蹒跚的老太太。大了的孩子,像鸟儿一样飞向四方。
飞得再远也不用怕,只要循着长长的红背带,就能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