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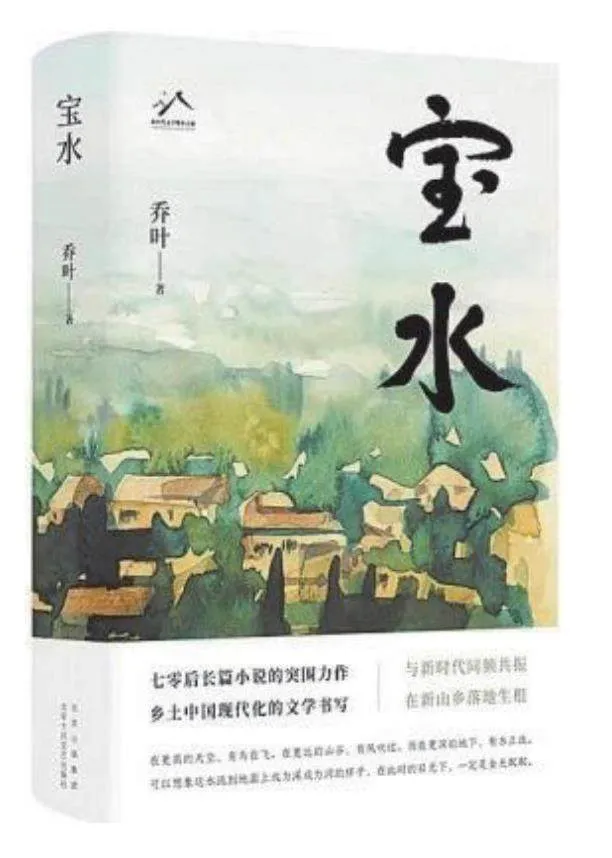
乔叶,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宝水》《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藏珠记》,散文集《深夜醒来》《走神》等。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2022中国好书、北京文艺奖、十月文学奖、春风女性奖等,多部作品被翻译为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
《宝水》这本书的上市时间是2022年11月,出版后跟读者交流了很多次,主题框架都是“文学和故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城市里,构成了市民的主体,但内心却牵连着故乡,虽然故乡可能在几千里之外,但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精神和血液里。
文学是精神的故乡
文学作品的节奏很慢,而北京、上海、深圳等这些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却是非常快的,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下,大家为什么还要读文学作品?这是因为信息交流的速度越快、传播的速度越快、发展的步伐越快,我们内在的东西越是需要慢下来、需要静下来、需要聚集能量。这时阅读经典就非常重要,尤其是阅读经典文学。就我个人的成长来说,文学是精神的故乡,文学从我小的时候贯穿到了现在的生活中。
我的写作始于散文,从1990年到2001年我以散文写作为主。2001年,河南省选拔青年作家到河南省文学院,我从基层被选拔到了河南省文学院,那时我已经出了七本散文集,《孤独的纸灯笼》是第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2002年我开始小说写作,这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颠覆性的成长。散文写作和小说写作很不一样。我年轻时的散文写作是比较平面化的,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想象、对人性的认识也是比较平面化的。我是在小说的阅读和写作中成长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有两个版本,银灰色的封面是第一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2018年,有一个出版社又出了一个修订版。其实,早在2004年3月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前辈就告诉我应该先写中篇和短篇,先写短的锻炼技术,但我没有听进去这句话,这是非常不成熟的一种做法,但我的运气比较好,虽然写得不怎么好,书却顺利出版了。成长总是有痕迹的,要有个过程。
文学是精神的故乡,这句话从精神层面上可以囊括很多,其中文学的传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感觉自己就浸润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中。茅盾文学奖评了11届,有50多部作品获奖,其中河南籍出来的作家有10位获了奖,占了很大的份额。虽然用这个数据做例证比较简单粗暴,但也由此可见河南强大的文学传统。我是去年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迄今为止我在北京工作了四年,在2020年之前,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南。我对传统文学资源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我年轻的时候写散文,后来写小说,早期也写了很多关于城市的小说,年轻的时候有叛逆心,希望自己写得很洋气,不想认领自己的乡土传统。后来发现自己特别想挣扎出乡土这个传统的时候,反而证明了这个传统是很强大的。我有一段时间写了挺多城市的文字,结果发现我比较受欢迎的作品正是带有乡土气息的。这倒逼着我去反思,我发现乡土还是很有它的价值。这个认识是不断在作品中体现的,在我的中短篇小说里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最慢的是活着》,它也是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
故乡是生长的文学
故乡是生长的文学。在《宝水》这本书里,我有两个向度的回归,第一是故乡意识,第二是女性意识。大家都说女作家只写女性,比较狭隘。还有这样一种论调,说高级的写作是雌雄同体的写作,女作家的作品如看不出作者的性别痕迹就很高级,因此我也写了很多男性视角的小说。别人说你写的一点都不像个女作家写的,我会认为是一种表扬,后来我认识到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我干嘛要这样别扭呢?干嘛要跟自己的本性对着干呢?他们说女性会狭隘、会有局限,那男性没有局限吗?因此它是一个伪问题。局限性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关键是怎么认识这个局限、怎么去破这个局限。后来我又回归到了女性视角写作。
我的一个小说集叫《她》,里面的小说全部都是女性视角的。我采取了一个试验性的做法,这些女性没有姓名,就是“她”,是各种各样的“她”的故事,这个“她”可能是一个搓澡工,或是一个家庭主妇,今年翻成了意大利语的《她》,图书的封面做得挺有意思的,中国版本做的封面是一个女人的背影,意大利的版本是正面和侧面的结合,艺术性挺好,在今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上展示了。
《宝水》可以说是我乡土写作的回归和女性写作的回归汇合到一起了。《宝水》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我比较喜欢授奖词里面说的几个“新”字,如“新时代”,“朝气蓬勃的新观念、新情感、新经验”,“在创造新生活的实践和人的精神成长中构造、融汇传统与现代、内心与外在的艺术形态”,“为乡土书写打开了新的空间”,这是对我的作品的高度肯定。从去年到今天,媒体提问时基本会问我一个问题,你跟前辈们写乡土有什么不同?我当然知道我在乡土文学链条上的传承使命,但是光有传承是不行的。我是“70后”的作家,写乡土的时候,我希望提供新的东西。什么是新东西?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城乡是二元对立的,城市是城市,乡村是乡村,大家都在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中,是相对闭环地运行着,城市意味着更高级的生活环境,摆脱农村户口就意味着人生的某种成功。李佩甫老师等前辈们很爱写乡村权力。究其原因,大概是村民都在一个村里生活,宅基地问题、计划生育问题、交公粮问题、分地等问题都在乡村内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就容易有矛盾,所以作家们都会写乡村权力。后来乡村解放生产力了,大量的青壮年都跑到城里务工,乡村面临着空心化的问题,留守儿童的问题,甚至有的地方撂荒了、没人种地的问题。国家层面也意识到这一点,近2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会谈“三农”问题,脱贫攻坚的问题,乡村振兴的问题。各种利好回到乡村,让乡村重新振兴起来,这是大的时代背景。
到我们这一代写乡村的时候,我希望写出现在乡村的各种状况,问题是有的,但它也是有生机和活力的。在《宝水》里我也尽量做了丰富的表达,提供出新的东西来。 我有一个获奖感言,谈了时代和文学的关系。我说故乡拥抱着我,时代拥抱着故乡。作家和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浪花和大海、庄稼和土地的关系。时代这个命题是特别大的,我每次去外面交流的时候,好多朋友、读者或者作家都会问你如何去写这个时代?其实我自己写作时,是不想“时代”这个词的,因为“时代”这个词过于宏大了。时代就像江河一样,它就在那儿,我们不可能把江河里的每一滴水放到杯子里,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从江河里取出这一杯水,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如何做大,而是如何做小,这是我的认识。怎样在时代的江河中取到自己的这一杯水特别重要,如果取好了,这杯水里面一定有时代的江河。
我经常做的事是跑村和泡村,跑村是看乡村样本,这是我的工作方法。面的关系就是看得多一点,但看得多肯定看不了很深,这是素材的广度。泡村就是点的关系,点位要扎得深,比较专注地跟踪几个村的变化,这是素材的深度。生活现场对我特别重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我着重想说的是认识照亮生活,很多人认为写小说和报告文学是一回事,以为我到村里去看了,然后我就照着这个人写小说了。报告文学或者新闻报道可能这么写,但写小说一定不行。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最后形成了一部小说,这中间要走过千山万水。
作家是在认识的过程中重新构建了故乡。我的籍贯是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这是我的实体故乡,但是当我把它放进小说中,故乡成为我的小说文本的时候,它就不是原来的那个故乡了,它是被我重新构建的故乡。我觉得这对所有的作家都适用。故乡用一草一木养育了我们,我们用一纸一笔再造了故乡。如果你是有过写作经验的人或者说你想写作,比如你是一个深圳人,当你想写你心中的深圳故事,你一定有自己的选择,也一定有自己重新的构建,你笔下的这个深圳就是你心中的深圳,你情感所在的深圳,是用自己情感的血肉重新构建的,这也是写作特别有意思、特别迷人的地方。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4南国书香节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