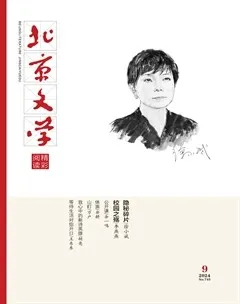小镇的春天
雷州半岛冬天极少下雨,干透了的黄土红壤上,风卷尘烟。到了春季,雨也不是痛痛快快地飘落,而是不分日夜地扬着毛毛细雨,好像担心久旱的土地一时承受不住水的饱喂。毛毛雨看起来轻柔温顺,却冷如冰水,冬天没有冻到的手脚,这时冻得裂开了血口子。那时小镇的人们冬天也依然穿着个拖鞋。乍暖还寒时节,春天已迈进来的这一只脚和冬天还没离去的那一只脚,跳着凌乱的舞步。毕竟还是到了春天,笼罩着烟雨的小镇,慢慢柔软了,温润了。一个冬天后有所褪色的镇子,被春风一遍又一遍补上了颜色,刷新了。
把小镇洗去灰尘的细雨,清明后悄然走远了。久违的曙光,轻松地穿过极薄的晨雾。半岛东岸的这个小镇,最早拥抱明媚的春光。
小镇在我国的热带区域。它换上春装后,那晃眼的绿,把人们从一个冬季的倦意中彻底唤醒。高大的凤凰树橘红的小喇叭形花儿,像爆竹般一夜间绽放了。人们在熟睡中似乎听到了花开的噼啪声响。姑娘们从树下走过,花瓣落在她们的头上。她们装着不知道。如果说这些是小镇春天的泼墨写意,改变大大小小院落灰暗色调的,则需要更多的工笔细节。房前屋后早就盛开的三角梅扮演了这个辛劳的角色。
在北方看到的三角梅,都是大盆栽的,成了名贵的花卉。记得人民大会堂国庆70周年招待会,装饰会场的多是三角梅。有常见的红和紫,还有黄的。团团簇簇,蔚如云霞。不是亲眼所见,不能想象三角梅还能如此气度非凡,如此雍容华贵。用过的请柬里,夹着的一朵三角梅,是从花丛旁的红地毯上捡起的。盛世给了三角梅无上荣耀。它见证一个古老民族史诗般的复兴。
花期很长的三角梅,开遍大半个中国。它不是我的故乡小镇所独有的。在那个庄严喜庆的场合看到它,自然想到小时候小镇的三角梅。巷口处,春天的微风吹动一丛早已绽放的三角梅。它薄如蝉翼翕动着,像一只只就要飞起的蝴蝶。
与高高的白玉兰树和凤凰树不同,三角梅贴着土地长,贴着土地开花。镇子里甚至用这些带着硬刺的三角梅做围墙。那时的镇叫人民公社。它办公的大院子,一大半围墙就是三角梅。院子里有栋20世纪初建起来的大洋楼。隔着公路,还有几栋公寓平房,百叶窗像窥视着什么。这是小镇近代的耻辱 ,一块伤疤。它最初是广州湾法租界的一个派出管理机构,叫镇公署什么的。办公楼两层楼,沉重的白色外墙包裹着一层,二楼廊道很敞亮,但该是栏杆的地方却是厚厚的墙壁,像坚固的工事。这批外来的占领者,没有忘记在院子装点一些他们认为的浪漫。春天里,楼前的几棵几乎没有叶子的鸡蛋花树,开着弱不禁风的黄花。楼后边有个小花园。好些的玉兰树,撑开巨大的几乎垂到地面的树冠。树下,落下来的玉兰花,拳头般大小,肥厚的花瓣正在萎缩。楼西侧,一片紫荆花下,青草覆盖的一层垃圾,踩上几脚,会露出掉光皮革的高跟鞋木坯。孩子们看着就奇怪,还有几分害怕,不知道这个张牙舞爪的东西是什么。法国番鬼把这块霸占的土地当成他们的小乐园了。世界上所谓的文明人常常做着这些美梦。日本鬼子1943年从镇子东南边的淤泥海滩,像强盗那样气势汹汹,爬了上来。法国人溜走了。新来的侵略者为了对付激烈抵抗,在办公楼前后又建起了钢筋水泥地堡。孩子们从长着野草的射击孔,看到里面黑黢黢的,于是从后面的一处凸起的门洞里摸进去,嚷着加码的赌注壮胆,在黑暗中爬过堆满芒稻壳的地道,总算看到了地堡的内部。陈年的积水和腐败的气味,吓得孩子们赶紧爬了出去。侵略者还在院子后面的山坡上修建了简易飞机场,跑道坚实的夯土,硬是被雷州黄牛拉着铁犁翻开,栽满新引进的小叶桉树,它成为雷州林业局林场的一部分。这都是后话。土地革命时就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南路武装,在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战斗中壮大了。抗日战争胜利,这片土地上的侵略者彻底败走。老人说,作为围墙藩篱的三角梅,是在这胜利的日子里,推倒厚厚的围墙种下的。我们看到它时,已经长得密不透风。它花开年年,不曾凋零,像这里坚韧顽强的人们。雷州半岛人,中原移民的后代,他们讲着保留不少古老汉语词汇句式的闽南方言,在那些屈辱的日子,血性无改,不辱祖先。
小镇春天里,还有来自远方的春水。新建成的雷州青年运河有条分渠,好像从镇子北面的天边落下。春耕前的小运河,灌满清冽的春水,欢快地荡起些只有急流才有的小漩涡,神气十足地穿过镇子,将东边的中学、小学与镇子分开。清静的校园迎来春季新学期。靠南一点的小学,响起清澈的童声,像突然飞回一群候鸟。老师带着孩子们,将教室里的桌凳,搬到校门前小运河的短桥边。短桥北侧,有个十余级的下河小台阶。小镇里的孩子,能吃苦,哪怕是一年级的孩子,也能将桌凳乒乒乓乓地搬到水中。没有刷子,他们就扎起稻草洗刷,不一会儿桌凳的木纹就显现出来。上个学期桌面上的涂鸦笔迹,洗去的是颜色,留下的是可以辨认的稚嫩又杂乱的划痕。桌凳焕然一新,仿佛轻了许多。一组组洁净桌凳,将伴随孩子们一个新的学期,留下他们成长的痕迹,像人生最初的年轮。小运河的水几乎要没过桥面,桥下的涵洞是看不见的。偶尔,桌凳会被涵洞里的水流吸走,漂到下游。那些渔民的孩子水性好,他们憋足一口气,逃过老师的眼睛,潜过涵洞,在短桥那边爬上桌凳。孩子们没有这么大的力气将桌凳逆流推回来,只有在桌凳被水边的小树挂住时,才能合力把它们拖拽上来,然后沿着小河堰抬回学校。挑头的孩子在校门口,会一个人钻到桌子下面,弓起腰,用并不结实的后背顶着桌子,像乌龟的模样。搬进教室时,当着老师和同学们的面,装出不喘粗气、毫不费劲的样子。他们是新学期受到班主任狠狠批评的第一批孩子。这些孩子却说,老师在底下真心表扬了他们。
代课的霍老师,踩着春风,走进小学校。这个学期,他还可以继续代课,没有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他是音乐老师,柔弱的身体,像贫瘠土地上长出来的竹子,风吹过总是摇摇晃晃的。一丝春风,一滴雨水,都是跳动的音符,打动着他的心弦。一个土生土长的小镇青年,对音乐如此敏感,细腻,倾心,执着,人们都说他投错了胎。校园里,他的步点透着弹性和节奏,一根细长的木棍子从不离手。在别的老师手中,这是教鞭,对于他,是乐团的指挥棒。他哪来的什么乐团么,只有教室里那些需要一句一句跟唱的乡镇孩子。后来,高年级教室里传出的无伴奏少年合唱歌声,散落在雨水打湿的春草上。大家说,霍老师的指挥棒真神奇。他备课桌子的上方,贴着卡拉扬的画像。他希望自己的偶像,能够每时每刻地看到他为播种音乐所做的奉献。哪怕是面对一年级的小朋友,他也是一丝不苟。他讲解简单的曲子,身体的一些部位,不由自主地神经质地颤动。孩子们陶醉于音乐,也陶醉于他的形体语言。他只是个代课老师,农忙假期间,还会肩扛犁具,赶着黄牛,下地春耕。生产队派什么活,他多不在乎。所以常常让他去最远的一小块地耕作。那一块水田,在山坡低处,周围一小块一小块水洼,浮着铁锈般的一层浮膜。走到了那里,已是太阳当顶,人疲牛乏。干不了一个小时,又要原路回来。晚霞中,牛饿得吽吽直叫。他被犁具压得更加摇摇晃晃。好在他生活在音乐里,摇摇晃晃的样子,仿佛只是被春风灌满,被春风陶醉。第二天,第三天,甚至第四天,他依然可以去那里耕地、插秧。他独来独往。他自由自在。他走在低矮浑圆的岭头,看得远远的。他呼吸着长长的春风,一路上哼着复杂优美的,在课堂里还不能给孩子们教唱的曲子。没有人知道其中就有他的原创。他歌唱小镇的春天。小溪欢快的流水声,山坡风中起舞的三角梅,回应着他的歌声。后来,他外出打工。人们以为艰苦的岁月,让他不再活在音乐的梦里。一天,收到他寄到北京的信,里面有他写的几首歌词,有吟咏春天的。这才知道他漂泊在广州,几十年的磕磕绊绊,蹉跎岁月没有湮灭他的音乐梦。这个时代不断给他希望。不知他消瘦的脸上,嘴唇上是否还留着浓密的胡须。他在信中让我在北京找个作曲家给他的歌词谱曲。一起当的代课老师,合用一间宿舍,我比别人更懂他的文字。不管怎么说,得想办法帮帮他。可是,找个合适的音乐人谱曲,并非举手之劳。工作一忙,竟然给忘了。不能怪他的歌词写得不够好,是我上心不够。想起来真让人久久内疚。
这几首歌词,已经遗失于杂乱的办公室。差不多能记个大概,这不是因为有还说得过去的记忆力。小镇的春天,美丽坚强的三角梅,清澈的流水,风中的歌,早已深藏于那时小镇里每一颗年少的心中。
特约编辑 蓦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