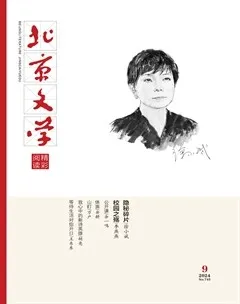诗人A与拾垃圾者B的故事
子时已过,A从书桌前站起来,活动了下身体,穿上大衣,从位于十七层楼的那个六十平米的房子里下楼,在小区院子里散步。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正值隆冬,北京却不似前些年那样冷得凛冽。光秃秃的树木在昏黄的街灯下显得萎靡不振,全然不似鲁迅后园的枣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天空也不是奇怪而高的,温暾混沌的空气直压下来,连趾高气扬的摩天大楼也仿佛矮了许多。
A觉得自己也如这空气一般,越来越温暾而混浊起来。
其实也无处可去。
A又回到楼下,靠在楼梯口那个长长的扶栏上,刚点上烟,果然又看到了B。已经连续几天了,每天大概都是这个时间,B像是从寒夜里突然冒出来,拎着一个大袋子,径直走到几个并排放置的大垃圾桶前,从里面翻出纸箱、瓶子等,一股脑塞进口袋,不一会儿,大口袋就鼓鼓囊囊,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几何体。但往往B并不立即离开,而是点上一支烟,靠在离A十米开外的扶栏上慢慢地抽。两人各自抽完烟,A乘电梯上楼,B和几何体消失于无边夜色。
这天,B装满口袋后,从衣兜里摸出一支烟,犹豫了一下向A走了过来。
“请问可以借个火吗?”
A摸出火机递过去, B点着烟把火机还给A,说了声谢谢,仍旧靠在十米开外的栏杆上慢慢地抽。
烟头明灭,映照着寒夜中两个人的脸。
A第一次朝那张脸打量了一下。蓬乱的头发下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棱角分明,但岁月的烟尘让人辨不清确切年龄。
或许他比我还年轻几岁。A想。
烟头再次明亮的瞬间,A恍惚从B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不安的东西,但又明显不同于他们这样身份的人常见的物质的焦虑。
这样相同的场景在连续几个夜晚重演几次之后,他们两人的眼神终于在夜色中碰在了一起。
A:“你是怎么干上这个的?”
B来自南部一个村庄。高中刚毕业时,也曾在去一所三流大学继续读书和打工之间犹豫过,最后他选择了外出打工。不过,B的打工只是断断续续的,且并不在一个地方扎根,挣些钱就回家,钱花完了再出去。前段时间,B没有外出,也没务正业,每日在村子里闲逛,且不定时辰,24小时都可能看到他的身影,但以晚上居多。
那天夜半时分,他正在闲逛,突然看到一个黑影从他一个远房堂叔家溜了出来。他睁大眼睛,夜色中却辨不清黑影的面貌。他索性跟踪过去,直到黑影溜进了村里那个最气派的院门。这个时辰以及黑影一路上左顾右盼的举动引起了B的怀疑。B的这个堂叔家有一个堂弟,常年在外打工,弟媳带着孩子和两位老人在村里过活。
B不由得想起了这个弟媳。她是B的中学同学,每次想到她,B总会联想到《雨巷》里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难道……B只觉头轰的一声,几乎站立不住,呆立片刻,两腿发软地飘回了家。
一连几天,B没去夜游,甚至白天也钻在家里。短短几天,B竟瘦了好多,像是生了一场病。B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在一个夜里,和上次差不多的时辰,他又悄悄来到堂叔家附近。然而,直到天亮,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偶有几声狗吠,夜色中的村庄静谧安详。且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那天所见之事在B的记忆中变得恍惚起来。又过数日,B差不多完全否定了那个记忆,甚至为自己的多疑感到可笑甚至一丝羞愧。他像被解除了魔咒一样又恢复了闲散。
可是,就在B又像往常一样在村里闲逛时,数日前出现的场景再次被他撞见。这次,被他强行否定的记忆愈发清晰地回到脑海。
每天,憨厚的堂弟、丁香一样的姑娘以及那个黑夜中鬼鬼祟祟的身影,交替在他眼前晃动。这次,他真的病了,像照了风月宝鉴的贾瑞那样,莫名其妙地一病不起。病床上,他突然瞥见挂在墙上的那件狗皮大衣,那是三十多年前父亲从西藏转业带回的唯一财产。
于是,一天夜里,他披上狗皮大衣,拖着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来到堂叔家附近。那晚的月亮天灯一样悬在头顶,他躲在堂叔院墙后面的暗影中蹲了下来。可是,夜半已过,始终万籁俱寂,甚至连声狗叫都没有,仿佛整个世界都沉睡了一般。
正当B松了口气准备返回时,大门突然悄悄开了一道缝,那个数日来萦绕在他脑海的身影再次从里边溜了出来。B只觉眼前一阵发黑,几乎瘫倒在地。他想都没想,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一头朝那个黑影扑了过去。黑影仰面倒地,B也像一条狗一样扑在了黑影身上。回过神来后,他迅速翻身爬起,惊魂未定中连爬带跑地逃回了家。
天亮后,B听说那人竟然死在了堂叔家门口。他惊惧不已,于是以打工为名,当天挣扎着离开了家。
A想象着那个场景。一个虚弱的病人,一张三十多年前的狗皮,竟然把一个大活人吓死了。真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第二天晚上,A和B靠着栏杆吸完烟后,把自己的一本诗集送给了B。
然而,接下来好几个夜晚,A都没有再看到B,有一次甚至等到天都快亮了,B也没有来。
大约一周之后,B终于又出现了。
“真没想到,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A。这几天,我把诗集读完了。”B说。
A仍然若无其事地抽烟,但内心竟颇紧张起来。
B接下来又说了些话,似乎是他对诗集的看法,但A没有能够从他含混杂乱的话语中捕捉到任何清晰的意见,只记住他说了一个词:语焉不详。
接下来B又消失了几天。再出现时,他依旧拎着那个大口袋,只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径自去垃圾箱里翻找,而是把口袋向A递了过来。
“这个送给你。”
A往口袋里看了看,昏黄的街灯下一个毛茸茸的东西,A确定是那件狗皮大衣。
“你要离开这儿了?” A接过口袋。
“可能有人要来找我,我得跟他们走了。”
回到家,A把狗皮大衣掏出来,挂在了书房的墙上。
果然,此后好多天,B没再出现。
一天夜里,A取下狗皮大衣,把自己的身体钻了进去。窗玻璃上映出了他的身影,A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形象,脑子里模糊地闪现出普罗塔戈拉曾说过的诗是一种外衣之类的话。
A脱下大衣,一点点叠好,装进口袋并用绳子捆了,塞进了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的缝隙里。
A从此再没看到过B。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