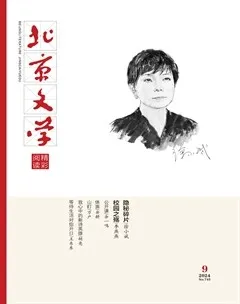生育史
一次次生育不仅繁衍出新的生命,也实实在在改变着一个女人的境遇——承载起十七次生育的是她隐忍缄默的一辈子。一位传统女性的生育史,照见了万千母亲的爱与疼痛。
亲爱的朋友,请您原谅我吧!
我把历史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进行拼接,
完全因为它附着了太多的苦难,
此外,还有我沉痛的祭奠……
我比庄墩子只小一岁半,但明显身单力薄,和他打架刚一上手,就感觉不妙,有点降不住他,我挨了他几记胖拳后,还被他骑在了胯下,真是窝火。
“×你妈的。”他的虎口用力地卡着我脖根儿,嘴里像喝了大粪一样臭不可闻。
我本想来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并将他掀翻在地,可他卡得我实在太紧,我都喘不上气来。我反抗了大约三五下,就耗尽了体力,只能在神志尚且清醒时翻着白眼,两只手臂放平,不再挣扎,以示弱。
“你叫我一声爷爷,说你服了。”
“孙子!”我宁为玉碎,也不为瓦全。
这时,我父亲走过来,像逮小猪崽一般把庄墩子从我身上抱了下去。“你哪能打你舅呢!再说了,他妈是谁?”
我迅速站起身,使劲扑打着满身的尘土,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掩饰自己战败的羞愧,并倚仗父亲在一旁撑腰,还放出狠话:“你再骂一句试试,看我饶不饶你。我撕烂你的嘴。”
“×你妈!”
庄墩子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可是我已经被他打得没有了士气,刚才他险些把我掐死。我心里十分感激父亲及时出现,才避免了我如三哥一样早夭。可是,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男子汉,也并不想就此罢休任人侮辱。但我一时又没有能扳回败局的能力和办法,便鼓足勇气强努着绝地反击,我也朝他开骂:
“你×我妈,我×你姥姥!”
“啪”的一声,父亲猛地一个大耳刮子抽得我脸上火辣辣地疼。“混他妈蛋!你说,他姥姥是谁?”
庄墩子的姥姥原来就是我母亲。我大概到了六七岁时,脑袋里才有些灵光,转过这个弯。怪不得父亲下手那么狠。
庄墩子和我打架那次,是母亲又给我生了弟弟,大姐带着他来娘家吃弟弟的满月席(实为一锅蒸白薯须子和白薯拐子)。
不过,当我彻底弄明白和庄墩子的亲戚关系时,我这个当舅舅的与那个混蛋外甥已然不打架了,准确地讲,是庄墩子早已沉没在一个芦苇塘的泥沼里有一两年了。关于庄墩子的意外离开,我并没有注意到大姐有啥情绪变化,因为那时她不但肚子里又揣上一个后来让我认为比庄墩子还要混的小混蛋,她腆着难看的大肚皮,稀里晃荡的两个奶子瘪塌塌地在破旧的褂子里悬垂着,没有一点精神劲,那年她也就二十出头或者不到,可完全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朝气和年轻女人的羞涩。那时她身边还多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外甥女,泥猴儿似的。
母亲,从十五岁开怀后,就一气呵成地没歇过脚儿,接连生了十七胎。直到她五十有二,赶上了一九八二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头班车,才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她作为女人一生最崇高而又最平凡,痛苦且快乐的漫长生育史。
女人生孩子如过鬼门关,不死也要活活撕下一层皮。分娩时揪心拉肝的痛苦过程,那是肉与肉生生地剥离,自然界里的动物们,不分语言和种群,都为之感动。乌鸦反哺,山羊跪乳,是流传了上千年的谚语。
在阴阳两界之间行走,每生养一次都可谓到鬼门关转上一圈。然而不知母亲是怎么想的,她好像丝毫都不在意,一切都是轻描淡写,每次生孩子都似闲庭信步。她为了她的孩子们,一切都无所畏惧,用她青春的炽热,从容无畏地闯过了十七遭。
母亲麻木而快乐地接受着我们的父亲——一个与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稼人,所给予她的疯狂粗鲁、无休无止的爱欲,占有,甚至是强迫,顺从地毫不腻烦地履行着作为妻子的义务,继而任劳任怨地再去践行和付出一个女人天经地义的母爱。十七次漫长的孕育和十七次痛苦的分娩,可想而知有多么艰辛。我们十七个捣蛋鬼的先后到来,几乎耗尽了母亲全部的心血和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光景。我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女人的最长的生育时间是多少年?有没有比母亲的这个漫长三十七年的跨度更长的?我还曾一度认为母亲能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我家好几个亲属和亲戚都生了十几个孩子,比如我的一个远房大娘,生了十四个儿女,我的一个姑奶奶生了十三个,我大姐的婆家一个老人,也生了十七个孩子,论孩子的个数已经比肩了母亲的纪录,但是她的最后一孩子降生时,是五十岁,而且人已经苍老、糊涂得不成,她说的数字只有她自己认可,她的男人却骂她不识数、胡嘞嘞,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是不是那个年代的男人,都是那副德行呢?
儿女,是母亲一生质朴的希望和全部拥有;也是她心甘情愿为之付出所有的重负和累赘。末了,母亲从生命的海洋中,只捞上来我们四男一女,兄妹五人。我们兄弟姐妹口中喊的大姐,也不知是第几位出生的姐,二哥也不知究竟是行二,还是应该行三或行四,就连我自己也不知自己该在的位置。天下那些当爹的人多半都是糊涂虫,我父亲只想着每晚“炖他的萝卜干”。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十七个?哪有那么多?”父亲瞪圆了牛眼扯开了嗓子,深深地怀疑着自己的勤奋。
于是,母亲掰着手指,一个一个地为他数说出哪一个是哪年来的,又是何时没的。生的是什么病,临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眼神……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她那五根粗糙布满裂纹完全失去了女人味的手指,时而伸直时而弯折地起起伏伏了三四次。
“老九,埋在大河沿那行柳树下了,这是你们的父亲回来时说的。”母亲无奈地叹气说,“可是他……老九没的那天,咱家里那条名叫大黑的狗,误吃了老鼠药也死了。”
“那有他妈的什么区别,都是一个死,狗死也是死,人死也是死,都是没良心的短命鬼。”
我是知道这个事的,母亲不止一回地说过,奶奶也不止一次地为此事骂过父亲。这件事,是父亲图省事,只在大柳树下挖了一个土坑,同时掩葬了老九和名叫大黑的狗。老九和大黑合葬了。
“我那九儿子还不如那条狗呢,狗还有个名字,老九还没有起名就糟蹋了。”
“狗是狗娘养的,老九是你养的。一个是人,一个是狗,品种儿都不同,能搁在一起比吗?”父亲梗着脖子以其独有的思维方式狡辩着,“要说,我最对得起的就是这个老九。其他的崽儿没了就没了,挖个壕,向里一扔,跟着三锨黄土,一埋。唯独老九,我还送了他一条狗当陪葬,他再转世投胎,嘿嘿……一准儿是他妈的二郎神!”
他的话,真让我觉得恶心。
母亲一辈子忙忙碌碌,但从没有离开过一个“穷”字。她和父亲成亲的时候,只有一间低矮破旧的土屋。小脚祖母趁她回门时,威严地指挥一伙人将父母亲新房里的摆设全部搬走了,原来那些家具不过是为了父亲结婚时家庭脸面好看,从村里别人家临时借来用的。就连挂着双喜字的门帘都是借来的。当母亲再次回到她的婚房里,房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她蹲在空空荡荡的土屋里,茫然无措,一时都不知第二天该从哪里过起。
一九六二年,生我养我的南梨村,那个只有几百口人的小村庄,在沉寂了三年以后,又听到了喧闹起嘹亮的、久违的且接连不断的婴儿的啼哭声。
那一年的秋天,大饥荒的恐怖阴影还未退尽,我便如期而至。也许,我用尽一生的时间都无法想象,我的母亲是忍受了多少磨难和痛苦,才让我挤进这美丽纷乱的人世间。
我从小是劈哑嗓音,几岁的时候,说话声就像一个成年人。青春期变声之后也没有改变过来,现在如果不看本人容貌,只听声音的话,我比电影演员曾志伟还像曾志伟。母亲为此半生自责,父亲倒是不以为然。
“你不住天地哭,有什么办法呢?”母亲说。
在我小的时候,每天清晨,天色刚一放亮,父母就要到生产队里出工,风风火火地去挣全家人的口粮。母亲把我放在家里,怕我被狗吃了,怕我淘气踩到炉火上,又怕掉到院子里的井里,也怕雄壮的大公鸡啄瞎我的眼睛……因为,在我之前,她已经有几个孩子死于各种不测,村里这种事情也偶有发生,母亲便下了“狠手”。每天上工前,便用一根手指粗的麻绳,一端系在我幼嫩的腰间,一端拴在窗棂上。我的活动半径大约有一根扁担长短,我的全部世界就是半幅火炕。我只能在炕上爬来转去,画我的半个圆圈儿。
“你就是那时候把嗓子哭劈了的。”母亲说,“前几天的时候,就只以为你找不到我,吃不上奶水,急得哭。几天之后才发现,那根粗麻绳把你的肚子和后腰都磨秃噜皮了,露出血淋淋的鲜肉。”
我对麻绳磨腰的事,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我二大娘家的三妹出嫁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岁了。农村没有耽误到那么大年龄才出门的女子,三妹算是个例外。三妹她童年时有一回不慎掉到了热粥锅里,上颌、脖子、前胸都被烫得皱皱巴巴。长大后,三妹总喜欢围围脖儿或穿高领衫。说心里话,她的模样长得挺好看的,明眸善睐,凹凸有致。但是村里人都知道她掉粥锅里的往事,能透过她的高领衫看到她布满烫疤的脖子。其实,远不止于此。我毫不违心地说,抛开世俗与近亲之伦理,如果让我娶她为妻,我也绝对不会愿意,因为我知道她的两个乳头都被热粥烫没了。
虽然我的嗓子劈哑了,说话不那么好听;虽然我有那么一段真正被束缚的童年时光,但是和三妹没有凸点的胸部相比,我觉得我已经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了。
母亲是受媒妁之言别无选择地嫁给父亲的。她是中国最末一批裹脚的女人。后来,国家倡导妇女翻身解放,妇女解放的明显标志是要先放开束缚女人的裹脚布。缠了一半的脚,突然被放开,长不溜丢圆个咕嘟的,样子非常难看。农民惯用身边常见作物比喻一切,这种缠得半途而废的脚,便被形象地称为“白薯脚”。母亲的脚也是白薯脚,但是她不喜欢“白薯脚”这个词,她更喜欢官家人那“解放脚”的叫法。
村里小脚女人不下大田干活。但是,脚解放了,女人平等了,半大脚的妇女们,每天也得与爷们儿一样去大田里劳作。
那年月里,老百姓365天都在不停忙碌,到了年底生产队核算分值,南梨村是方圆十里八村最穷的村子,一个工日只能核上几分钱。但是,正在孕育着下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我的母亲,仍舍不得耽误一天工。生产队里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每天8分,大着肚子揣了崽儿的女人一天最多只给记7.5分。母亲说,村里面怀孕的妇女,如果想挣到7.5分,那一定是个十分要强的人了,她必须要比挣10分的男劳力还要能干活,而且能多干活。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既感慨又自豪,因为她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生产队里唯一一个能挣到7.5分、怀上身孕的女人,就是她了。
平日里,收工回来,母亲无怨无悔地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深夜,她还要在灯下纳鞋底、织纱活儿,为孩子们缝补,一针一线地直到月上柳梢。
生产队没有休息日,但是若遇到雨雪天气,队员无法劳动的时候,那将是母亲难得的休息日。不用去生产队上工,但母亲也不会休息,还要手不闲、脚不停地收拾起永远属于她的干不完的家务活。
有时,我总乱想,缠足变成了解放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不把母亲的脚放开,不让它们解放,或许我的母亲和如我母亲一样的农村妇女,还能轻省一些,一生还会少干一些农活吧。
我排在兄弟姐妹中的第几位,我脑袋里始终是一团糨糊。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
母亲对子女的计数方式,是把她孕育的所有孩子,不论生死,进行总数排列。而父亲则只算活下来的我们几个。
“都死㞗的了,还算啥算?”父亲很讨厌母亲的算法,他心里觉得晦气。父亲还总是恶狠狠地斥骂那些死去的孩子是没良心的讨债鬼。我看到他骂人的时候,双眼间的眉毛骤然竖立,扭结到了一起,形容十分可怕。于是,我便从内心里发誓,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千万不能死了。另外,我也很惧怕死亡。我怕父亲偷懒,会把我和死狗埋在同一个坑里。或许是因为他制造一个孩子太容易吧,他不必像母亲那样费时费力,所以他才根本不会太在意我们这一群为人儿女者的恐惧。在他的眼里,我们究竟算什么呢,张开嘴等着吃饭的讨债鬼?死狗?还是随意可以擤甩的黏糊糊的鼻涕?
我每天都在努力地活着。尽最大的可能,让自己的生命力更加顽强。
在我的上边和下边,我记得清晰的,还有两个哥哥、两个以后夭折的姐姐和一个妹妹。把我拴在窗棂上是我母亲没有办法的办法。童年的我是孤独的,没有玩具,没有童话,没有儿歌相伴。于是,那些人是猴变的吗?我是从大河里捞上来的吗?这些稀奇古怪、天真幼稚的提问,就成了我反反复复询问母亲的唯一话题。
我从哪里来?
这个类似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沉浸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虽然没有令我达到“郁结成疾”的地步,但也促使我更加关注生命的起源。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以假睡的形式,一动不动地躺着,眯着眼睛,偷窥父母做爱,偷听他们发出的声音。我那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每个夜晚都要那样,但是人的本能告诉我,他们一定是在为我的下一个弟弟或妹妹而忙碌。
“今晚吃炖萝卜干!”
这是他们的暗语。起初我是因对“炖萝卜干”而感兴趣,而记住的这句话。那时,萝卜干可是好东西,平时家里是很难吃到的。当父亲对母亲说“今晚吃炖萝卜干”时,我还以为他们要背着我们吃好吃的呢。我等了一晚上,都困得打哈流泪了,也不见纳着鞋底的母亲去炖萝卜干。我实在等不及了,便问:“什么时候吃呀?”
“吃什么?”母亲被我问蒙了。
“萝卜干呀!我爸不是说今晚吃炖萝卜干吗?”
母亲缺少营养而显现菜色与疲惫的脸上微微泛起一丝红晕。她飞眼挑了一下坐在八仙桌旁边的父亲。
“吃了五谷想六谷!滚蛋,赶紧睡觉去。”父亲虽然口中骂着,但是我见他并无愠色,好像还有一丝笑容。
我不敢反抗他,他的威慑力在我的神经上刻有印痕,以致他去世多年后,我想起他时,对他的眼神、怒骂、拳脚留给我的记忆,都会产生一阵阵莫名的不可自控地颤抖。
“你才吃了五谷想六谷呢。我也没说想吃萝卜干,这是你说的。”我小声嘟囔着。
父亲竟然笑了,笑着在我的后脑勺轻轻地拍了一下。不疼。我认定那是一种父爱。
我上炕睡觉了。佯装睡着,他们见我不再动弹,也上炕了,像打架似的,互相搂着、掐弄着、笑着,在一个被窝里。
这个阶段的母亲,似乎还是充满快乐的。而触及我灵魂的、为我留下了刻骨铭心印象的,是停留在祖母、母亲以及那个时期的女人们,她们日常无意讲述的那些只言片语的故事碎屑,那便是母亲一次次悲怆的分娩。
在中国北方,我的家乡——南梨村,人们把女人生孩子叫“躺下”和“摸炕”。上了岁数的老人们至今习惯这么说。
“你妈的胆儿肥哟……”小脚祖母聊天的时候,习惯端坐在炕头上,叼着细长的烟袋锅美美地吸足了,长长的指甲搔挠着窝头一样弯曲畸形的小脚。而后,她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讲述母亲摸炕的趣闻故事。她那尖细冷漠的语调中,不时夹杂一丝嫉妒和对逝去的光阴无法挽回的悲凉。
“你大哥落草的时候,已经是你娘生的第三胎了。那年,正好赶上毛主席进京开国。你哥上边俩水葱似的丫头,可惜命浅,啧啧。”
那年,我母亲又一次“摸炕”了。
我感觉我那粗心的父亲,根本不配做父亲,他从来没有把老婆生孩子当作一回事儿。那天,他一大早起来,拎着粪筐从街上铲回一筐细沙土铺在了土炕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大步流星地赶到生产队里领活,出工下田了。
谁也没有料到,有着丰富生育经验的母亲,生过多个孩子的母亲,那一次她却真的难产了。从早上太阳露头,一直折腾到了近晌午时候,我的那个不知是弟弟还是妹妹的婴儿,也只露出了一个血糊糊的脑袋,怕是早已断气了。我看到他(她)闭着眼睛,头发贴在头皮上,全是血。
“男的还是女的?”我睁大了眼睛问。
小脚祖母叹着气,说:“最好跟你一样,带把的才好。”
那个节骨眼上,虚弱无力的母亲仰躺在粗糙的沙土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她两眼冒着惊悚的光,一声声痛苦地号叫着,汗水如泼雨似的往下滚落。
“就是大人身子亏,上医院吧。”一向老成有道、胸有成竹的接生婆神色慌张,她哆嗦着举起两只血淋淋的手,额头的汗珠噼里啪啦地乱滚。我见过她探囊取物般地为母亲接生,然而这一次她紧张得不行,明显乱了方寸。母亲的叫声一声紧着一声,最终已经无计可施的接生婆子眼圈红红地催促着祖母说:“婶子,婶子,上医院吧,上医院吧……我真怕……”
小脚祖母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她知道家里穷得连耗子都不愿意来了,哪有钱去医院呢?
从挖心揪肺的阵痛中,缓过神来的母亲,嘴唇被她咬破了,流着鲜红的血。她却倔强地用力摇着头,执意不肯去医院。(一直到她生最后一胎,也从没有去过一次医院生产。)
“上医院吧,我是一点招也没有了。”接生婆甩着手,跺着脚,用颤抖的语声哀求着祖母和母亲。
接生婆最后彻底绝望了。她看着小脚祖母竟然黑着脸,一扭一扭悄没声儿地先走了。
母亲泪嘤嘤地对接生婆说:“孩子不行了,日子总还得过,去医院不是白花冤枉钱吗?”
“可你的命要紧呐!”
“我、我心里头有数,还能再挺挺……”
“会出人命的呀!”
“又不是头胎了,没啥。”母亲惨白的脸上漾出了带泪的苦涩的笑意说,“该井里死的,河里死不了的,死不了的……”
“哎呀!你那个大大咧咧的老爷们儿啊……”
无奈之下,黔驴技穷的接生婆怕担上人命官司,砸了日后的饭碗,她都没有来得及洗手,只是甩了甩,便丢下孤零零的、“心里有数的”、时刻都有可能丧命的母亲,抹着泪水、汗水,慌慌张张地走了。
接生婆一走,躲避在院门外面的小脚祖母也慌了神,她又折进屋看血泊中的母亲,然后恐惧地踮着那双弯曲如窝头一样的小脚,到庄稼地里去喊正在掐高粱穗的儿子——结实——我的父亲。
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像母亲正在流淌的血。
小脚祖母一声声凄厉的炸喊声:“可塌天了,结实,结实——,你老婆这回生不出来了。结实,结实啊……”
正在干活的社员们,从茂密火红的高粱地里纷纷探出头来,他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有人听清了祖母是在喊叫我父亲。于是,大家也帮忙喊:“结实,结实……”
父亲从一片高粱穗下面,挺出了头。他嘿嘿地笑着,一点也不以为然,他朝喊叫他的社员们大大咧咧地说:“哼!没屌事的,又他娘的不是头胎,老娘们儿只要开过了骨缝子,就好像老母猪下崽,哧溜,哧溜的。”他的一通话,惹得大伙儿一阵子哄笑。他看见社员们都在笑,他也就跟着笑,又对我的祖母打发了一声:“你回吧。”
这就是父亲,天塌下来都不在意的父亲。在他的眼里,他老婆的命,还没有一个工值钱。
在生死关头,苦命的孤独无助的母亲,擦干了泪水,我搀扶着她胳膊,她慢慢地用双肘支撑起笨重的绞痛不止的身躯,双手吃力地抠住冰冷、灰黑斑驳的墙壁,我赶忙将羸弱的肩头,顶在她的体侧,她才颤抖着、倔强地站起身来。我记不清母亲在老土炕上来回折腾了有多久,一下一下地跳蹦,但是她根本跳不起来,只是足跟一掀一掀地,血水从她的双腿间汩汩涌出,顺着大腿小腿向下流淌着……母亲的一丝不挂胴体散发着鲜血的腥臭味,我既害怕,又恶心,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她,我只要稍稍撤一下肩膀,她都有可能瞬间倒下或者死去。
那一次,我那苦命、坚毅和倔强的母亲,不自觉地创造出了她生育史上的一个悲怆的奇迹。那是一幅任何画家都无法描绘出的感天动地的图画。
生产的阵痛还未消失,刚从死亡线上归来的母亲,默默地望着已被父亲气冲冲卷裹进破草席中的死婴和胎盘,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再一次夺眶而出,我不停地为她擦拭,可无论怎样加快速度,都无法将她的泪水抹净,急得我也跟着哭了起来,于是,我便和母亲一起去感受那骨肉生离死别的巨大悲痛。
如果说我的兄弟和黑狗共葬我只是听闻没有目染,而这一次,我是目睹了父亲把那一坨血糊糊的肉,扔摔进铺开在屋地面上的草席里,就好像它完全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更不是他的孩子。那一幕,令我终生难忘,无数次走进我的梦里。我也是从那时开始,赋予了自己极强的代入感,总怀疑陪葬黑狗的是我,被扔摔进破草席里的也是我。
母亲的心是极其柔软的。村里有人去世了,她都要去街道边穆然肃立以目相送,默默地陪人家流泪,眼睛都哭成了桃儿。那时,我总觉得她一定是触景生情地想起了一个个先后离她而去的孩子。有时,她会在殡葬队伍的后面,一步一挪地跟着走出很远,有时她会悼送到村口,直到出殡的人群消失在田野的尽头。
我觉得这已超出了为乡邻的追悼范畴,她是为生命的苦短无常而痛哭流泪。
破草席被父亲野蛮地卷裹着拎出了屋门。到了院里之后,他便解放了双手,直接改用一只大方铁锹端着了,然后,出了院门。黄土版筑夯起的院墙低矮且破败,我和母亲依旧可以看到他的肩膀、脖子和头在墙头上移动。
当父亲头颅从矮墙头外面消失的瞬间,母亲终于彻底地放声大哭起来。她再也看不到从她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了。父亲只坑葬了他们骨肉的形体,殊不知那团没有了生命的血肉,却把真正的痛,遗留在人世间,遗留在母亲心里。我想,或许只有母亲自己才能体会得到这种骨肉剥离的痛吧!
母亲的心又是无比善良的。她对春天田野里长出的绿油油的幼苗,都像热爱生命一样,倍加爱护和珍惜。每当她看到田地边被踩歪的庄稼幼苗,她都会蹲下身,细心地培上土。
生产队大田里间苗的时候,母亲舍不得拔掉绿油油的秧苗,把秧苗留得密匝匝的。
队长在田间督工监察,大声喊叫:“大嫂,你这苗儿留得太密了,秋后等着收柴呀?”
母亲轻柔地说:“看着翠生生的苗儿,怎么也下不了手呀。”
队长没有好脸色地赞叹:“你的好心眼啊,南梨村街上真得要数头一份儿。”
“毁青苗是要损寿的。”母亲也黑着脸,小声地嘟囔。
“莫毁青苗”这句话是母亲一生认定的格言。无论种田还是生育,在她的生命中,一语双关。
母亲的故事被我讲得毫无章法,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明朗的主线,只有一个不停生孩子的主人公——我的母亲,一个生了十七个孩子的母亲。她把生育认作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在这条路上,她来来回回地走了十七遭,零散的只言片语,并非被我搓碎和打乱的,而是她在讲述给我之前,就已经被她和着岁月的艰辛与风霜,反复揉揣得没有了最初的完整模样,十七次的生育情节,仿佛是她生命之中一幅幅并不连贯的图景。但是,我发誓,我并没有对她的生育史做任何的虚构,只是记录、拼接与缝补;只是在回忆中,看图说话。
任何的夸张,都是对我母亲不可饶恕的侮辱。这个只有我母亲才能创造出来的悲怆的壮举,让我的灵魂感动和震撼,直到永远。
吃草根、啃树皮的大饥荒年代里,每人每月的口粮,只有十二两五。在这要命的当口,我母亲却又一次“摸炕”了。当我看出她微微隆起的肚皮时,我都替她发愁。我心里简直难受得不行,无法言表。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以后一个孩子也不要。
母亲这一次“摸炕”,是她生命中的又一个劫难。她用心血营养和孕育出的小生命,在我的意料之中,再次夭折了。三天时间里,母亲没有吃上一点东西,一家人全都饿得奄奄一息,没有人去关照月子中的母亲。饥饿得已经发晕的母亲,在那天夜里,拖着极度浮肿虚弱的身躯去了村西大食堂,刚到门口,就昏死过去了。好心的炊事员赵三爷偷偷塞给了母亲一个鸡蛋和一瓢白面,她才起死回生。这是她在十七次坐月子里最惨痛的一回。多年后,母亲对那次坐月子还记忆犹新,念念不忘赵三爷的救命之恩。
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更为难熬的是寒风呼啸的漫长冬夜。家里缺少棉被。上小学前,父母只要不是晚上偷偷地“炖萝卜干”,母亲通常都会和弟弟、妹妹还有我,四个人滚在同一边土炕上,同盖一床破旧的棉被。每晚,母亲只得露出她半个丰腴的臂膀侧身而眠。三更时分,她时常会被冻醒。但她每次都是悄无声息地为我们掩好被角,用她暖暖的软软的胸膛和厚实的脊背依偎着她幼小的儿女们。
在冬天每一个清冷的早晨,我们几个孩子最怕穿棉衣。因为,棉衣冻得像冰块一样。这时,母亲准会喜滋滋地坐起来,把我们几个孩子的小棉袄,一件件地围在她白花花、热乎乎的身子上,焐热后,再给我们依次地穿上。母亲用她的体温,为我们驱走了一个又一个的寒冷的冬季。
母亲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她的乳房在三十余年的孕育生涯中,再也没有流淌出一滴香甜的奶水。我们兄妹五人,全都是靠吃盐水调的面糨糊长大的。
村里很有生育经验的老人们说,我母亲这种情况属于“馋”奶,只要能吃上几顿荤腥儿,香甜的白白的奶水,就会自然流出来。然而,母亲在漫长的生育期中,几乎没吃过一顿肥肉,甚至她从来没有踏踏实实地坐过一个完整的月子。在十七次月子生涯中,她一边照料躺在襁褓中的婴儿,一边忙活着她永远也放不下的针线活。有一次,产后第三天,母亲就开始下炕,担水、拾柴、推碾子。
苦难对她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岁月的沧桑和一次次生育的磨难,没有给母亲留下任何产后后遗症和妇女病。相反,恶劣的环境和粗茶淡饭却使母亲愈加丰满和健壮了。
母亲的每一次分娩,都是一次壮丽的日出。
“猫还有九命呢?何况是人哩?”她说。
对待生育,母亲是那么执着和顺其自然。
生我小弟时,一向不主张母亲多生多育的姥姥匆匆赶来了,她对她这个不听话的女儿又气又恼又怜惜。面对炕上地下一群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外孙子们,她无奈地摇摇头,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母亲千万不能再生养了。
“三丫儿啊,你记住妈说的话了吗?”姥姥急不得恼不得,父亲在房檐下坐着,她又深说不得。
母亲点点头,专注地依偎着嗷嗷待哺的婴儿,脸上漾满了喜悦、疼爱。
“您取个名吧,猫还有九命呢?他要来,就让他来呗!您看他长得多俊啊!”母亲无比满足。姥姥叹了口气,她知道自己刚刚那一通苦口婆心的劝导,她的女儿早就当成了耳旁风。
“叫啥名呢?”姥姥略微沉吟了一下,没好气地说,“名大压人不好养呢。依我看就叫他萝卜干吧,皮实,好养!”
母亲扑哧一下笑了。她笑的同时,还不忘用眼睛的余光瞄看了我一下。
“不好听。”母亲直言否定了。
“那就叫老咸菜。”姥姥像是有大学问,张嘴就来。
母亲轻轻呼唤着“老咸菜,老咸菜”,乐呵呵地点点头。
老咸菜,从此就成了我老弟的乳名。
外婆发自内心的真情忠告,也没对她这个不长记性的女儿起到什么作用。直到五十二岁,母亲才生完了她的最后一胎。那是一个丫头,出了满月不久就夭折了,她的后背上有一个先天的烂洞,红红的,不晓得是啥病。那年,我的大嫂也过门儿快两年了。我的小侄儿是在我母亲坐月子的同时降生的。婆媳里屋一个外屋一个,两人同时坐月子,羞得母亲连大气也不敢喘。
出了满月的第一周,母亲发现她这老闺女背上的烂洞越来越大,几欲烂得透亮了,感觉这个末生的女儿定然是活不成了,便抹着眼泪儿对父亲说:咱这丫头来尘世一遭,都没有吃上一口奶水,怪愧对她的,你去大儿媳那里要一小茶碗的奶水给她尝尝吧,也算我们尽了养育的责任。那一次,父亲听了母亲的话,拾了家中一只布满纹痕的粗瓷茶碗,去我大嫂住的里间屋里求奶水。大嫂是个明事理之人,她二话没说,一手揽着尚且软骨沓沓的大侄子,一手撩起家织布衫的衣襟……
那时,出在我家婆媳一起坐月子、老公公向儿媳“求奶”的这件事,成了南梨村庄当年的一大趣闻。村里的乡亲们在谈论这一则趣闻的同时,总是嫌笑料不够足兴,还要把我和庄墩子打架互骂的情节加上,只有加上了,才会感觉我家的生育关系足够混乱。而我那一句“你×我妈,我×你姥姥”,在乡间流传多年,上上下下好几辈人,无不耳熟能详。
母亲,大名:崔秀芸;乳名:三丫儿。一九三〇年生,属马。一生分娩十七胎,育有四儿一女。义女六人,义子六名。
母亲目不识丁,身无财产和隐私,一辈子一生只信守两个字:本分。
母亲的人生格言:“莫毁青苗”。
母亲高寿,八十八岁无疾而终。那天清晨,她起床后,用桃木篦子将头发篦过三遍,在脑后绾成圆髻。之后,走出房门,开始扫院子。每天早起扫院子是她坚持了大半生的习惯,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坏天气,谁也阻拦不了她。
我把早餐做好之后,喊她吃饭,她过了八十岁以后有些轻度耳背,我大声地重复了两次:红糖鸡蛋、水揪疙瘩。我看她才朝屋门这边走了,我便回身进屋为她端饭、拿碗筷。
可是大约过了两三分钟,也不见她走进屋。我再次走出屋门喊她的时候,发现母亲已经歪坐在门口的青石阶上,站不起身了。
我知道母亲的大限将至,没有喊人,也没有急于请大夫,而是蹲下身,半跪着将母亲抱起来。母亲年轻时,又高又胖,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年月,她也比村子里其他妇女高大壮实很多。而暮年的她已经被岁月抽巴得只剩一身的皮包骨,不足七十斤了。谁能想得到谁又能相信,母亲这干瘪的身躯里,曾孕育过十七个孩子呢!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个婴孩儿一般轻飘,就像当年她曾经抱着我一样。
“儿子,妈要走了……”母亲微声喘语,“这辈子,妈没有照顾好你,把你拴在窗户上,你才哑了嗓子……下辈子,妈一定好好照养你……”
“下辈子,我可不想做您的儿子了,我不想让您再生我、再养我。”我把嘴唇贴在母亲肥肥阔阔的耳郭边,轻轻地一字一顿地对她说,“妈,儿子,下辈子,想让您好好歇一歇……”
母亲安详地笑了,走了。
崔秀芸,中国北方一名普通得像野草一样的女人。
作者简介
方言,作家、编剧,原名孙海潮,汉族。京西孙家铺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高研班作家。曾在新华社任编辑工作。现已出版长篇小说《一辈子也别丢下我》《爱之幻梦》等六部。其他作品散见《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南方文学》《延河》《都市》《安徽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作家天地》《光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作家网等报刊和网络。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