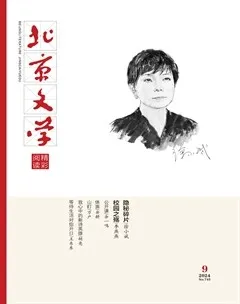上海小夜曲
小说以一个连锁便利店店员的视角,写三个孤独客之间游离朦胧的情感,那份从疏离中炼造出来的温情为支离破碎的生活增添亮色,带给在喧嚣里流浪的人们以慰藉。
1
便利店在九江路上。站门口,一抬头就能看见东方明珠。那么近,在眼前似的。便利店附近,都是低矮的老建筑,两相对比,十分触目。走过这儿的人,看见,都会忍不住掏出手机,拍一张照片。我也拍过,发朋友圈,配一句话说,这很赛博朋克。不过看多了,也就习惯了,不再觉得惊人。
我看看表,六点差几分,再过十分钟左右,红红就会来。买关东煮,有时候也买咖啡,买烟。三十五一包的万宝路,黑色包装,并不是女士烟。她抽起来,有一股豪迈气。店里禁烟,她拆开,叼一支在嘴上,出去抽。等再进来,我冲她喊欢迎光临,她往往会吓一跳。她一定是在抽烟的时候陷入沉思,我的喊声吵醒她了。她是那种常蹙着眉头的长相,平常看上去,也像是在沉思。似乎她的人生充满疑虑,容不得她放松。眉头下,两条细眼睛,直飞入长发里去。长发烫得微卷,向下,夹着小巧的鼻子和下巴,十分惹人疼。搁古代,这样的女孩子,该是谁家的大小姐,养在深闺,大门不出。或是谁家的姨太太,金屋藏娇,无聊时逗一句鹦鹉,摸几把骨牌。哪会像现在这样,跳舞喝酒一夜,到天明,才得空吃一口东西,垫垫肚子。
跳舞喝酒一夜,是我猜的。就像红红这个名字,也是我赋予的。而这些,都来自她常穿的一双红色舞鞋。有些旧了,鞋头塌陷,没了形状。但颜色仍十分醒目。附近没有工厂学校,像她这样长年做夜生活的,工作是什么,并不难猜。
又搁这儿等你梦中情人呢?钟姐常和我搭班,半年多,彼此熟透,知道我关注红红。见我站门口,便过来跟我调笑。我不好意思,嘴上辩解说才没有,我是在看东方明珠。钟姐抬头看一眼,说这么暗能看见个啥。又说,这天,不知道是阴是晴,别刚晴没几天,又阴了。时间还早,看不出阴晴,但应该不是晴天。晴天的话,这个时间,天应该更亮。钟姐是东北人,来上海多年,还是不习惯上海天气,常抱怨阴冷。也难怪她抱怨,最近上海天气是怪,元旦过后,就没几个晴天。我也抬头看一眼,东方明珠半掩在灰色的雾里,看不清楚。钟姐回去柜台里,站定后问我,这不是雾霾吧?我摇头,说不知道呀。我也走到柜台里,站她旁边。夜班七点钟结束,刚好错开早饭时间,但难保有些人赶时间,起得早。六点半左右,我和钟姐就会站到柜台里,做好接待准备。
你今天准备跟人说话吗?钟姐问我。圣诞没敢跟人说话,元旦没敢跟人说话,我看你啥时候跟人表白?我元旦跟她说话了。说啥了?我说新年快乐。钟姐扑哧一声笑出来,你还跟我说新年快乐了呢。她来之前,我至少跟二十多个人说了新年快乐,本以为练习充分,能够像欢迎光临一样脱口而出。但看着她,莫名地嘴上就黏了胶水,四个字,说半天,才艰难说完。我都怀疑她没听见,要不然怎么也会看我一眼。一直以来,她都没怎么看过我,大概是以为不值得她注意吧。要不然我那么放肆地盯着她看,早就被发现了。不过,她也许习惯了被注视。
那你说完新年快乐,没顺便表个白呀?钟姐继续拿我开涮。我顺着她的语气,用东北话说,表啥白呀,咱跟人差十万八千里远呢,挨得上吗?哟,哟,钟姐说,可别跟我说你不喜欢她,要不是还留着这俩眼珠子有用,估计都得飞出来,贴她身上了吧?她说得有趣,我笑起来,没回她。
欢迎光临——门上的铃铛一响,有没有人进来,我和钟姐都会条件反射地这么喊一声。而进来的人,不提防,往往会被这吓得愣一下,定住似的,一两秒后才又活动。我觉得好笑,忍不住,嘴角翘起来。钟姐看见,拉我一下。客人进门喊欢迎光临,离开时喊欢迎再次光临,取食物时戴手套,结账时推销商品,保持微笑,这都是店里规定。哪项做不好,被发现后,都会扣钱。钟姐刚做这一行时,被扣过不少钱,心有余悸,执行得格外认真。不过钟姐胆子小,杯弓蛇影,常自己吓自己。我跟她说,这大早上的,他们才没空看监控。她说我不懂。她比我大四五岁,自有她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我争不过她,也懒得争。
钟姐胆小,是被她前夫吓出来的。她前夫是她高中同学,十七岁在一起,十九岁高中毕业,就结了婚。两个人,几乎算青梅竹马,互相陪伴长大。结完婚,两个人一起去海南打工,在陌生地方,建设新家。钟姐说,都是因为海南的太阳太大,环境气候,跟东北反过来,她丈夫,那么知根知底的一个人,竟彻底变得陌生。以前烟酒不沾,慢慢学会抽烟喝酒不说,又学会赌博,打老婆。常常跟一帮狐朋狗友出去,大半夜酒醉回来,闹得鸡犬不宁。钟姐说,晚上都不敢睡,怕他半夜打她,来不及跑。就算睡着,一点动静,也会突然醒来。至今如此。钟姐怀孕,请假在家休息,她丈夫听人挑拨,非说她偷男人,肚子里怀的是野种,把她锁家里,钉死窗户。她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也只是调解。警察走后,她丈夫有了新借口,又把她打一顿。
钟姐说,那时候也是傻,没想过跑走,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命该如此。我劝她,不是傻,是年纪太小,不成熟,一旦走入死胡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钟姐说,年纪小是一,主要还是读书少,没大眼光。她又说,早知道上学时候好好读书就好了。我上学时候也没好好读书,职高出来就到处打工,她这么说,我也不好说什么。过段时候后又说起来,她说你不一样。都是没读好书,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不一样。钟姐说,至少你不会发疯。
孩子早产,七个月掉下来,保温箱住几天,还是没养活。钟姐提心吊胆,加上产后抑郁,没多久就疯了。她丈夫把她遗弃在海南,多亏邻居热心,打电话给她父母,几千里地飞去,把她接回老家治疗,才没死。不过钟姐应该感谢发疯,要不然,不知道还要在她丈夫手下受多久。钟姐说,理儿是这个理儿,不过那种躺床上脑子过电的滋味,这辈子都不想再试第二次。正常人,谁也不想试脑子过电的滋味,那感觉,想想都头皮发麻,后槽牙疼。钟姐算幸运的,没留下后遗症。到现在,也算走出阴影了。我们开玩笑,说她脑子没好透,还该再电一电。她也不生气,笑着说我们才“欠电”。只是有时候,还会祥林嫂似的,到处跟人说这段“光辉历史”。
欢迎光临——我没听见铃响,听钟姐喊,才跟着喊一句。声音此起彼伏,显得很热闹。进来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脱掉帽子,跟我们说早上好。我们又都跟他说早上好。
2
红红没来。红红经常来,但也不是每天来。我没多想,下班去地铁站路上,只低着头,认真走路。钟姐过来,突然用肩膀撞我一下,问我,难过啦?没见着梦中情人,回家要睡不着了。什么梦中情人,小心让人听见。钟姐哟一声,说,还害羞了。我继续朝前走,钟姐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一天天的,抢着上夜班,还不就是为了能多看人家两眼。我辩解,才不是。她说,那为什么?你可别说是为了陪我。我看她一眼,说,那可不一定。
便利店夜班十小时,要接收两批货,整理上架,做早点,做保洁,其实不轻松。我不像钟姐,有心理阴影,害怕人多,才选择天天上夜班。我抢着上夜班的理由,钟姐说对一半,另一半,是因为我妈。
我跟我妈住一起。租来的房子,住二十几年,也成了家。我妈出钱,用我的名字买了新房子,在嘉定。她嫌远,不愿意搬过去住,我也不愿意。两个人就挤在50平不到的空间里。小门小户,有种说不出的温馨。但随着我长大,空间明显变得拥挤起来。两个人,矛盾不断升级,总拌嘴。一段时间过后,有意识地,我们都选择走出去,彼此分开,寻找新的空间。我妈重新找了稳定工作,朝九晚六,在养老院当后勤总管,坐办公室。我妈选了白天不在家,我便选夜里。剩晚上几个小时在一起,吃饭看电视,聊一天见闻,母子关系恢复,比以前还亲密。
以前,我是说很久以前,我跟我妈,关系其实比一般母子还要好,因为我们曾相依为命。我没有爸爸,十九岁,我妈怀孕,就独自来上海,生下我。赖一帮姐妹帮忙,才挣扎着活下去。我有十一个干妈,过年领压岁钱,领十一份。
我没有干爸,可从没缺过叔叔,数量多少,已记不清。他们出现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时间短的,一个月不到,我还没认清脸就消失了。时间长的,至今还有联系。我过生日,仍能收到短信。我怪过我妈,觉得就因为这么多人来来去去,给我童年带来太多动荡不安,才让我如今很没有安全感。我妈嘴上强硬,跟我说她也是没办法。没有那些人,她一个单身女人,如何能在这大上海活下来。但还是照顾我情绪,没再让那些叔叔们上门。后来,我想通了,不再有怨气。家里才又有叔叔出现。
一觉睡醒,我爬起来,去卫生间。看见马桶上坐着南叔,正戴着耳机刷手机视频。我手扶在门上,打一个哈欠,问他好了吗?他拿下耳机,问我说什么。我又问一遍,他好了,胡乱抽几张纸擦过,就提起裤子。我按冲水前,瞅一眼马桶,里面就只有几张纸。
南叔洗手,一边问我还睡不睡。我又打一个哈欠,问他几点了。南叔说三点多。时间还早,我跟他说再睡一会儿吧。南叔说,午饭在锅里,你睡醒自己热一下吃。
南叔是最近搬来跟我们一起住的。听我妈说,他正在跟他老婆闹离婚,没地方去,只好先在我们家委屈几天。他委不委屈我不知道,但家里地方小,多一口人,饭桌前坐着,都显得挤。我才是真的委屈。南叔搬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他年近退休,不用天天上班,在家有空,收拾之外,专门研究吃的,每天不是鱼就是虾,养得我跟我妈都胖了。而且南叔安静,穿拖鞋在屋里走,没声。又整洁,上完厕所,会拿纸把马桶圈擦一遍。这份闲情雅致,可不是以前哪个叔叔能比的。
要我说,我妈配不上南叔,用网上的话说,两个人,差着阶级呢。我妈自然知道,可南叔不知道。恋爱让他盲目。他以为是他老娘的死,才促成今日局面,冥冥中自有指引。
南叔跟我妈,是在养老院认识的。南叔老娘,住养老院七八年,他每周去一趟,待半天。我妈不是伺候他老娘的护工,要不然他才看不上。我妈是主任,主管养老院的所有护工,类似监工。上班就是喝茶,等着问题找上门,解决问题。但我妈生性好动,坐不住,养老院里到处走,找人说话。南叔说,他把老娘送进养老院,没多久就跟我妈认识了,后来再去,我妈每次都能叫出他名字,记得他说过的家族故事。这是我妈的本事,这么多年混社会的经验,特别能认人。南叔这么说的时候,我妈不解释,我也懒得多话,只盯着南叔看。同时心里想,认识几年,早不在一起,晚不在一起,偏在南叔闹离婚分财产时才在一起,用脚趾头想,我也知道我妈图什么。不过也是巧,南叔闹离婚,偏赶上他老娘去世,从养老院到殡仪馆,再到墓地,我妈帮不少忙。南叔感激,五十多岁的人,重燃爱情,对我妈动了真心。我妈趁机抓住,笼络他,住到我们家来。几件事,看似分得清,其实纠缠在一起,织成一张网,将南叔网入其中。
我吃了南叔的饭,嘴软,常犹豫要不要多说几句,将他唤醒。但想到另一方,是我妈,说多,反而显得目的不纯。跟钟姐讨论,钟姐说,这种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也没用。不无道理。
南叔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的,我回去床上,没睡多久,就被他电话吵醒。他跟我道半天歉后,才不好意思地说,想让我帮个忙,搬点儿东西。他给我一个地址,我坐地铁过去,是一个老小区。南叔在小区门口等我,见到,跟我说明。这是他岳父母家。两个老人不知道他和他们女儿闹离婚的事,遇到事情,还是和往常一样,打电话找他。他拖几天,看年关将近,拖不下去,才来解决。
边朝小区里走,我边问什么事。他说是前段时间,楼上往下扔东西,一个罐头瓶子,落在他岳父母家后院玻璃顶上,玻璃砸碎一大块。虽没伤着人,但他岳父母担心,想起来让他给后院换一个砖瓦的顶棚。
我向四周看,很快就明白过来。这种老小区,一楼的住户,都把向外的窗户挖开,做成后院,扩大自家面积。后院位置,正挡着楼上窗户,玻璃顶棚虽然采光好,但也确实容易碎,不安全。
南叔说,本来找好了工人,按他们要求订好的砖瓦水泥,但临近过年,工人突然回老家去了。砖瓦水泥送到,小区不让放外面,只能先搬进后院,等工人过完年来施工。
我没意见,跟着南叔走到他岳父母家,果然,在楼门口,看到一小堆建筑物品。南叔敲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来开门,南叔介绍我是他朋友的儿子,过来帮忙。老太双手合十,上下摇着跟我道谢,嘴里不停地说辛苦辛苦。
其实也没什么辛苦,南叔从物业借来平板车,两个人把东西抬上车子,拉到后院,再抬下来,没多久也就搬完了。老太客气,说已经打电话让老头子去超市买新鲜鲈鱼,要留我们吃饭。南叔拒绝,说还有事要忙呢。只让老太找一条毛巾,递给我,让我擦擦身上的灰。我留心南叔岳父母家,看书架上堆满书,书架过去,又贴墙放着钢琴,防尘布盖着,十分整洁。去卫生间,看水池边、地上也都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难免心里波动,想南叔跟他们,才是真正一家人。
3
还是平时时间,六点过几分,红红出现了。不过不是一个人,陪她一起的,还有一个男人。个子很高,比我高一个头,大概一米八几,快一米九,站柜台前,遮得我眼前光线都暗下去。买关东煮,两个人一边挑,一边说笑话。时不时把脸凑到一起去,十分亲近。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们,认真地拿东西,算钱,扫码结账,说欢迎再次光临。
红红来,钟姐每次都故意走开,让我去招呼。这次也一样。等红红他们离开柜台,背对着我们坐在用餐区,钟姐才过来。她用肩膀撞我一下,说没事哈。我苦笑一下,说当然没事。但刚说完,就意识到心底一阵疼痛。被揪住一般,越拧越紧。
我用手捂住胸口,使劲向下按按,才好些。钟姐焦虑地问我咋了,我把手向下滑到肚子上,来回晃着,跟她说,突然肚子疼。不等她再问什么,我就跟她说,我去趟厕所。
钟姐说得对,我喜欢红红。钟姐每次开我玩笑,我都辩解,其实是不敢承认。我怕承认后就得去面对,得大着胆子跟红红说话,告诉她我喜欢她。但我跟她差太远了,她那么漂亮,那么不凡,跟她告白,除了自取其辱,不可能还有别的结果。
从马桶上站起来,我下意识地提裤子,才发现裤子根本没脱。便利店有规定,上厕所不能超过五分钟,精神恍惚之下,我也不知道在厕所蹲了多久。这时候,来不及自嘲,赶紧开门出去。镜子里看一眼,我注意到眼睛都被我揉红了。打开水龙头,接一捧冷水泼在脸上,用袖子胡乱擦一把。
红红跟那个男人竟然还坐在用餐区。我问钟姐,我去了多久。钟姐说,没多久。我哦一声,继续回到柜台里,招呼后面的顾客。我的眼睛,一直留意着红红他们。好几次,我看到红红的头,朝那个男人肩膀上靠去,很快,又抬起来。有一次,那个男人甚至伸手揉了揉红红的头发。烫得微卷的头发,看着就十分柔软,男人的手那么粗壮,把她的头发都揉疼了吧。
一直到下班,钟姐都没再来招惹我。换班,收拾东西,走到门外,钟姐才问我没事吧。我没事,能有什么事。钟姐说,这种事也正常。是啊,我说。到地铁站,分开,钟姐又问我,真没事吧?我看着她,咧嘴笑笑,跟她说,还好啦。说完转过身,赶紧走了。到家,躺床上,我以为会睡不着。但实在太困,没多久就睡着了。梦也没做一个。
接下来,红红再来,一般都是和那个男人一起。买好东西,在用餐区坐半天,慢慢吃完才走。开始时,钟姐照顾我情绪,没多说什么。两三次后,就忍不住跟我评论起来。她说那个男人油头粉面,一看就是那种嘴巴很甜、很会哄女人开心的小白脸,靠不住的。真正过日子,还得是我这样的男人。我顺着她的眼神看过去,那个男人,确实头发上抹了油,脸上也涂了粉,说他油头粉面,不算冤枉。不过男人长得眉开眼阔,高鼻厚唇,一脸正派。我回钟姐说,他挺好看的,跟红红很般配。钟姐说,各花入各眼,我看你跟红红也很般配。我再看红红,她穿衣打扮还和原来差不多,不过心情好了,眉头舒展,整个人精神很多。我跟钟姐说,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自己几斤几两,心里还是有数的。钟姐骂我一句,又说,到底是谁吃不着葡萄。
吃不着葡萄不要紧,只要红红还一直来,我能看见她,就和以前没太大区别。虽然看着她跟那个男的有说有笑,心里难免失落,但到底没得到过,没体会过曾经拥有的快乐,失落也有限。不是不能承受。
再过几天,我就又能有说有笑地跟钟姐开起玩笑来。我们通过仔细观察,猜那个男的是红红同事,要不然也没法同时来便利店吃东西。钟姐还猜那个男的肯定是刚上LnZrmMKMHAb4xVFDJWVSuA==班没多久,看见红红好看,就巴上她,和她谈恋爱。钟姐说,等着瞧吧,往后那个男的遇见更好的,肯定就会甩了你的红红。我嫌钟姐嘴毒,没一句好话。钟姐哼一声,说,这种男人我见多了。我笑她,离过一次婚,就搞得跟在青楼上过十年班一样。钟姐伸手打我,我朝旁边躲,碰掉台子上一个铁盆。铁盆落地上,声音响,惹得红红他们都扭过头来看。冷静下来,我故意问钟姐,到底见过多少男人?钟姐板起脸,朝着红红的方向,做出张嘴要喊的姿势。我赶紧求饶。钟姐才笑了,说,还反了你了。
老在一起说红红他们,我和钟姐关系更亲近起来。晚上上班前,她约我提前出来,一起吃东西。以前我都拒绝,这段时间,也答应一两回。吃完逛街,钟姐看中一双高跟鞋,红色的,拿起来要试。我想起来红红脚上的红舞鞋,觉得以钟姐的气质,穿上肯定不合适。没想钟姐穿上,也挺好看。钟姐说,就跟你说了吧,别瞧不起人。钟姐把鞋子还给店员。我问她为什么不买,钟姐说,太贵了。我看看价格,是不便宜。我工作几年,存不少钱,看钟姐犹豫的样子,一时冲动,想跟她说我买给你。但话到嘴边又拦住,终于还是没说。
这件事后,我连着两天,都做梦梦见钟姐。一次是梦见她躺在医院病床上,脑子上戴一个金属帽子,连着电线。我坐在旁边看着她。还一次是梦见她跟我牵着手在路上走,她叫我老公。梦里,她那一声老公叫得十分亲切自然,好像我们已是结婚多年的夫妻。
睡醒起来,蹲马桶上,我想得久,忘了时间。南叔喊我,我才清醒过来。南叔做了萝卜丝饼,泡了咖啡,让我当下午茶,先吃点垫垫。六点多我妈回来,再开晚饭。我倒一杯咖啡,慢慢喝着。
南叔也倒一杯咖啡,在桌前坐下来。
我问他,下午喝咖啡,不怕晚上睡不着吗?南叔说,没事,咖啡喝习惯了,已经没太大影响。好巧不巧,这句话正撞在我心口上。我跟南叔说,人也一样吧。南叔用疑问的语气嗯一声,等我继续解释。我就解释说,人跟人在一起习惯了,也就没太大影响了。南叔点头。
4
红红又一个人来了。买一包万宝路,拆开,到门外去抽。门斜对着柜台。我站在柜台里,探着头向外看她。钟姐突然出现,也看着门外,问我,咋回事?我收回身子,说不知道。
红红抽完烟,回来,又和以前一样蹙着眉头。我小心地看着她,想问一句都还好吗。还没问出口,就被红红的电话铃声打断。红红拿起来看一眼,嘴里发出一个声音,似乎是骂了一句。她把电话直接按掉了,没接。我看她脸上神色严厉,没敢再跟她说话。
红红走后,钟姐用手扇扇鼻子,说,醉成这样,这得喝多少酒呀。红红醉了吗?我完全没看出来。钟姐说,你没看她走路都晃?晃吗?我还真没注意。
这之后,一连几天,我都没再见着红红。钟姐幸灾乐祸,跟我说,看我说啥来着,肯定是分了。我嘴上说那也不一定,心里则暗暗得意。想钟姐说得真对,油头粉面的男人,果然靠不住。不过我也担心红红,不知道她会不会太伤心,走不出来。
七点钟,我跟钟姐准时下班,背着包朝地铁站走。出门,钟姐突然站住,捏着口罩打一个喷嚏。她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太累,还是天冷受寒,鼻炎又犯了,一直打喷嚏流鼻涕。我跟她说,实在不行,就别上夜班了。钟姐重新戴好口罩,说,再上几天吧,快过年了,我准备回老家一段时间。她问我,你呢?我知道她的意思,是问我过年还上不上班。不上班也没事可做,上班反而能拿三倍工资。再说我也没老家,可以让我回去几天。我跟钟姐说,到时候看吧。钟姐嗯一声。
地铁站在两个红绿灯外,转个弯才能到。转弯时,我们都看见对面花坛里躺着的人。旁边行人过往,都盯着看,但没人走上前去。钟姐说,不知道是啥人,醉成这样。她这话让我没来由地惊一下,走过去后,又扭回头看。
我看见了那双红舞鞋。
真的是红红,脸朝下趴在花坛里。我跟钟姐把她翻过来,摸摸鼻子,还有温热的气息喷出来。应该只是醉了。但这么冷的天,她身上只有一条长裙,露两条光胳膊在外面,冻得没有一点儿血色。脸上也雪白雪白的,只有嘴唇,不知是涂的唇彩还是冻的,颜色乌紫。我脱下羽绒服,包在她身上。问钟姐,现在怎么办?钟姐问我知不知道她住哪里。我怎么可能知道。钟姐说,那报警?似乎也不行,警察来,少不了把我们也叫去问话,而我们,也没什么能说的。我想一下,跟钟姐说,要不叫一个车去你那,等她睡一觉醒了再说。钟姐一个人住,没什么不方便。果然,她点头说行。
正拦车呢,红红醒了。她看我一眼,挣扎着要下来。我放开抱她的手,让她站到地上。我问她感觉怎么样,还好吗?她没理我。只裹了裹身上的羽绒服。
钟姐拦到车了,打开车门,让红红上去。我们还没上,红红就从里面关上车门,不知道跟司机说了什么,让司机把车开走了。留下我跟钟姐站路上,面面相觑。
我身上没了羽绒服,觉得冷,抱着两手发抖。钟姐看见,拉着我走了。还好地铁上有空调,下地铁,我快跑几步,很快到家,没怎么冻着。钟姐给我发消息,问现在啥情况?我困得不行,跟她说,现在睡觉。
睡醒起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上完厕所,回去重新躺下。看手机,有南叔的消息,让我睡醒给他电话。我打过去,南叔说还是顶棚的事,他等不及工人,干脆自己动手搭了。我惊讶他斯斯文文一个人,竟还有这本事。他说,以前搭过兔子窝,差不多。顶棚搭到最后,得爬上去把瓦摆整齐,他怕脚下不稳,不敢爬上去,问我能不能去一趟。
我过去,看见顶棚果然快搭好了。南叔站在楼后面的梯子上,正拿着铲子,弯着腰把墙上的水泥抹匀。南叔放下铲子,跟我说,伸手能够得到的地方,他把瓦都摆好了,只剩下够不到的地方了。我等南叔下来,爬上梯子看,瓦是青色小瓦,搭积木一样,一个扣一个,按规律排队。我踩着墙上去,跨一大步,到另一边的墙上,站稳身形。南叔重新爬上梯子,站在梯子上,把瓦递给我,同时指挥我操作。排瓦不难,而且南叔也排得差不多了,没剩下多少。我且排且退着步,很快弄完。
下来,南叔让我先走,剩下他收个尾就行。我看时间还早,回去也没其他事,就帮他一起做完。零零散散,竟弄到天黑。南叔又借来平板车,让我帮他一起,把拆下来的玻璃顶和剩下的建筑材料都装上去,运到垃圾房。南叔要去旁边楼还借来的其他工具,让我去物业还平板车和梯子。他跟我说了物业地址,但我地方不熟,绕一圈才找到。
回去,看楼后面没有南叔,我就绕到前面,到房子里去找。想跟他说一声再走。房子门开着,我还没进去,就听见南叔声音,他在卫生间里,用上海话冲谁喊着——阿拉也算兢兢业业,一个电话,屁大点事体,半夜三更,穿着拖鞋跑过来。伊呢?阿拉老娘住老人院,七八年,伊看过一眼么?伊没得去过呀!现在阿拉老娘人都没了,阿拉勿得再想跟伊搞七捻三!
我站一会儿,听里面一时没有声音再传出来,犹豫是不是先敲个门。但又想,这种时候,我进去,似乎也不合适。就退出去,朝外走了。
上地铁,我给南叔发一个消息,说我先走了。过许久,南叔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就走了。我跟他说朋友过生日,约好去唱歌的,前面忘了。
挂上电话,我把手机拿在手里,点开微信。有钟姐的消息,问我醒了没有。我回一个表情给她。钟姐很快回过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吃晚饭?我不是很想跟她一起吃晚饭,但回消息,回了一个表示同意的表情。
钟姐想吃火锅,我就跟她去吃火锅。吃完到处转着,磨磨蹭蹭,一直到上班时间。我妈来电话,问我去哪儿了,我把跟南叔说的借口又跟她说一遍。钟姐听见,问我咋不说实话,我说我妈嘴碎,懒得跟她解释。钟姐笑着说,是怕你妈知道,以为你在谈恋爱吗?我也笑一下,没多说什么。
火锅辣,吃完,我肚子就不太舒服,等进去便利店,打完卡,觉得更难受了。跟钟姐招呼一声,朝厕所跑去。看着时间,蹲满五分钟才回去。
红红,红红——刚一进门,钟姐就冲我喊。红红怎么了?钟姐越着急,话越说不清楚,弯腰拎起一个纸袋子,指着跟我说,红红,羽绒服,你快去追!我听懂了,立即翻身冲向门外。
门外,马路上,我却站住了。不知该朝哪里追,向西,不远处就是熙攘的十字路口,人来人往。向东,是灯光闪烁的东方明珠,一抬眼就看得见。那么近,仿佛就在眼前。
作者简介
于则于,原名于业礼,中医学博士,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写作小说、诗歌等,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清明》《芙蓉》《青年作家》《香港文学》等文学期刊。有小说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海外文摘》等转载。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