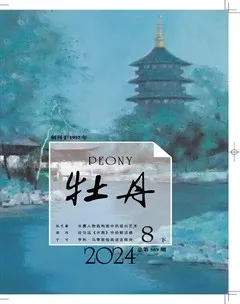花木兰故事的跨文化再生产研究
本文以我国南北朝时期传唱的乐府民歌《木兰辞》为切入点,从文化再生产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对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1998年)与真人版《花木兰》(2020年)两部影片的叙事方式、意象符号运用、人物形象重造、故事内核重塑等方面进行全面剖析,进而探讨新时代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更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
花木兰的故事最早源于南北朝叙事民歌《木兰辞》。全文寥寥三百余字,却受到各个时期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乐府民歌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愈发频繁,一个个鲜活的东方形象通过电视、电影等现代电子媒介活跃于国际舞台。在这样的世界浪潮下,花木兰的故事从民间故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并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断地在当代意象中被重创和再现。迪士尼重新诠释了花木兰的故事,将传统中国故事改编成美式电影,以“他者”视角塑造了木兰形象。
一、从巾帼英雄到迪士尼公主:迪士尼《花木兰》系列电影登场
1998年,动画版《花木兰》上映,这是迪士尼首次尝试将中国故事作为主题的电影。这部前后花费五年时间制作、耗资超过1亿美元的动画,让从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花木兰闪亮登上国际舞台,化身为迪士尼公主系列阵容里的第8名成员。花木兰的出现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她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形象不同于迪士尼以贝儿公主、爱洛公主为代表的第一代“白皮红唇,金发碧眼”公主形象,更在于其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平凡姑娘爱上王子”的迪士尼经典叙事逻辑,转而以一种带有社会意义的“民间故事形态”呈现。与此同时,动画版《花木兰》讨巧地将美式幽默文化注入古老的中国故事,以蟋蟀、木须龙等大胆梦幻的符号想象对木兰的故事重新解读,成功将传统的中国故事改编成美式经典。
2020年,迪士尼二次集结强大阵容,将《木兰辞》改编为由刘亦菲、甄子丹、巩俐等大咖领衔主演的真人版剧情电影,重新演绎了在情与理、正与邪中的新型木兰故事。真人版可以说是对动画版的一次升级,但影片上映后,评分和口碑却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尤其是国内外的评价分化现象格外引人注目:在北美等地区上映后,《花木兰》真人版的烂番茄新鲜度为79%,国内豆瓣的评分却一路走低,从5.9持续下降到4.8,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争论之声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此版作品不够正宗这一观点上。
那么,观众的争论究竟是因真人版影片中的木兰形象与以往《木兰辞》中的木兰形象大相径庭而起,还是因其与迪士尼动画版中以西方“他者”视角塑造出的木兰“公主”形象不符而起?观众口中所谓“原版”的花木兰,是否已在无形中变了样?从巾帼英雄到迪士尼公主,花木兰身份转变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对迪士尼电影《花木兰》进行解读。
二、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对《木兰辞》中意象符号的移植和重构
从故事的设定背景上看,花木兰这一人物虽没有被记录在正史中,但《木兰辞》的发生背景是可考的。据考究,木兰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这个王朝由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定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之北一带)。诗中“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几句也明确指出了木兰在行军过程中经过的主要地点:黄河、黑山、燕山。而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却把木兰塞进南方的福建客家土楼,土楼旁是大片的水稻田地。尚且不论水稻田的出现是否合情合理,客家土楼作为客家人从北部迁往东南沿海后建造的防御性建筑,在地理位置上只出现在中国南方。而在时间追溯上,土楼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因此,最早的土楼历史总共也就700年,这与木兰故事发生的时间至少相隔了1 000年。
而影片中时空错乱的画面、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远不止于此。在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手撑华伞的宫女在花园中身着洛可可风长裙风姿摇曳;俗语“四两拨千斤”被直译成“Four Ounces can move one thousand pounds”(4盎司可移动1 000磅);媒婆身后的对联中的上联“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出自元代杂剧《西厢记》,而《木兰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传唱的一首乐府民歌。另外,在动画版电影《花木兰》中,花家祖宗在石碑上显灵时的样貌与格兰特·伍德所作的世界名画《美国哥特式》中的模特形象如出一辙;伪士兵谎报军情时,以大熊猫作为行军坐骑;作为中国文化代表性元素的大威猛的龙,被改造成蜥蜴一般大小。
与此同时,在对中国特色文化习俗的诠释上,二者默契地忽略,诸如当户织布、赴市鞍马、点兵册封、对镜梳妆、庆贺归来、杀猪宰羊等大量灵动丰富的生活场景,迪士尼动画版与真人版两部影片均未体现,转而选择堆砌熊猫、大红灯笼、笔墨纸砚、围棋等中国元素,而主镜头则被放置于战场之上。这倒也符合迪士尼,或者说好莱坞的美式拍摄风格。毕竟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有足够阔大的空间杂糅进功夫、武侠、情爱、英雄主义等元素。
三、迪士尼电影《花木兰》故事内核的嬗变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花木兰》只是在表面上遵循了原作的故事结构、语境和文本叙事顺序,其内部的“肌理”实际上进行了符号化的重建和移植:从最表层的故事叙述、意象符号,到人物形象塑造,再到故事主题内核,都被强烈地涂上了跨文化的异域色彩。
原诗中,木兰从勤劳善良、淳厚质朴、心思细腻的平民少女逐步转变为坚毅勇敢、受人赞颂却不慕高官厚禄的巾帼英雄,内心由弱到强的成长历程由此显现;策勋归来后,木兰又再次回到出征前作为勤劳织女与孝顺女儿的状态,其美好品质依然保留。然而在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既没有神秘背景,也没有异人天赋的木兰,从小就显示出与常人不同的、强大的“气”(Chi)。因为“气”的存在,木兰在身份暴露被驱逐后得以独当一面;在完成自我觉醒、认清使命后重新回到战场,凭一己之力引发雪崩,击退柔然;而同样具备强大“气”的女巫,竟能利用“气”随意地变换身形,人鹰不分且多寡互成。
在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的演绎下,一方面“气”的妖魔化呈现使木兰的英雄之路更加富有戏剧性,另一方面木兰成长与转变的过程显得粗糙且生硬:木兰的迎战,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带着“我会为家族荣誉而战”(I will bring honor to all us)的坚定信念走向战场,斗志昂扬。参战的积极性消解了木兰从军的无奈与复杂性。事实上,木兰从军的抉择过程是艰难的,但这一点电影并没有展现出来。电影中木兰积极参战的行为一方面以西方文化的勇士精神作支撑,另一方面简单化了木兰从军的心理状态,从军的悲壮性无从体现。此外,木兰的觉醒不是通过不断斗争磨砺出来的,而是通过女巫与凤凰来强行点拨,这大大淡化了原作中木兰的勇气。最后的关键节点,木兰单刀赴会,营救皇帝,凭一己之力成为拯救全军队的“超级英雄”。
迪士尼改编后的《花木兰》更像是木兰找寻真我、实现自身价值的一次蜕变机遇,而作为原故事主题内核的“忠孝”二字,却变为点缀。中国元素、西方精神和女性主义三种价值观念的杂糅,导致影片最后成为一部看上去很“中国”,内核很“西方”,主题很“现代”的电影。
四、对花木兰故事跨文化改编的思考
《花木兰》导演妮基·卡罗曾在采访中谈道:“这当然是关于中国文化和那里的一个非常古老和重要的故事……但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种文化,那就是迪士尼文化。”由此可以看出迪士尼制作方改编的角度非常讨巧。不管是1998年诙谐幽默的动画版(通过赋予童话式的梦想来激发观众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天真与童趣,从而将大人小孩“一网打尽”),还是2020年演员阵容豪华的真人版(以花木兰作为核心主角,在男性阳刚气质与女性阴柔气质的结合中展现出其独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榜样形象),都是既保留了中国元素,又体现出西方文化,从而成功地将中西文化融合并展现。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花木兰入选“迪士尼公主”时,她就不再是那个当户织布的少女木兰了,而变为追求自我意识觉醒、天生自带光环的耀眼主角。她所承载的也不再是“忠孝仁义”的中华传统美德,而是“善良纯真”“坚强勇敢”“勇于追梦”等公主标签。虽然迪士尼团队在拍摄与制片方面技艺娴熟,从叙事层面到运作机制都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体系,但木兰真正难能可贵的美好品质被剥离了出来;与此同时,武打场景、魔幻元素的大量出现大大满足了国际影迷的感官需求,却让木兰故事丢失了最原初的质朴和感动。
《木兰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有着鲜明浓郁的民歌特色和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在对木兰这一形象进行再塑造与呈现时,不应只是对其故事和人物进行粗糙的、商业的挪用,而应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深层精神内涵。诚如伽达默尔所言,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之间的关系,对于真正艺术文本或艺术作品含义的探索永远不会结束,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新的误解不断被消除,从而使真正的意义从所有遮蔽它的事件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还有新的理解源源不断地出现,揭示出意想不到的意义要素。在赏析经典文学作品时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这是对木兰形象的如实挖掘,也是对经典的尊重,但在现代语境下,对木兰形象进行再创作时,我们要意识到木兰也需要成长,要与时代接轨,要有思想与认识上的进步。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基于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带来的启示,以平等互通、包容万象的态度,从迪士尼的做法中获取灵感,将本国文化的个性融入世界文化的共性中,并以通俗晓畅而又富有特色的阐释,塑造出符合当下时代精神的新型木兰形象。笔者相信,在未来更多像花木兰故事一样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定能以更为多元鲜活的样态在经典与流行中找到平衡,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也定能在新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国际舞台上,更为自信而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