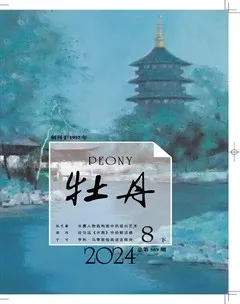历史视角下的骨法用笔与没骨画的关系研究
骨法用笔和没骨画是中国画体系里两种至关重要的绘画技法。本文从历史视角出发,对骨法用笔和没骨画的定义、起源与发展及艺术特色进行分析,揭示两种技法的精髓及其相互关系。
一、骨法用笔的发展历史及特点
(一)骨法用笔的定义
骨法用笔源于谢赫六法之一,其核心在于通过独特的用笔技巧,以“骨”喻形,传达物象的形体结构、气质精神与韵律动感。此处的“骨”并非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指一种内在支撑力量和精神气韵。骨法的核心在于用笔要肯定有力,这一特征与书法用笔的要求相通。骨法用笔不仅追求笔力的强度,还涉及利用笔墨线条来表现人物俊朗神气的技巧。
(二)骨法用笔的起源与发展
骨法用笔出自古代南齐谢赫的画论《古画品录》六法之一,“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骨法用笔的提出与前代绘画理论有承袭关系,与之最密切的便是顾恺之的画论,其在《论画》中曾八次用到“骨”之一字,如“有天骨”“有骨法”等,谢赫则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法论。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本意是强调以人的内在精神来品评人物,将人的才性、气质、性格、能力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外在形象观察人的本真,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也逐渐融入绘画。
唐代是中国绘画的黄金时代,阎立本、吴道子等将骨法用笔推向新的高峰,他们以遒劲有力、顿挫转折的线条表现人物的形象气质。骨法一词最初源于相学,用于描述人物的体态形象和气质,在汉魏时期广为流行,这里的骨法用笔即由线条构成画面的主干,使绘画对象具有“形似”特点却又不完全等同,由线条的质量给人以力量感,从而具有“骨气”。在绘画艺术中,线条是表现对象美感的关键要素,作品的结构、形态和神韵均需要适当的笔力来呈现。画家应当运笔果断,意在刻画出传神生动的作品。
到了宋代,文人画的兴起标志着骨法用笔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绘画不再局限于对物象的描摹,而是具备了彰显创作者身份地位和文人气质的新功能。正如吴昌硕所言,其绘画成就的关键在于运用书法之法于绘画创作。这也凸显了书法用笔在绘画中的重要性,骨法用笔的意义也得到了拓展。
(三)骨法用笔的艺术特色
骨法用笔作为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历经千年不断传承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技法理论,成为画家创作和评判的重要标准。骨法用笔强调“以线立骨”,即通过线条的勾勒、皴擦来塑造物象的形体结构和质感。画家通过线条的粗细、浓淡曲直、虚实等变化,加以腕力、臂力的调动,使线条具有力度和弹性,追求笔力劲健、力透纸背的效果,从而表现出物象的形体、质感空间以及内在的精神气质。骨法用笔还注重墨色的变化和传达物象的精神内涵。在绘画实践中,无论是中锋的浑厚凝重,还是侧锋的灵动飘逸,都应体现“骨立”的精神,即线条要具有内在的张力和节奏感,再赋以墨色的浓淡干湿,丰富线条表现力,传达出“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因此,骨法用笔并非单纯的技法追求,更是一种审美追求,也是实现“形神兼备”的重要方式。
二、没骨画的发展历史及特点
(一)没骨画的定义
没骨画是中国画技法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没骨画不同于工笔和写意,没骨画法之没,意指隐去线条,其精髓在于笔墨与设色的浑然一体,以色代线,以墨写形,强调形神兼备。它既不像工笔线条稳定、精细和流畅,又不同于写意画中大刀阔斧、挥洒自如的笔墨风格。
(二)没骨画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没骨画起源的探讨主要围绕“彩陶说”与“凹凸法”展开。新石器时代,彩陶等器物上的纹饰以色彩填涂为主,用色自由奔放,可视为没骨画的原始形态。“凹凸法”以色彩晕染为主,不受线条束缚,开创了没骨画的先河。南宋楼观记载,张僧繇将“凹凸法”融入山水画创作,并称之为“抹骨法”。宋代是没骨画发展的黄金高峰时期,徐崇嗣、赵昌等人将没骨技法运用到花鸟画创作中,取得了极高成就。这一时期。没骨画逐渐摆脱了“凹凸法”的影响,形成了独立的绘画体系。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兴起,没骨画的题材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明代徐渭、陈淳等人的写意花鸟画,以及清代恽寿平、扬州八怪等人的作品,将没骨画的写意精神和笔墨趣味发挥到了极致。其中,恽寿平的没骨画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没骨画的艺术特色
“直接以色图之”是没骨画的主要特点,通过色彩的变化塑造形体、表现质感。墨色亦是色彩,在没骨画中与其他颜色一样是塑造物象的媒介。画家通过色彩的层层晕染、渲染,使画面呈现出浑然天成的效果。没骨画虽然省略了明显的墨线勾勒,但并不等于放弃笔法。相反,画家通过细腻的色彩表现,将笔法隐含于色彩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没骨画要求画家具有极高的色彩控制能力和对材料的敏锐度,以确保色彩的运用既精准又充满动感。没骨画看似简单,实则对画家的造型能力、理解能力等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它追求一种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意象美。没骨画强调的不在于对客观物象的精确复制,而在于对物象精神气质的传达。
三、骨法用笔与没骨画的关系探讨
(一)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骨法用笔和没骨画作为中国画中两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并非割裂对立的存在,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有显著差异,实则在艺术创作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画丰富的表现体系。骨法用笔强调线条的勾勒和结构的塑造,这为没骨画提供了坚实的造型基础。没骨画虽凭颜色隐没线条,但这种画法对物象形体、结构的把握,依然离不开骨法用笔的支撑。骨法用笔的线条勾勒体现了中国画对线条美学的追求,骨法用笔下的作品常给人刚劲有力、结构严谨的感觉。没骨画则以柔和的色彩运用和流畅的笔触展现出一种自然灵动之美。骨法用笔以线条为主,色彩为辅,没骨画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界限,将色彩与线条融为一体,画家在创作中可以灵活运用这两种技法。例如,董其昌在《昼锦堂图》中,先用浓重的赭石勾勒山石轮廓,之后运用花青皴擦表现山石结构,最后施以石青石绿等色进行点染,以此替代传统的墨色勾勒,展现山石的形态,突显其“骨”。在树木的刻画上,他通过精准的线条表现出树木的造型和枝干的穿插细节,使画面更加真实,从而创造出既有力又灵动的画面。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骨法用笔和没骨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唐代时,骨法用笔逐渐成熟,并在山水画和人物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宋代花鸟画兴起,没骨画技法逐渐成熟,并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完善。两种技法在历史发展中互相借鉴,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
(二)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骨法用笔与没骨画法虽在表现形式与技法上存在差异,但在艺术追求与审美意趣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骨法用笔追求线条的力度与韵律,通过线条来传达物象的精神气质,强调“以形写神”“意在笔先”。没骨画亦是如此,通过色彩的变化晕染传达物象的内在神韵。骨法用笔与没骨画法皆以追求画面气韵生动为共同的审美意趣。骨法用笔通过笔墨的虚实相间、抑扬顿挫来营造画面生动的气韵,而没骨画常通过逸笔草草的手法、色彩的丰富多变营造出气韵生动的效果。这种审美理念上的融通,为骨法用笔与没骨画的互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唐代,画家们在传统骨法用笔的基础上,探索通过更自由、更富有变化的笔墨来表现物象。例如,唐代画家杨昇在描绘山水时,在骨法用笔的基础上,运用没骨画的技法增强山水的气韵,使画面更加生动。宋代花鸟画家赵昌不仅擅长骨法用笔,还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没骨画技法,使作品既有线条的刚劲又有色彩的柔美。尽管骨法用笔与没骨画法技法各异,但在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趣上却殊途同归,皆是为了表现物象精神和气韵。这种技法和理念上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画技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三)创新探索,骨没新境
在当代国画创作中,骨法用笔与没骨画的界限逐渐模糊,二者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作趋势,为传统技法注入了新的活力。没骨画并不是“没有骨”,反而应该“强化其骨”,其精髓也是“骨”和“肉”的关系,是运笔和设色的交融互补。例如,画家霍春阳在其花鸟画作品中,常常以细腻的骨法勾勒花卉轮廓,再辅以没骨法的自由渲染,创造出既有结构感又富有韵味的画面效果。其他画家也尝试将没骨法巧妙融入传统骨法用笔中,创造出更加轻柔、清秀、雅致、飘逸的画面效果。这种融合打破了单纯工笔和写意画法的局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语言。例如,在花鸟画创作中,部分画家不再拘泥于工笔画“双勾填彩”的程式,而是借鉴没骨法,以色彩的层层渲染来塑造形体,或以略带写意的笔触直接点染,追求“色墨交融”的艺术效果,使画面更具清音灵动之感。周午生先生的禽鸟画创作便是这种融合的典型案例,他传承了工笔画中对禽鸟形态结构的精准把握,但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他摒弃了工笔画中以细笔勾勒丝毛的传统技法,转而采用阔笔披毛,以色彩的浓淡变化来表现羽毛的质感和蓬松感,并借鉴了林良、吕纪等人的写意笔法,以墨色点染,一气呵成,使画面更具生气和动感。在设色方面,周午生先生并未完全遵循“三矾九染”的繁复程式,而是在总结传统设色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概括,以更加直接、明快的用色方法,使画面色彩更加亮丽,同时注重保持石色的半透明性,以体现“色不挨墨”的传统审美趣味。这种将骨法用笔与没骨画法相结合的创作理念,既是对传统技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代审美趋势的积极回应,反映了他们对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
四、结语
骨法用笔和没骨画在技法上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既在艺术创作中提供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又在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画的多样化发展。骨法用笔与没骨画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却又并非简单的对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对于形式与内容、技法与意境之间平衡的追求。骨法用笔以其精细的线条和表现力,为中国画的创作提供了坚实基础,没骨画则通过色彩或墨迹的直接表现,丰富了画面的视觉效果和艺术表达。这两种技法虽然在具体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在艺术理念和表现上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追求通过笔墨表现物象的神韵和意境,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高度艺术追求。
本文不仅详细介绍了骨法用笔与没骨画的技法精髓,还阐释了它们在现代国画创作中的巨大潜力。现代画家可以在传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创新性地融合骨法用笔和没骨画,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