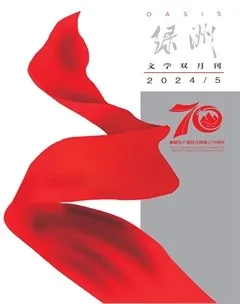珍藏七十年
2023年岁末,顾晨叶结束了这一年最后一场讲解。这一天,也是她与这家全景式展示新中国屯垦戍边历史的博物馆相识的第16个年头。
那一年,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的顾晨叶被一则招聘广告吸引,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所学专业,顺利通过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原石河子军垦博物馆)的招聘考试,成为这家博物馆最年轻的讲解员。
在博物馆,一把铜质军号深深吸引了她,穿越厚重的历史,她仿佛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北的号音,听到这把军号引领二军五师十五团1800多名官兵,徒步15天,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胜利解放和田。听到类似的军号,每天清晨准时在新疆的亘古荒原上嘹亮响起,召唤她的爷爷们,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唤醒那片沉睡万年的荒原。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主动请缨进军新疆的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有诗云: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这样的画面,早已定格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七十年前的人和事很有可能已经固化到一些简单而抽象的标志中,比如一幅黑白照片,比如一座雕塑,又比如一个和那段往事曾密切相关的地名。但七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似乎还有很强的穿透力,它顽强地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仍在激励我们。
静卧在密封展柜中的一件件旧式武器,每一件背后或许都有一个悲壮的故事。“铸剑为犁”后来常常被人引用,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10万大军“扑向荒原,作战地图变成生产地图,炮兵的瞄准仪变成水平仪,战马变成耕马”,这是诗人的语言。
1952年2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他用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口气告诉全体官兵:“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这是顾晨叶每一次讲解的重要环节,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自此将书写崭新的华章。
1950年初,陶峙岳的起义部队刚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不足两个月,王震便率领陶峙岳、张仲瀚、陶晋初等几员大将,马不停蹄赶往玛纳斯河西岸,有人对他说,那里有400万亩可耕荒地,有玛纳斯河、奎屯河和充足的泉水,宜农宜牧,二十二兵团的机关便定在了石河子。
8月,王震再次来到玛纳斯河西岸,对那个叫石河子的地方详尽踏勘。
当时的石河子只有29户人家,有1个镇长,1个警察局长,9间小铺子,1所小学,1名教员,40多名小学生,他们大多居住在一个叫老街的地方。王震当晚投宿在老街西口的一家车马店,出门数步便是水沟、苇湖,蚊虫肆虐。
天气异常闷热,陶峙岳和其他几个人久久无法入睡,清晨,忽听王震在屋顶上喊:“真是好地方。”众人上房顶,见王震一手叉腰,一手遥指四周沉睡的荒野,用诗一般的语言告知他的大将,就在这里,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世。
这是一座军人徒手建造的城市,这座城市后来成为兵团的象征和缩影,成为新中国屯垦第一城。著名诗人艾青曾在这座军人建造的城市生活16年,他感叹: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
这座年轻的军垦新城,有太多新中国屯垦戍边的记忆。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的馆址,最早是二十二兵团机关办公楼,史称“军垦第一楼”,它是石河子的第一个建设项目。石河子老街几户铁匠帮忙打制粗糙的劳动工具;官兵们自己动手搭围窑,土法烧制砖坯;圆木上钉上蚂蝗钉,拴上绳子,二三人一组,从几十公里外的山里拉运木料。1952年5月动工,同年9月竣工,一座高二层(中间主体四层)、建筑面积为5600余平方米的办公大楼矗立在万古荒原上。
它的造型类似苏联上世纪50年代山地拖拉机,位于石河子原来的中轴线子午路的南沿线上,1995年以前,它一直是这座城市的政治中心。
和拖拉机有关联的还有金茂芳。1952年8月,山东女兵金茂芳走进了“铸剑为犁”时代,这一年,金茂芳19岁。她拒绝了护士、医生、教师等工作,坚决要求到生产一线参加劳动。当年冬天,组织上安排她去学习拖拉机修理与驾驶技术。
她是兵团第一代女兵、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曾创下一天播种120亩地、7年完成20年劳动任务的纪录。1960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金茂芳便是1元纸币“女拖拉机手”的原型。她驾驶过的拖拉机便收藏于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990年秋天,时年20岁,英语专业毕业的张红彦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这幢著名的办公楼。当时,组织上为她提供了两个工作选择,图书馆或是博物馆,她思忖片刻,选定了石河子军垦博物馆。
当时,成立两年的博物馆筹建办便设在“军垦第一楼”。没有文物,向社会征集,工作人员深入当地十八个农牧团场,走家入户。1992年,他们来到兵团第八师一二二团的一户职工家里,年长的老军垦名叫王德明,他家的杂物棚子里,架子上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摞旧衣服,有大衣、衬衣、手套、袜子,这些衣物上布满了大大小小、花花绿绿、材质不一的补丁,其中便有那件后来成为镇馆之宝的“百衲衣”。
这是一件1950年配发的军大衣,上面有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补丁296块。许多人在“百衲衣”前驻足、感动、流泪。1995年,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首次展出时,“百衲衣”便引起轰动。一个第一次到博物馆参观的湖南籍女兵眼中含着泪花,声音发颤地说,那时候就这样。
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的第一个冬季,二军五师十五团的官兵徒步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时,遇到了罕见的沙尘暴,他们眼前只有漫无边际的黄沙,他们义无反顾地前行。这支部队的部分留守官兵后来成为兵团第三师四十七团的屯垦新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再也没有离开过和田。
几十年后,一位兵团司令员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用飞机将健在的原十五团官兵接到乌鲁木齐,安排在兵团最好的徕远宾馆,标准间,丰盛的晚宴,参观新疆首府,老兵们有些恍惚,这就是他们最初进疆时的那个迪化吗?从和田飞至乌鲁木齐,空中约需两个小时,而他们当初却走了15天。
司令员的眼睛有些湿润,他说,每年都要请他们来一次。他心里有些悲伤,因为他知道,来的人会越来越少,他们中的许多人将长眠于那片陌生而又熟悉的土地。
2020年8月12日,原二军五师十五团最后一位留守战士董银娃在第三师四十七团敬老院去世。他们,留下了不朽的“老兵精神”。
1950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一周年之际,起义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原新疆警务总司令陶峙岳成为二十二兵团首任司令员。一次,王震试探地问:“愿不愿意入党?”陶峙岳问答:“固所愿也,不敢请尔。”
不久,他向王震袒露:“虽不敢轻易启齿加入共产党,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1965年夏季,陶峙岳将他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兵团党委。因为一段特殊时期的开始,他的入党申请被长期搁置。
1982年2月,时隔十七年,陶峙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年9月28日,党中央批准他为中共党员。90岁新党员陶峙岳入党申请书上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于人类社会事业的实践。”
陶峙岳的党费证现珍藏于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一位国内艺术品鉴定专家曾说:“这本党费证我不能估价,也不敢估价,但我送它八个字:无尚珍品,绝无仅有。”
在这家博物馆,还有许多普通兵团人的故事。博物馆收藏了一面具有特殊意义的国旗,来自兵团十师一八五团一连。这个“西北边境第一连”所在地叶西盖在地图上没有标识,但它俨然祖国西北边境绵绵延续的长城上的一处垛口,忠贞而坚强地矗立着。
1979年春天,一连一个上海知青在离国境线不足200米的地方,在他耕种的玉米地里,首次升起一面自制的五星红旗,这个升旗人就是沈桂寿。
哈萨克斯坦边境小镇阿连谢夫卡就在沈桂寿的玉米地对面,对方哨兵的瞭望塔抬眼可见。此前,对方的士兵每天都在郑重其事地升国旗,沈桂寿想,我也要让五星红旗升起来。
沈桂寿步行一整天,来到35公里之外的团部。他要买一面国旗,和国境线那边的士兵一样,每天举行升旗仪式。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跑遍了团部附近的商店也没有买到。
回到家,老沈翻箱倒柜找出家中的红被面,和老伴一起连夜缝制了一面国旗,又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庄稼地边用石头垒起一个台基,竖起了桦木旗杆。
十五年如一日,每天日出而作时,沈桂寿就在地头举行升国旗仪式,直到他1994年退休。
如今,在一八五团一连,当年沈桂寿升国旗的地方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连职工每家每户的院落里都设置了国旗杆,每逢重大节日、活动,数十面国旗迎风招展,在“西北边境第一连”织出一道独特的风景。
不仅仅在一连、在一八五团,在兵团所有的边境团场,升国旗、唱国歌,这些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的仪式,在这些地方显得更加神圣、庄严。
刘守仁被定格在这家博物馆,与“中国美利奴(军垦型)”细毛羊有关。四十九年,17885个日夜,刘守仁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军垦细毛羊培育事业,用累累硕果印证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1955年,南京农学院畜牧系毕业生刘守仁,经过一个月的旅途,辗转来到了石河子,一辆拉木头的大卡车将他带进了坐落在天山深处的兵团紫泥泉种羊场,这一年他21岁。
1957年春天,紫泥泉第一代杂种羊在天山深处诞生了,但毛色不太纯正。
1965年4月,正值牧草返青的时候,几百只细毛小羔羊咩咩落地了。经过科研部门的鉴定,羊毛的细度、弯曲和光泽,都达到了高级毛纺原料的标准。1968年,刘守仁培育的“军垦细毛羊”在北京农业展览馆正式展出,引起了国内外巨大的轰动。从此,中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优良细毛羊种。
1982年金秋,一位世界著名的澳大利亚遗传育种学专家来到紫泥泉种羊场,他的目光突然被不远处涌动的白云一样的羊群吸引住了。那威武雄壮的公羊,脑袋两侧盘着螺旋形犄角,层层裙褶般的厚毛,看上去似曾相识,他觉得难以置信,在澳洲以外的地方还能见到这种高品质的细毛羊。当洋专家听翻译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培育成功的细毛羊时,蓝色的眼睛瞪得老大:“奇迹,奇迹,真是奇迹!”
刘守仁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重要贡献奖,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999年12月27日,时任新疆农垦科学院名誉院长的刘守仁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被有关媒体尊称为“中国细毛羊之父”。
七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七十年,一个人的人生可能已步入老年。但七十年,之于一个国家,之于一个组织,尚处壮年。
七十年来,兵团三代军垦战士在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在塔克拉玛干和古尔班通古物两大沙漠的周围和漫长的边境线上,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耕耘着,开拓着,在新中国屯垦戍边史上书写了崭新的一页,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
1999年8月,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鉴定专家组将那件“百衲衣”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同期鉴定确认这家博物馆共有国家一级革命文物29件,包括战士们当年手工打造的红砖,表面有“ZZ”字样,代表着二十二兵团,包括第六军赠给二十二兵团成立大会的锦旗,陶峙岳乘坐过的嘎斯六九吉普车,张仲瀚给罗承瑛、王炳臣的信等等。
陪伴着29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和数千件馆藏文物,张红彦已从青春少女成为博物馆的“老人”,两鬓略显斑白。而这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始终在更新、丰富,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兵团创业初期的艰辛,更可以触摸到兵团发展壮大的脉动。
这家博物馆浓缩了七十年兵团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通过这种浓缩的选择,你可以从中看到兵团成长的历程:有喜悦,有艰辛;有高峰,有低谷;有奋斗,更有开拓。星移斗转七十年,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兵团七十年灿烂的夜空中自然少不了璀璨的星群,兵团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
这家博物馆经过多次扩建、改陈,它的变化印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更是一部鲜活的兵团七十年发展史。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老旧人物照片,印证了这支屯垦队伍的壮大和变迁。在这家红色博物馆,无处不在叙事一种兵团精神,这种精神长期以来支撑着兵团的发展,而兵团的发展和壮大在最近的十几年尤为明显。
七十年来,这个“兵团”一直在变化。身在其中,或许不知其变,有时或许会埋怨它变得太慢。但回眸一看,它却紧紧跟着新中国和新时代发展的步伐,有时候慢半拍,但有时候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七十年依稀刹那间。今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昨天的“新闻”。旧的“新闻”记录着以往时代的足音,映照着过去的侧影,人们从中或许可以读出曾亲历过的世变风云,或许还会窥见一些不曾知晓的往事。
历史中的大部分人物已经从历史的前台隐去,再过若干年,知道他们的姓名、了解那段往事的人还会更少。虽然只有短短七十年,但这段历史很不平凡,令人难忘。新中国史无前例的屯垦史,完好无缺地保存在这座外观朴实、内涵丰富的博物馆内。
那是一段激情奔放的历史,那是一群充满血性的战士,那是一片如醒狮般活力四射的土地。它在中国西部。它在新疆。它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座已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博物馆,承载着并永续着那段难忘的红色记忆。
这座红色博物馆,让石河子声名远播。顾晨叶终生难忘的一场讲解定格在2022年7月13日下午4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在一层大厅会见兵团老中青三代代表。他强调,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
石河子,不仅仅是一座新兴的城市,更是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最成功的范例,在这个意义上,石河子已超越了它作为一个城市存在的理由。而与其共存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便是一部厚重而浓缩的兵团发展史,让新中国屯垦伟业的声光影像永传后世。
责任编辑蔡淼宁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