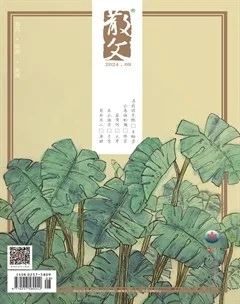环外”生活
从喧闹的市区搬到外环之外的郊区小镇,第一个感受是:早上起来听到窗外小区门卫的说话声, 已不是久已听惯的天津方言,而变成了带有唐山味的河北话。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所谓天津话,是指以天津老城为中心的一个尖朝南、底朝北的三角形方言岛内人们所说的方言, 使用范围其实很有限。据说天津方言起源于皖北,是由明成祖朱棣“燕王扫北”时从安徽迁移来的军人及其眷属所说的江淮方言演变而来的,而我所感觉的“唐山味”其实也不准确,应该说是“静海味”,因为我所住的小镇已临近静海, 而天津方言区就是为北京音和静海音、宝坻音等包围的一个方言岛。著名小品演员赵丽蓉所说的方言就类似宝坻方言,与我在这里听到的语音比较接近。
这个郊区小镇距市中心十二公里,有地铁可直达市内,空间距离并不远,但自然风貌、风俗人情与市内已颇为不同。此地古为宋辽对峙之地, 留下的一个古迹就是杨八郎庙,后称疙瘩爷庙。庙中有一棵据说树龄已有千年以上的古枣树, 后又由此树萌生出两棵新枣树。三棵枣树虽看去年事已高,仍然姿态纵横,风骨遒劲,生机勃勃。据说信者摸摸古枣树干上的疙瘩, 就可以把病痛从自己身上移除、吸走。由此,被尊为“疙瘩爷”的老枣树,就成了代为背负人们苦痛和罪愆的拯救者, 也使得庙中的香火得以延续至今——这大概也是古庙由原来的于史无证的杨八郎庙逐渐演化为疙瘩爷庙的原因,神祇之受崇拜与否,也取决于人神之间的互动程度。
搬到小镇生活的另一个突出变化,就是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夜色的浓黑和天宇的辽阔,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浓似墨汁的黑夜是我童年时所熟悉的, 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城市都以“不夜”为荣,所以黑夜就被彻夜长明的灯光肢解了, 城市的夜空被高高低低的灰黄、低垂、无精打采的灯光所割据,画地为疆,将真正的夜空挡在了外边。这种光的滥用, 已成了一种为人们所习焉不察的新的污染。碧海青天、浩瀚星空这些能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自然存在, 好像都已被人们忽略、遗忘。人们日益沉浸和沦陷于日常的操劳和感官的娱乐之中, 丧失了与更高的存在进行精神上的感通、交流的兴趣和能力。这种现代性给人提供了生存的便利, 但也给人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人越来越“宅”,蜷缩在自己造就的安乐窝里,完全遗忘了身外的世界。自然具有一种澡雪心神的功用:《霸王别姬》中有虞姬的这样一个唱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轻移步,走上前, 荒郊站定, 猛抬头, 见碧落, 月色清明——云敛晴空,冰轮乍涌,好一派清秋光景。”无边碧落中的一轮明月一下子将人从战乱纷争、大兵围困的现实迫压中抽离出来,得以从高处反观自己和身边的一切。宋朝茶陵郁禅师在摔了一跤之后突然悟道,写下:“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日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禅师写的是人心中的这轮“明月”,一个人的内心若是乌云密布,充满烦愁,自然也就难以领略空中的明月之美, 也就无法使自己的心灵在瞬间得到提升和解脱。
我出生在一个三线城市,小城不大,出门就是城墙、郊外。我们上小学时经常由学校组织到附近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对农村并不陌生, 而且我幼时在乡下的外祖父家住过几年,所以对田地、旷野、村落、炊烟有着特别的好感和依恋。住进城市之后,就和乡村隔绝了, 出门散步也只能在人多且狭窄的河边林荫道走走,感觉很不过瘾。这次搬到郊外,散步可以说是有了足够的空间:新修的宽敞的大道直通天际, 走在旁边的人行道上有一种天高地远、心旷神怡之感。道旁是姿态纵横的百年枣树, 再远处则是在风中起伏的麦田、杨柳掩映的小河。古人论诗,常说有一种萧疏简远、洒落清逸的风神、情致,实际上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神明归位、心与道合、人与天齐、无为而为的超然之境。今人往往以西方式的“自由精神”比附老庄的“与大道同化”的逍遥游,两者其实是迥异其趣的: 后者是要确立自己先于他者的自主性, 前者则是要将自己融入更高的存在,从而实现生命境界的提升,两者各有其独特意义,不可偏废。一百多年前严复从西方引入“自由”一词时,心中颇为惴惴——在译介斯密的《原富》时,严复就已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意识到:“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的确,对一切社会制度最大的威胁,往往就来自于“无信仰者的自由”,这是一种为所欲为、被贪欲驱使的野蛮自由, 显然对一切秩序都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有节制的自由,一种平衡群己之界的文明自由。要获得这种文明自由,能够“修己以安人”的功夫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一诗中所写的“野性的独流减河”以及“少女一般羞羞答答”的团泊洼,也都离我居住的小镇不远,独流减河在雨季的确水势很猛、水量很大,是“九河下梢”的天津引泄大清河和子牙河洪水直接入海的人工河道。团泊洼则位于静海城区东部,总面积六十多平方公里,现在是著名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它是北方难得见到的巨大的湿地, 远远望去, 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平时波浪不兴,确实有一种静美情致。著名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离现在的团泊大桥不远, 遗址现在已被列入天津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干校的正式名称,应为“中央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由八个协会和戏曲研究室、电影剧本创研室、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所等十二个文艺单位的七百余人组成,1970年9月由宝坻迁至静海团泊洼,当时有学员六百二十七名,均是曾享誉全国的著名艺术家,也是“文革”中被定为有政治或历史问题的需要劳动改造的人物。这些艺术家在这里生活了五年,条件比较艰苦,四人居住一屋,喝苦水,自给自足。周扬、华君武、秦兆阳、吕骥、吴祖光、郭小川、王朝闻等名人在静海期间,为活跃此地的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吴祖光、王杰等曾为静海县业余作者修改过剧本,宋扬、王古芬等为静海业余宣传队排练过音乐舞蹈,袁毅平、尚进等为静海摄影爱好者办过培训班,陈其明、卢开祥等为当地剧团排练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而著名诗人郭小川,则在这里冒着风险、悄悄写下了诗歌名篇《团泊洼的秋天》,使这个水域颇大但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北方湖泊进入了文学史。人世几回伤往事, 长河无语只东流。今天的独流减河、团泊洼边,干校明显的遗迹只剩下了两个砖砌的门垛、废弃已久的水塔, 以及水塔上残存的当年写下的标语,其他另有几排已近倾塌的平房,是当年干校学员们的宿舍。“文革”之后,由于审美个人主义思潮的勃兴, 以郭小川为代表的人民主体性诗学,一直受到专家的冷落,但读者是最后的裁判者,《团泊洼的秋天》至今传诵不衰,融入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显然彰显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古人说“大道低回”,历史,总是像河流一样在曲折中前行,而不是笔直地流向大海,对历史不能求全责备,要充分理解历史的曲折和艰难,同时又不放弃社会必定会进步的信心。
团泊洼附近还有一地颇值得一看,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曾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一村”大邱庄。它的起步甚至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6 年,短短几年间,这个偏僻乡村就成为闻名全国的“焊管之乡”,而其带头人大起大落的人生也具有一种极强的戏剧性与醒世作用。历史总是最好的老师。我居住的“环外”的这些地方,常常是引发人思古幽情的所在。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