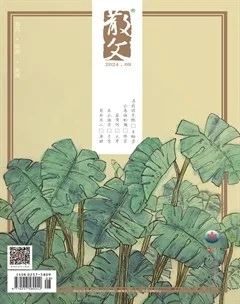废黄河
一
常来这条河,却叫不上名字,就像常见一个人,却叫不出姓名。此地人讲:“上老淮河边走走吧。”“走,咱们去废黄河钓鱼去! ”怎么姓淮又姓黄? 怎么就“老”了,就“废”了? 穿街而来,一街花花绿绿的电动车,一巷花花绿绿的夏装女。一足跨左,一足跨右,我奋力蹬踩,骑着最忠实的坐骑,吱呀呀不烧油不耗电。此生合是诗人未,黄昏骑驴看黄河。
数月没来,河已发育得丰满而风姿绰约,滚滚的河水激荡起浪花,夏季南风为它推波助澜;苇子长高了,长长的叶子撩风抚水,像披着湿发的新浴少妇;菖蒲绿油油,涨水岸边努力挺拔着肩腰,做个傲然出水的剑客; 空中斜飞的喜鹊尚幼,羽毛还是稚嫩的浅灰色,因而更加欣喜练习着飞行,在河面上搭一脚,箭至岸边合欢树枝头,把粉色花瓣弄落一地;爱凑热闹的小麻雀与水鸟打成一片,旋即又飞到柳树上叽叽喳喳地争吵个不休。
水泥小路沿河,容纳行人和自行车通过,我吱嘎吱嘎地踩,目光所及除了成双的情侣,也有一些如我般形单影只者。一位少年自一辆山地车上跳下,从容地从书包里拿出书,在那条斑驳的仿古石凳上坐了下来。先望了望河水,又拂了下身边的片片柳叶, 拈起一枚在手里捻着打转,终于进入书本的世界。他是个高三毕业生吗?高考就要临近了,来河边减减压?高考年年考,有没有这样一题:“我国的母亲河是? 全长多少公里? 发源于哪里? 流经哪些省份? ”不管孩子们如何回答,我查得的答案是:我国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
仔细地看了又看, 黄河并不流经江苏, 然而这里是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此地人称唤“老黄河”早都已经习惯了。
二
太阳想从云缝里挤出个笑脸,热情却被厚云阻滞,挣扎许久,从浓云另一头箭出。“云里的日头灰中火”,被迫改道的光柱射向大地,竟似伴有隐隐现现的老天的泪滴。我摸摸头发和额角,望望微风河面的微小涟圈,确实是稀稀的雨滴。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一千多年前李白吟咏黄河,他看到的黄河,是今天的黄河吗? 奔流到海,是今天的海吗?此黄河,彼黄河,此海,彼海。此黄河,是废黄河、古黄河、黄河故道,而彼黄河是改道后几百年历史里的新宠。“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此黄河仿佛是杜甫的《佳人》。我又想起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奔驰骏马啊四条腿,黄河大海啊都是水。李、杜、王,唐朝诗人当年可曾真的到过黄河的入海口,那入海口,是今天的入海口吗? 废黄河,怎么就被废了呢?
九曲十八弯,绵延五千多公里,母亲河从青藏高原而来,水流携带着混浊厚重的风土。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脾性。据统计,在1946 年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约一千五百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中六次重大的改道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在宋代,黄河曾改道经由江苏入海,其原因却并非黄河自身的桀骜不驯。南宋建炎元年(1127),刚刚灭辽的金人背弃了与宋的盟约举兵南下,不久就攻破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徽宗钦宗父子被金人虏走,宋代黄河沿岸的根基尽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宋代仅存的皇室势力为躲避金兵的追逐不得不举国南迁。
黄河、淮河、长江和大海,都应该记得靖康之难发生的第二年,即公元1128年,宋守将杜充在今天河南滑县的李固渡扒开河堤, 以期能够通过人为制造黄河决口,阻止金兵进一步南进。而一百多年后,当蒙古人南下灭金时,金国也如法炮制了当年宋阻止金兵南下的手段, 扒开黄河口。有样学样,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 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北郊十七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
山有山的命运,河有河的命运,城有城的命运,文有文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泰山并不最高,却荣为五岳之尊。我家乡安徽境内天柱山本为南岳,而后尊位却被衡山夺去。东京汴梁城在宋代何等的繁华,一幅《清明上河图》为其留下历史见证;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在李白吟诗送孟浩然的唐朝是多么的“烟花三月”,今天成了普通的小城,而当年属江苏的松江府,却成为今日繁华耀眼的东方魔都。
一切皆运气,主宰唯有天。对于江河来说,奔赴大海始终是不变的理想,是河之梦。在中国古代,能独自完成入海的河备受朝廷崇敬。废黄河又称古淮河,她就在我眼前,我逡巡在她的堤岸。有人说淮河是一条最倒霉的河,它悲催的命运并非缘于自己没志气,而是偏与强者为邻。强邻总要生事,如墨西哥遇到美国。淮河年均径流量达六百二十二亿立方米,与黄河不相上下,水质清澈见底,更胜黄河的污泥浊水,但是如今的淮河,已经成为长江的臣属。
三
我的家乡枞阳县,是引江济淮工程的起点。
我在舅舅家吃鱼, 肥而大的胖头鲢,据说跳上来有小胖伢那么长。抱又抱不住,舍又舍不得,大鱼入怀喜坏了人。鱼味至鲜,是纯正的长江鱼味,可是长江禁捕,哪儿来的江鱼? 舅舅告诉我,本县标志性的枞阳大闸正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引江济淮”新闸。我去观看开闸,那水飞流直下,气势吓人,轰轰隆隆,水星水雾,银河壮瀑。我刚走到闸下空心的水泥草坪,浑身衣服和鞋脚已被打得精湿。傍晚,夕阳在天又仿佛不在天,水的飞沫罩下,人们在闸下的栏杆外欢喜地沉肩, 伸着手,弯着手臂,像迎接初生的赤子。跳了跳了,有大鱼飞上来啦! 原来有这么多观众,热热闹闹地等候“长河大鱼跳龙门”呢。引江济淮的入口长河,是长江的夹江,沿新闸往上游走,我参观又一座巨型船闸,连同一道如虹的崭新长桥, 车辆不过老枞阳闸,而在这“长虹卧波”的新桥上面爬坡而上,像是龙飞在天了。许多河闸、许多设备、许多标志、许多彩绘牌,这里就是“引江济淮工程”枞阳段。我忽然生出许多感慨:淮河水本来就是流向长江的,已经流入长江许多许多年了。一边是淮水入江,一边是引江济淮。这里面一定有着某种深刻的道理,如枞阳话“翻筋倒板”逻辑,相对的,逆向的,像是河鱼的“溯游而上”。
三千年前漆黑宁静的夜空下,一轮蛮荒的月亮银光照彻大地,一条大河在芦苇野草中静静流淌,一种叫“淮”的短尾鸟群栖于河边;偶有野兽的叫声,那是山上森林中发出的。远古,洪荒,弱肉强食,山、水、鸟、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平衡与宁静之中。这条大河,因生存着大量的淮鸟而得名。
枞阳话有一个词,“淮洪人”, 说一个人有点颟顸不管不顾,叫作“小淮洪”。我读《金瓶梅》做笔记,小说多次出现“淮洪”一词。雪娥向月娘投诉潘金莲:“一句话儿出来,她就是十句顶不下来,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什么骨秃肉儿拌的他过。”家乡位于长江淮河之间,从情感上讲我于长江亲些近些,因为简直出门就是长江。小时听广播本省和全国天气预报, 大人们总问:“可报江淮之间了? ”
家乡枞阳有“先让礼让”故事流传,黄河此处我想赠一个雄性的“他”字,他绝不是谦让的六尺巷,他自身强壮得就像一匹西北虎在鹿麂的面前,猛虎要生存必须捕食,于是侵袭和攻掠,黄河毫不客气地占领了淮河的水道,当仁不让地将之据为己有。遇此突袭,淮河怎么办?对抗,交涉,然后退让,默默另行改道,奔向南方而在一片洼地淤积,汇成了洪泽湖。成了湖也不要紧,还可以奔大海而去,可是河一旦变成了湖,就改变了性格,也就改变了姓名,洪泽湖的水再流出来, 成了许多细小支流,有的变成了人工干渠。洪泽湖周边的总渠干渠,我记不清多少次乘车和开车经过,那被高高“架”起来的水,有的地段与古运河交集, 有的地段与地下泗州城相会。宋人杨万里有诗《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一曰: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诗人想说的是, 南宋就这么大个气魄,金人打到黄河就决河改道,打到淮河就两岸咫尺南北对峙,打到长江就指望天险划江而治。同是南宋诗人的辛弃疾在江南北固亭上更加悲壮地忧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船离开洪泽湖岸边,到了淮河心情就变得不好,何必要说到遥远的桑干河才算塞北边境呢!
四
岸边有一座小小的木亭子,我进去坐下来。亭子旧了,也残破了,六角形的座椅早已揭去了木皮,露出底层的三合板和固定用的铁钉子。亭柱是原木,上了层清漆,原木木纹看上去仿佛一条条粗犷而又细腻的河流, 又像是祖国独特的山河地理,散发着古老文明悠悠的质朴香气。一条小花狗也是进来避雨的, 无声来到我的脚边,样子很想要啃我一口,又没敢张嘴。我望着河发呆,狗望着我发呆。一位染黄发的小伙进了亭子, 先是拿手机发微信,大约发出去了,便死死盯着屏幕,仿佛钓者注目鱼漂。半天没动静,拿起拨号,然后贴在耳朵上听。
并非正式标志的“古黄河大桥”的桥肚里,停着辆电动车,车的一侧绑着钢丝筐,筐里放着一只剪口的方形塑桶,桶里没放水,有鱼,是活的,无助地蹦跶。一位鬓白渔者正在河边拾掇网纲,画面像《老人与河》。“老大爷,哦,老师傅,鱼多吗? ”我请教。老人不答。网纲上很脏,沾着黑色河泥、螺蛳、小蚌,还有一些垃圾,老人一边抖一边收拾着渔网,偶尔拣出一条小鱼来,银亮亮的身段,饱鼓鼓的眼睛,活蹦乱跳着。小鱼大约不知它的蹦跳多么徒劳:上了岸,失去水的滋养,更多地消耗体力,只能使自己离餐桌更近。鱼的一生结束了。
废黄河,又称故黄河、咸丰故道、淤黄河、黄河故道,源自河南省兰考县北,过民权县、商丘市、安徽省砀山县北、江苏省徐州市,经宿迁市南、淮安市北,再折向东北方向,过涟水县、滨海县北,由响水县套子口(废黄河口)入黄海。提到兰考县,便想到焦裕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兰考遭受严重内涝、风沙、盐碱,他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与自然灾害作斗争, 努力改变兰考面貌。兰考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否与“废河”有关呢?“废河”在淮安段,起自淮阴区五河口,流经清江浦区、淮阴区、经开区、淮安区、涟水县,在苏嘴镇流经盐城市后入海。黄河夺淮之后, 带来了难以计量的泥沙,泥沙愈积愈多,便抬高了河道,古淮河河床升高,再升高,终于将入海口淤塞,黄河淮河的水都不能注入黄海了。被淤塞抬高之地全面沙化,干旱而盐碱,“三农”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也正像兰考民谚歌哭的那样:“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去逃荒。”这时候的黄河犹自潇洒,这条黄色浊龙把腰臀扭摆扭摆,下游再摆回到了山东省境内,最终像酣畅地解手一样, 把滔滔黄浪注入渤海,从而完成了赴海的梦想。从自然的角度看,河又何错之有? 混浊厚重得发黄的带着泥腥味的河水, 大胆而小心地交汇、交涉,最终交融到浅蓝然后深蓝而咸腥的海水中。高山不让一抔土,大海终须纳细流,从此,河的姓名不再是河了。今天的黄河在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入海, 我猜,“黄河口” 这个镇名必出现于决口改道的1855年之后。
“儿多母吃苦,滚糊滚粥菜遭殃。”说回这古淮河,可就苦了,她带着一肚子黄河遗弃的浊浆苦水,却又失去了排泄向海的出口,便淤积,淤积,成一片洼泽,被迫做成了一盘洪泽湖。洪泽湖鱼也香来米也香,尤其是“洪泽湖小鱼锅贴”最为有名。取小鲳鱼、小鲴鱼,胣肚鲜煮,辣香调料,大火煮沸,再小火慢炖,生铁锅边,趁鱼香热气,煎贴小麦粉粑于锅帮。那小鱼锅贴,配上洋河酒,我多次在进货途中,特地绕道去品尝。可是小鱼再多,也比不上唐朝的大鲈鱼,郑谷《淮上渔者》写道:
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
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
唐朝的淮河, 就是今天我脚边的这条———废黄河。
五
老渔人又接连撒了几网,鲜有渔获,却并不显出失望,嘴角仍挂着淡淡笑容。他的网撒得较为业余,简直可称“菜鸟”:不圆,不开,也不远。几乎不能叫“撒”,充其量只算是“抛”“甩”。但是否不是网的问题,而是河的问题,鱼的问题?
人要发财,地要发达,时来铁是金。洪泽湖做梦都没有想到,南宋和黄河一动,竟把自己做强做大了, 就像一个自身条件并不好的龙套意外做了主角, 竟在今天的中国五大淡水湖中稳坐了把交椅。洪泽湖原为浅水小湖群,古称富陵湖,两汉以后称破釜塘, 隋称洪泽浦, 至唐代始名洪泽湖。1128 年以后,黄河南徙经泗水在淮阴以下夺淮河下游河道入海,淮河失去入海水道,在盱眙以东潴水, 原来的小湖扩大为洪泽湖。洪泽湖主流注入宝应湖和高邮湖。京沪线上的常客,进货常往来于苏南苏北,也恰依河流的方向。车过高邮,我总要吟诵秦少游:“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此作如水温柔,被誉为女郎诗。再读几百年后汪曾祺《大淖记事》系列小说,路过高邮街上小吃, 总想寻找小说里的小锡匠或小和尚明海。淖,即烂泥、泥沼、湖泊。如果没有那一场黄河夺淮形成了淖, 人间是否也就没有了“淖”的故事? 文学史上是否就会少了高邮的经典?路过高邮,我也关心高邮湖走向,感觉水到这里就变得简单了:距长江近了,就像俗语里的老辈疼下辈,水往低处流,高邮向江都,经邵伯湖六闸,最后在扬州三江营汇入长江。既至江都, 必提杨广,这个风流奢靡的皇帝,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京杭大运河。这个风流蕴藉的皇帝,同时也开创了《春江花月夜》格,而后才有张若虚的孤篇盖全唐: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潮水涌动,青苇淹摇,正是涨水季节,古淮河河身变得健硕,河面很阔,那根粗大的水泥桥柱旁,湍急的水流打着漩涡,水面上的漂浮物时尚而缤纷,白色的饭盒、红色的塑块,在水面上欢快飞跑,像一只只小而欢快的轻舟。
六
沿河踱步, 一座桃花坞公园截断河沿路,小道在此变窄,直至消失,视野却陡然宽阔, 无数的小路如无数的小溪在意杨林里流淌。此岸一片高大意杨林参天挺拔,被向晚和风轻轻地抚摸, 树叶发出欢快的回应,沙沙响声像雨点,又若鼓掌,似洗牌。杨树林中密密匝匝,光膀子的老人、穿背心的老人,长发的老人、短发的老人,白发的老人、黑发的老人,男性的老人、女性的老人,老人们专心致志一丝不苟, 叽叽歪歪又斤斤计较地搓着麻将。妇女带小孩子们在这里玩耍,捉迷藏、扑蝴蝶、网蜻蜓。林子外头,小吃摊一字摆开,捞凉粉的、煮螺蛳的、炒米线的、炸油端子的、烤肉串的……
“毛蛋呀,活珠子———”小电喇叭里的女声,高音然而如古淮之水一样温柔,仿佛邻家小妹来到了门口, 那柔声叫卖使人产生流口水的食欲。一直想吃一回“活珠子”,及至吃到了嘴才知, 是孵小鸡失败的鸡蛋“活”成了珍贵的“珠子”。嚼着那韧韧的未成之筋骨,蛋的滑韧、肉的细腻、软骨的酥脆,唇齿绕着淡淡的臭味,然而久嚼生香。
恍惚觉得,这,也许正是古淮河的滋味。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