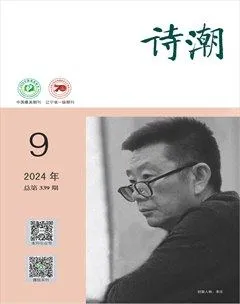麦须的诗 [组诗]
卡佛的量子时刻
我在读美国人雷蒙德·卡佛的
《到2020年》——
像是春天掉下的樟树叶子
一个陌生人和一些熟知的生活
他写得很好,但这不能让我停止发笑
他说:“那时我们中的哪些人
将会被留下,衰老、恍惚、口齿不清”
他死于1988年的2月,是肺癌
我笑得很大声,隔壁办公室小姑娘
的脸在门口晃了一下
之后我开始沉默,我发现
的确不是他,而是我和此刻,2024年的4月
但我仍然在2020年的昏暗里摸索
我想起我的那些朋友,想起
那些不值一提的往事
如果不是他,我将如何悄悄地沉没
那么应该是他赋予的这个时刻
2024的2020,或是1988年前的某个夜晚
它们交叠着,是作为他的一次复活
还是那些晚凋的樟树叶子?也许我早已死去
“他用手指摸索你的灵魂”
一个叫作狄金森的女人
和一个不叫狄金森的女人
或是一个狄金森和另一个狄金森
她们裹着围裙,带花边的和不带花边的
走进厨房,点蜡烛或是煤油灯
有窗户的话就可以
看看窗外,黑有两个原因
没有光或者没有窗
但都不要紧,黑是一些石头
可以摸着,尖锐的
长牙齿的,软绵绵的
凹陷的,空荡荡的,坠落的
除了烤面包,也烤红薯
蛋和鱼,用嘴吃的和不用嘴吃的
煎和炸,端去给父亲和别的男人
还有一些是花草和云朵,或是孤影
她们曾抓阄或接受洗礼
也曾喝下汤药或享用葬礼
她们写或者不写,听莫扎特或是雀语
她们在厨房,在地里,也在纸上
她说:我还活着,我猜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
无须告诉我
你将要去往哪里
也无须告诉我
你为何要动身离去
伊萨卡,伊萨卡,遥远的伊萨卡
乌云在翻滚,遮住
更宽广的海,天空的额头
黑铁一般没有丝毫光亮
落叶的帆影在旋转
伊萨卡,伊萨卡,无尽的伊萨卡
闭上嘴,不要再说话
风暴里只有风暴,当你跳上船头
砍断缆绳,只有那无比巨大的
瞬间,那永不沉没的瞬间
伊萨卡,伊萨卡,没有手的伊萨卡
弗罗斯特的小径
现在它们同样在我的
林子里,从迷雾遮挡的远处
行进到我的面前
行进到所有人的面前
一直就在,不是吗
远在我们出发之前的存在
相向而行的交会
无论路边会长出什么样的花草
再迟一点我会抛开这样的
惶惑,当黄昏降临
一幅早已绘就的长卷铺陈将尽
拢起手,回味那些繁复
拆解成的细节,你有三个
选择,其一,其二,非一非二
但绝不会出现第四个
“人不能同时拥有一种生活
以及对这种生活的赞美”,我们
自然而然地相信怀疑
竭尽全力去面对每一次选择
并以此确定,我们选择了无人的那条
石川啄木与和尚良宽
持花逃逸的良宽和尚
于今晨坐化
握着不停漏下的沙的啄木
也因咳嗽离世
手扶他们的灵柩
想着不曾见过的他们的模样
——扮孩子的老人
扮老人的孩子
无二的顽皮,为偷吃园中海棠果子的某人
画 皮
比如那只鬼
那原本不具形态的存在
那张因极度悲伤和恐惧变得
狰狞的绿脸
你得在语言里描摹另一张脸
小心翼翼的,如同变色龙
悄悄固定其体色
细微的吸收与融合
你一直知道
必须掩埋一部分真相
即便只是无知
那张绿脸之后的绿脸
指引你成为自我中的自我
更多的镇静剂
来自窗棂外更多的眼
更多的你看着
你的赤裸,而你仍是鬼
仍在夜里脱去皮囊
梭视,巡游,总在尝试
一口咬下自己的头颅
众 神
有些事物我们看不见
但不影响它的存在
以一亿种或只是一种方式
进入我们,围绕我们
选择是玄妙的,或是
不愿看见,或是不能看见
那个被放大的盲点
是树叶,也是摘星的高楼
或是不需要看见,或是
看见本身的背离
或是不被河流所接受
而存在,或只是因为消失
我可以为你描述一只甲虫
也可以为你描述一具
干瘪的被蚂蚁抬着的尸体
但你要注意,你听到的或只是
一条腿,一根手指
或只是某一只甲虫,某一具尸体
你永远不会想进入的不仅是
另一个灵魂,也是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