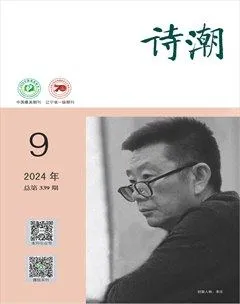近作十二首

力 量
种子推开头上的土块,石块,
树根让城市的水泥地面鼓起,变形。
春天,无数花叶从草木的身体萌生。
燕子的翅膀只有几寸宽,
它们每年丈量一万里的距离。
空气几乎不存在,
但它愤怒的时候奔走呼号,
推翻房屋。
水没有骨头,
但雕刻着全世界的海岸,
像无数把刀。
今夜的北斗
北斗像一只手,一个箭头,
指向东南。
是风要从东南吹来,
鸟要从东南返回吗?
东南是大海的方向,
那里黑夜笼罩着黑的波涛。
整个世界都仿佛向东南倾斜,
河流不自觉地向东南跌落。
风的位置
很难知道风在哪里。
它喜欢在杨树的身旁停留,
把它的叶子朝各个方向摆动。
松树身旁很少有风,
也许凝重的松树在自己周围,
创造了一处平静的空间。
也许因为松树的手指像是针,
能够刺痛,但无法捕捉,
风从它的指缝间流走。
柳树的长条善于摇曳,
于是常常有风从那里经过。
夜雨之前
一块乌云盖住了世界,
它与夜一道无声来临,
仿佛夜是它最好的掩饰。
空气里颤动着期待,
不知天空将落下怎样的消息。
低低的乌云之上,群星注视,
它们只看见乌云的脊背。
月光照在那崎岖的脊背上,
照见它不息涌动的高峰,深谷。
意 外
诗是意外,爱是意外。
为什么意料之中的礼物,
仿佛也降低了价值?
春天会来,但不确定在哪一天。
一只鸟升空,可能向东,可能向西。
在生与死两个固定的点之间,
我们飞翔,即兴表演。
同时我们祈祷那些黑色的意外,
永远无法萌芽,像铁的种子。
春天出现在一切时代里
春天出现在一切时代里,
在盛世,在乱世,
在敌人占据的长安城,
在人们饥饿的日子,
在人们看手机,开车的日子。
最初令人惊异的桃花,
依然灼灼,令人惊异。
海棠依然在桃花之后。
春天每年出现,永远年轻。
它不变的故事,
织入我们杂乱的故事。
寂静的花朵
诗的花朵只在寂静中开放,
像是夜晚的昙花,
像是森林深处的祭坛。
它在喧嚣中枯萎,
被喧嚣刺中。
仿佛一种易受惊的动物,
随时准备逃走。
仿佛珍珠沉睡在海底,
潜水者需要潜入孤独。
淘 洗
一条大河日夜淘洗,
它的泥沙中或许会出现一粒金沙。
一个生命经过许多晨昏,
凝聚为一首诗,一支歌。
仿佛人只是材料,
风一样过去,不留痕迹,
而风中沉淀下来的诗与歌,
才是一切的目的。
河流的终点
河流抵达了大海,
它们的终点,目的地。
它们走那么远,那么曲折的路,
就是为了清空自己,失去自己,
为了不再被遥远的声音召唤。
在大海里它们变蓝,变咸涩,
变为鲸鱼的家园。
它们与来自世界各个高山的水汇在一起,
它们无法容忍各自分开,
拘束在各自的河道中。
我们已经在交出自己
我们仰望天空一分钟,
把生命的一分钟交给天空,
它在天空融化。
我们注视一只飞鸟一分钟,
那一分钟我们交给它,
由它带走。
我们为一件小事焦灼,
把一些分秒,一些梦交给那件事,
它把它们绞碎。
我们像投资者分配自己的财产,
我们像穷人,一无所有,只剩下时间。
在没有完全交出自己之前,
我们已经在交出自己,
我们已经变成别的事物的质料。
罪 感
春天来了,
我们站在花朵旁,
心像花朵一样绽放。
这时一个捡垃圾的人走过去,
我们的眼睛中有了罪感。
有时候我们因一本书而大笑,
因彼此而大笑,
然后我们想起战争,饥饿,
笑容在我们脸上凝固,
蒙上了灰尘。
仿佛只有孩子可以大笑,
因为他们是新来的,
还不知道那些,
还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的后背上没有负担。
格式化生活
翅膀,乱发,第六根手指,
一切多出来的部分,
都被剪去。
少的部分,
心中,脑中的一个个孔洞,
被填补以泡沫。
然后人们显得充实,健康,
只有他们自己听见风在那些孔洞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