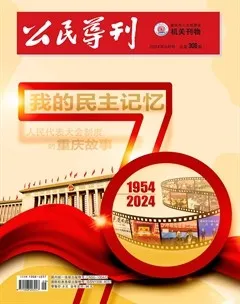陪诊师,这个“临时家属”需正名

去哪里挂号、在哪里就诊、到什么地方缴费……面对迷宫一般的医院和复杂的就诊流程,你是否会感到不知所措?对于一些人来说,独自看病不仅仅孤独,更多是无助。
近年来,我国职业陪诊服务需求日益旺盛,陪诊服务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因陪诊师的从业资质、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缺乏明确界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让这一新兴职业在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同时,也伴随了越来越多诸如“临时家人”“换汤不换药的黄牛”等争议。
作为潜力巨大的就业方向,陪诊师为何会存在诸多乱象?行业未来该如何发展?
8月26日,人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李平预约了西南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专家号。
就诊当天,李平通过社交平台购买了“代问诊”服务,全天服务价格为399元。谁知在他付款后对方又表示,如果需要代取报告、代邮寄,则要另行加收服务费。
为了不让前期投入的费用“打水漂”,李平只能按照陪诊师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加钱,以确保自己能够顺利就诊。
“感觉自己被套路了!”李平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李平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今年5月,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的王女士预约了新桥医院的无痛肠胃镜体检,并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一位陪诊人员。
然而,支付完100元定金,她却被对方直接拉黑,只得独自前往医院就诊……
作为近年来的新兴职业,陪诊师被视作有效缓解独居老人、行动不便患者、异地就医患者等群体就医困境的有效补充。
但现实并没有设想的那么美好。
陪诊服务宛如“开盲盒”
为了给年迈的母亲寻找一名靠谱的陪诊员,陈玉潘伤透了脑筋。
陈玉潘是家中独女,在上海从事外贸工作,很难照顾到独自在重庆生活的母亲。
前几年,疾病接二连三地袭击了陈玉潘的家庭。
2021年冬天,陈玉潘的父亲在一场高烧之后,因并发症去世。紧接着,陈玉潘的母亲又在上楼梯的时候突然摔倒,送医后被查出患有轻微脑梗。
陈玉潘本想接自己的母亲去上海生活,但其母亲因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等现实因素,仍独自留在重庆。
“我前几天打电话回家,听到她一直在咳嗽,才晓得她感冒了。”母亲身体有恙,让身处外地的陈玉潘非常紧张,她担心母亲因感冒引起并发症,坚持要求母亲去医院就诊。
但是陈玉潘母亲觉得感冒是小病,没有必要去医院。在陈玉潘的再三劝说下,她才勉强答应。
考虑到母亲患脑梗后行动缓慢,身体也比较虚弱,陈玉潘想找一位陪诊师,接送母亲到医院,并协助完成各项检查。
然而,找一位合适的陪诊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陪诊师主要工作职责包括协助患者办理就医手续、陪同患者就诊、提供医疗咨询和建议、协助患者与医护人员沟通以及关注患者病情变化等。
“我一问才发现,许多陪诊师,都是年轻的小姑娘在做兼职。她们要么没有相关证书,要么不愿意上门接送,要么就是没有照顾老人的经验,我担心老人在看病过程中,遇到需要协助的地方,她们处理不了。”陈玉潘说。
最终,有一位陪诊师的条件勉强让陈玉潘感到满意。
这位陪诊师表示,自己持有护士证,还有急救证,有三年多陪诊工作经验,但是服务费用也增加了许多——半天的服务,需要陈玉潘支付500元。
就在陈玉潘即将下单的时候,这位陪诊师表示自己可以帮忙获取预约已满的专家号。
这种类似于“黄牛”的行为让陈玉潘很反感。犹豫再三,她放弃选择这位陪诊师。
“钱只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我发现自己没办法仅凭网络上发过来的护士证和急救证照片,就把老人交给这样的陌生人。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陈玉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记者在小红书、大众点评等平台搜索发现,以个人、机构等名义提供陪诊服务的账号或商家不在少数,但在服务人员资质、定价、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
部分陪诊师称自己是医学生或护士,但以涉及隐私为由,拒绝提供相关学历、从业证明。
这就导致消费者在选择陪诊服务时,宛如“开盲盒”:大家并不知道,自己选择的陪诊师是否能够提供合适的服务。
陪诊市场亟待规范
在老龄化趋势加剧及医疗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职业陪诊师行业在重庆市乃至全国范围内迅速崛起,成为医疗服务领域的一股新兴力量。
然而,这一新兴行业的快速成长也伴随着诸多待解问题。
据了解,目前陪诊师行业主要遵循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发布的《老年陪诊服务规范》、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批准发布的《陪诊师职业技能规范》等团体标准,专门针对陪诊师行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
另外,陪诊师行业的主管部门尚未明确。
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行业监管与服务指导,管理职责归属模糊,多部门共同参与但缺乏统一管理,导致监管效能有限。
此外,相关技能培训体系也不统一。虽然各地政府部门联合高校、协会、陪诊机构等积极组织小范围的陪诊师职业技能培训,但覆盖面和深度仍显不足。
目前绝大多数陪诊师都是在社交平台上获得订单,而游走在互联网上的陪诊师专业素质更是良莠不齐。
消费者最关注的服务价格也缺乏统一标准。一二线城市普遍为半天300元到400元、全天500元到600元,三四线城市一般是半天200元、全天400元。
“缺乏统一标准规范是目前陪诊行业的一大痛点。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尚未建立,加上通讯工具特别发达,难以杜绝市场乱象。”专业医疗陪护机构“佑倍护诊”重庆负责人张丹表示。
“一个男生打算做陪诊小程序,于是接单体验,视频点赞量有900多。”张丹看得十分难受,“一群外行人来凑热闹,把行业搅得很浑。”她注意到,不少陪诊小程序并非由有经验的陪诊师管理,“谁都可以开发个平台,让各地兼职陪诊师入驻。”
张丹表示,自己供职的这家陪诊平台招聘陪诊师时,有完整的审核流程,持有护士证的人才可以申请入驻,还要进行笔试、面试考核和陪诊培训。
面对行业现状,张丹建议,专业的陪诊公司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自律,规范陪诊师的行为,加强专业化培训。
立法规范行业发展
“陪诊师尚未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缺乏明确的监管框架和标准,行业乱象频发,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根据陪诊师行业发展趋势与从业人员规模,适时推动陪诊师职业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确立其法律地位。与此同时,制定专项法律法规,明确主管部门、服务范围、服务流程、资格要求、收费标准及监管机制,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针对目前陪诊师行业现状,市人大代表、上海中联(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卓建议,应明确陪诊师的职业分类与法律地位。
陈卓还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对非法陪诊行为的打击力度,实施严格的监管,建立陪诊师实名注册与持证上岗制度,确保从业者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而针对市场上存在的培训机构培训质量参差不齐和虚假宣传的现象,陈卓表示,可以设立国家级或省级陪诊师培训与认证中心,统一制定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并加强对培训机构的资质审核和教学质量评估,确保培训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引导和鼓励培训机构加大在员工培训方面的投入,提升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可喜的是,一些省份已经开始对规范陪诊服务进行探索。
从2020年起,浙江省的浙大二院、浙江医院等多家医院先后推出公益陪诊服务。
2023年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开通公益陪诊服务热线,组建了一支由医务社工、医护人员和基层志愿者联动的陪诊团队;2023年9月,首届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培训启动,面向各社区为老服务工作人员;2024年3月,上海市首批575名参训学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获得由上海开放大学与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共同颁发的“上海养老服务陪诊师”证书,这标志着上海市首批陪诊师已持证上岗。
重庆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也在积极开展志愿陪诊服务。
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重庆市已有129家医疗机构实施了就医“一站式”服务,该服务集成了咨询、挂号、缴费、取药等多个环节,能为患者就医提供更多便利。
相信在各方力量的努力下,陪诊服务会愈加规范,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