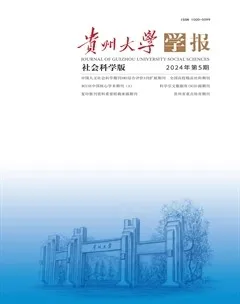母职回归:农村家庭抚育模式变迁及其生成机制

摘 要:家庭抚育是家庭再生产的重要过程,是塑造地方社会文化的重要方式。基于鄂东农村的经验调查发现,当地农民家庭形成了同代照料、隔代抚养以及亲职教养等不同的家庭抚育模式;在家计模式“全工化”、家庭结构少子化以及城镇化的家庭现代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开始在家全职抚养子女。大量年轻女性劳动力的市场闲置是家庭为实现发展目标并应对教育转型的策略化结果。研究发现,集体供养、情感满足、角色转化与舆论支持构成了农村打工母亲回归家庭抚育的生成机制;而母亲亲职回归不仅缓和了农村家庭隔代抚养的困境,满足了教育模式转型对家庭抚育主体的要求,还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
关键词:家庭抚育模式;母职回归;城镇化;家庭发展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4)05-0106-08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育养后代是家庭的基本生活面向,包含着生育、抚育的复杂活动,延展于家庭再生产的进程中。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育养后代发生了极大转变,与传统的重“生”不同,当代家庭愈发重“养”,将孩子抚育成才构成主要的家庭目标。关于家庭抚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既有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可以概括出以下三类视角。
第一类是文化视角的阐释。有学者认为家庭抚育构成了生育文化实践的重要内容,对于家族绵延、种族延续具有重要的意义[1]。也有学者认为家庭抚育受到地方性文化的影响,地方性文化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儿童抚育方式,还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2-3]。还有学者对中国的家庭抚育文化进行了探讨,认为抚育子女使婚姻、家庭永续,实践着家庭内部的伦理秩序[4]。
第二类是制度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学者主要讨论国家、政府在儿童抚育上的角色和功能。有学者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后,集体照顾体制和家庭形态变迁受到冲击,家庭无力回应儿童的抚育和照顾需求[5],而家庭责任过高、男性角色缺失与国家福利不足使得中国家庭面临着严峻的儿童照顾风险[6],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积极应对儿童抚育事务,回应无法从家庭获得必要照顾与教养服务的儿童[7]。在农村地区,政府应更多向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进行政策倾斜,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8]。其中,女性群体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建立支持学龄前儿童抚育的国家制度,解决职业女性的后顾之忧[9],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性别正义,保障女性就业权益[10]。但是,也有学者注意到,国家政策干预实际上造成了一系列不平等的社会效果[11],需要进一步反思政策介入的路径和边界。
第三类是市场视角。在这一视角下,部分学者讨论了家庭抚育的市场化替代现象,市场被视为提供专门托育服务的主体[12],但目前的市场托育仍然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13-14]。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试图向家庭回归,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家庭育养方式及特点,尤其是对家庭抚育中的权力关系进行讨论。有学者认为收入增加及男女平等的观念使得传统的抚育方式发生变迁,家庭中逐渐形成了代际合作的育儿模式,尤其在城市,双方父母和男性逐渐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15]。在代际合作育儿过程中,代际关系呈现出“台前幕后”式的抚育模式和权力格局[16];同时也在家庭内形成了“严母慈祖”的分工体系和弹性权力关系[17]。
既有研究为理解家庭抚育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对于家庭抚育模式的认识;但既有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学者是从问题视角的立场来看待家庭抚育的不足与困境,并试图从家庭之外寻找相应的儿童抚育出路,而较少看到家庭在儿童抚育上的稳定性、发展性和灵活性优势。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极少数回归家庭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于探讨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关系与家庭政治实践,而忽视了对于当前阶段家庭儿童抚育模式形成机制的探索。作为家庭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儿童抚育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迁,表达了家庭变迁的面貌,对于顺利实现家庭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鄂东J村的田野经验为基础,回归家庭视角分析农村的家庭抚育问题,试图呈现农村家庭抚育模式的变迁过程、机制,探讨母职回归家庭抚育对于家庭发展与转型的意义。
二、J村农民家庭抚育模式的类型、特点及变迁
1.田野介绍与访谈对象
2020年5月到6月期间,笔者在湖北省东部的J村进行家庭抚育的专题考察,通过参与观察与半结构访谈的方式,了解了农民家庭的生计模式,家庭抚育历史,对家庭抚育的发展变化有了一个整体上的认识。J村地处长江支流的巴水河上游山区,全村有298户,共1 000多人,包含着三大姓和若干小姓;该村共有耕地面积888亩,山林面积3 980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型村庄。九十年代末期打工经济兴起,J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主要向东莞、佛山、温州等远地打工,少部分开始在本地打零工;2008年以后,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外出务工规模急剧增加。近年来,随着当地旅游产业与房地产开发,城镇化以及本地服务业发展起来,部分农村中老年妇女开始在本地市场打工。总体上看,当地农民维持生计的方式愈益多样化并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
在笔者的11位访谈对象中(如下表),可以概括出一些特征:第一,从家庭角色上看,有6位被访者是主要作为家庭抚育责任的承担者陈述个人经历的,有5位是主要作为家庭抚育的对象来陈述成长经历的;但二者也有重合,有6位兼有两种角色的经历。第二,从人员受教育水平来看,青年一代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中老年一代。第三,从家庭结构来看,当地总体上呈现出家庭规模缩小和家庭少子化的特征。
2.农民家庭抚育的主要模式、特点及变迁
在集体照顾体制解体以及家庭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民家庭抚育方式也在发生转变,并且不同时期农民家庭的抚育方式存在着明显差异。笔者试图从抚育与代际关系角度对J村先后呈现的多种家庭抚育方式进行区分,并概括出以下三类主要的家庭抚育模式:
第一类是同代照料。同代照料主要存在六零、七零年代的多子女家庭中,通常是指家庭中的哥哥、姐姐承担了弟弟、妹妹的照料事务,既包括成员完整与功能健全家庭中的同代照料,也包含其他特殊家庭的同代照料。HX是J村一位五十三岁的中年妇女,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其读小学时,父母忙于生产,弟弟妹妹太小无人照看,她最终辍学在家照看三个弟妹,直到弟弟妹妹上学。同村LQ是一位三十岁的青年妇女,有一个与之相隔八岁的弟弟,在其读中学时期,父母外出打工,为照顾无人照看的弟弟,LQ每天请假回家,给弟弟做饭、洗衣服,傍晚再赶回学校上晚学习,直到弟弟上寄宿学校独立生活。在同代照料的家庭抚育模式下,年长的子女,尤其是女性往往成为父母的帮手,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父母的角色,在这种家庭抚育模式下,家庭内部形成了密切的代内互动。这种照料的持续时间较短,但是通常都是以牺牲年长子女,尤其是女儿为代价的,往往造成了家庭抚育上的代内不平衡。
第二类是隔代抚养。隔代抚养通常是指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承担起孩子的抚育事务。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年人普遍成为家庭孩童抚育的主体,既包含着老人作为主体对孙辈的抚养,也存在着老人作为辅助者参与代际合作育儿的情形。HM和ZC是两位27岁的职业白领,也是J村为数不多在城市有正式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两人都是家中的独子,自小开始,两人父母皆外出打工,他们被交由各自的祖父母来照看,并一直被照看到考上大学。同村26岁的ZW和LT则与前两人不同,在上学之前,他们的父母将二人送到外祖父母身边照顾,但在外祖母有了自己的孙子后,二人又被父母接回,再交给祖父母照顾生活和上学。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外出打工,父母将子女交给祖辈代为抚育的现象在农村十分普遍,形成了“隔代抚育”模式,而祖辈与孙辈共同生活,形成了“跨代的拟核心家庭”[18]。在隔代抚养的抚育模式下,祖辈全面负责孩童的安全、生活照料和学习辅导。隔代抚养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源于作为新生代的亲生父母的“独一代”对其子女难尽抚育之责[19],同时它也是新生代农民家庭生计模式转换和家庭弹性分工的结果。农村老年人在隔代抚养中发挥着重要的代际支持作用,但也存在着抚养主导权上的差异,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共同在子女家庭抚育上发挥作用,但作为祖父母身份的老人在儿子家庭上的支持力度更强,祖父母往往比外祖父母更普遍地构成隔代抚养的主体。在隔代抚养模式下,传统家庭责任和现代家庭梦想交织,祖辈影响着家庭抚育,同时其抚育行动也受到孩子父母决策的影响,子代不得不在寻求平衡中实现家庭的稳定和发展[20]。
第三类是亲职教养。亲职教养主要是由父母直接承担孩子的照顾、抚育事务。近年来,父母尤其是母亲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孩童的照顾、培养和管教。这种照顾模式下,家庭抚育事务主要由年轻家庭主导,并且也越来越成为年轻女性的生活重心。JS、YN和LL是近年来从J村嫁出的三位年轻妈妈,三人都育有两个孩子,其中年龄最小的LL,自其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便不再外出打工,在家照顾两个孩子;YN认为老人无法辅导自己两个女儿的学习,便辞工回家照顾孩子的吃穿用度和学习;JS为了照顾两个儿子,在县城买房专门照顾孩子上学,她表示“为了照顾他们的学业,我五六年都没有追过一部电视剧看看,干什么都是围着孩子打转”。一方面孩子成为青年父母的生活中心,另一方面亲职抚育体验也成为青年父母媒体社交的主要内容之一。有学者指出,父母的亲职抚育正愈益丰富化、精细化,亦趋向科学化和民主化,亲职抚育的观念实现了从义务到权利的意识转变[21]。但就抚育投入时间来看,男性与女性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女性越来越多地从工作回归家庭,投入在子女照顾、培养和管教上,这重新塑造了家庭生活面貌。具体而言,亲职教养的家庭抚育模式重新拉近了农村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确立并巩固了年轻一代在家庭抚育上的地位,但同时也增加了年轻家庭的抚育压力。与此同时,亲职教养的主导,并不意味着隔代抚养的必然弱化或削弱,后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以代际支持或代际合作的方式继续发挥着作用。
总之,从J村的田野调查经验来看,在近二、三十年间,当地农民家庭抚育的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迁,主要变化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抚育主体代际转换。家庭抚育天然地构成了父母的事务,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父母往往无法充分在孩童照料上倾注时间和精力,而多子女家庭中年长子代参与照顾则缓解了这项压力,但在家庭少子化时代,同辈姐妹兄弟难以弥补孩童照看力量的不足,而年轻父母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难以及时回应家庭抚育的需求,老人往往成为照顾的主体。尽管如此,老年人依据过去的经验和育儿方式抚育孩子,也无法真正回应新时代孩童的培养教育需求,由此,有着独立收入、更高文化水平以及更高教育目标的年轻父母最终成为家庭抚育的主体,并且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从工作岗位回归家庭,专注于家庭抚育事务。
第二,抚育任务在逐渐升级。最初的家庭抚育内容较为简单,包括生命安全保护以及最基本的生活照料,此后,随着子女越发成为家庭的重心,培育儿童学习成才逐渐成为两代父母抚育的任务和目标,尤其在当今社会,成才成人往往共同构成父母抚育子女的中心任务。
第三,抚育时间在不断增加。在以安全与基本生活照料为主的家庭抚育阶段,从孩子出生到孩子顺利成长为一个独立照顾自身生活的个体,家庭抚育时间较短,但在不断发展的教育目标之下,家庭抚育的时间开始大为延伸。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家庭抚育模式并非单一存在,而是与其他类型的家庭抚育模式共同发挥作用。
三、母职回归家庭抚育的社会基础与形成机制
1.社会基础
首先是家计模式的“全工化”转换。自九十年代打工经济兴起开始,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家庭逐渐形成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和家庭分工,通常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年人留守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并负责照顾孙辈生活和学习。形成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此模式下,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共同构成了家庭积累,并且非农务工收入逐渐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而老人在农村照顾孙辈,在相对较低的抚育成本下照看孩子,减轻父母的压力,极大地释放了家庭中的年轻劳动力。然而,近年来随着农村老龄化的推进和县域经济的发展,J村劳动人口逐渐退出农业生产,退养或是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尤其“八零、九零后”青年群体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当地农民家庭的生计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即农民家庭正在逐步形成以非农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全工化”家计模式,这种全工家庭的生计模式,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和积累,同时也为家庭抚育升级和母职回归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次是家庭结构的少子化变迁。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执行强化,当地农民的家庭结构发生显著改变。从家庭规模来看,子女生育数量减少,大家庭大为减少,过去的多子女家庭结构逐渐向独子家庭或两子家庭转变。八十年代之前,J村90%以上的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子女,但在八十年代到二零一四年左右,家庭子女数一般以一到两个居多,只有极少数的三孩家庭,而在放开二胎政策出台后,独子家庭生育二胎的现象极为少见,新婚家庭生育二胎相对较多。生育制度与生育政策影响了家庭的生育行为,也加速了家庭的现代变迁。在多子女家庭的时代背景中,家庭内外的抚养资源差异相差不大,而未成年子女往往依赖于父母的劳动与资源整合、分配以维持生活。在当今社会,尽管社会分化拉开了家庭之间的距离,但是在少子女的家庭结构中,一来子女本身成为家庭成员中的关注焦点,二来家庭内部的抚养资源分配格局相对缓和,这使得家庭资源的流向最终集中于子女身上,从而形成了农民家庭抚育模式变迁和母职回归的价值基础。
最后是家庭目标的发展性强化。家庭及其维系构成了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追求,在现代性的压力之下,家庭的功能面向被激发[22],家庭卷入现代化转型之中。家庭不仅要实现传统意义上传宗接代的价值目标,更要实现家庭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通过调动家庭自身的潜能而实现的,而就目前来看,农民家庭最主要的发展目标即是实现城镇化。城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包括异地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的模式,农民城镇化的手段和方式多有不同,包括婚姻、教育、买房以及就地就业等。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农村而言,子女教育是实现家庭城镇化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学者发现,隔代陪读日益成为农民家庭实现城镇化的重要教育策略[23],但与隔代抚育的水平和方式不同,亲职直接参与家庭抚育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效果,不仅避免了隔代抚养中的亲职缺失问题,还强化了对儿童的严厉管教和人格培养。城镇化同时作为农民家庭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激励着家庭的发展,也推动着家庭抚育模式的调适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家庭目标的转型升级构成了家庭抚育模式转变和母职回归的动力基础。
2.生成机制
一是婚姻市场洼地中的竞争与集体供养机制。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之下,男女性别比呈现出明显的失衡结构特征;而在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结构下,J村所处地带经济滞后形成了婚姻市场的洼地,女性劳动力大量涌入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带,加剧了当地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稀缺性;同时,本地婚姻偏好的存在往往使年轻女性在婚姻市场以及家庭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地农村年轻女性拥有劳动的自主选择权,既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外就业,同时也被鼓励打理家事而不用出外打工。J村越来越多的年轻媳妇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在家或是在镇、县租房以及买房专门陪读,由其他家庭成员定期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普遍形成年轻母亲在家照顾孩子,公公婆婆和丈夫外出打工挣钱供养家庭的情形。婚姻洼地以及女性资源稀缺使得女性在家庭分工上获致了优势权,刺激家庭通过集体供养的方式留住女性。而年轻女性则从打工场域回归家庭,其直接效果在于母亲亲身参与子女的照顾、培养和管教过程。
二是亲职抚育中的教养与情感满足机制。经典的研究中认为母亲与子女因生育结成了天然的关系,而父亲的养育才确立了父亲的角色,无疑将父母的角色分别置于结构化和建构的过程;然而事实上,血缘的纽带还不足以支撑当今社会中家庭健康亲子关系的形成,育养过程便是一个情感互动与亲密关系建构的重要途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隔代抚育在特定阶段完成了家庭再生产的任务,但是也引发了诸多新的问题。一是隔代抚育中的孩童往往受到祖父母过分溺爱的影响,而在成长教育中缺乏严厉管教内容;二是家庭抚育中父母在场的长期缺乏,使得子女与父母的情感建设与亲密关系发展受到影响;三是在新的家—校沟通环境下,孩童智识教育往往需要更年轻化、知识化的家长参与合作。以八零后、九零后为主体的年轻夫妇,相对于六零、七零后的祖父母,拥有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更现代的教育观念,年轻母亲回归家庭、参与子女的抚养教育,一方面可以克服隔代抚育中的诸多问题,同时也能够发挥年轻人在子女教育上的角色优势;另一方面,亲职抚养还满足了父母、子女双向的情感需求。
三是“台前”“幕后”转换中的代际合作机制。随着家庭生活重心的向下转移以及家庭的发展转型,城市代际合作的育儿模式愈发普遍。父母、祖父母甚至外祖父母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父母往往为孩子的抚育进行规划安排,并主导家庭的重大决策,祖父母与外祖父母通常帮忙实践这种规划,充当着“照料者”和“协助者”的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代际合作的育儿模式中,父母往往处在“幕后”并拥有抚育的主导权,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虽处在“台前”,但依从于父母的各项安排,无实质上的决策权。但就农村而言,代际合作育儿的家庭抚育模式并未成熟。在隔代抚养与亲职教养中,二者实际上都存在代际合作的关系,但是农村的隔代抚养实践中,祖父母往往具有教育的主导权,而亲职抚养过程中,祖父母通过支持子代家庭也间接支持着孩童抚育。不同于这两者,代际合作中的祖父母与父母在时间或程度上参与并没有明显偏向,但二者之间的分工与权力十分清楚。当母亲回归家庭后,农民家庭的隔代抚养模式发生了极大转变,父母成为家庭抚育的绝对主导者,祖父母主要成为家庭资源的提供者。J村不少农民家庭中五、六十岁的祖父母通过农业生产或是就近务工的方式获得收入,为家庭积累资源并向子代家庭输出,除了特殊情况下的帮忙照看,不再干涉孙辈的教育、教养。因此,年轻媳妇逐渐成为家庭权力资源分配的主导[24]。在这一抚育模式转换过程中,母亲既站在“台前”,同时也是主导,并且家庭抚育中仍然存在着代际支持与合作关系。
四是社会舆论支持机制。在具有差异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女性角色与家庭地位具有极大的差异,有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了南、中、北的划分,分别形成了“宗族性”“原子化”以及“小亲族”结构的村庄,女性的角色受到文化的塑造,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结构的挤压和影响[25]。在宗族性村庄,妇女往往被视为家庭,尤其是男性的附属;在原子化村庄女性往往被视为更加独立的存在个体,而在“小亲族”村庄,女性的价值裹挟在村庄社会的竞争评价中。因此,在职业和家庭之间,不同村庄中女性面临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舆论环境,而这些舆论环境对于她们而言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保护机制。位于鄂东山区的J村是一个非典型的宗族性村庄。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打工经济与交通现代化加速了当地的女性流动,并且现代教育提升了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与独立意识;但是,传统宗族文化的底色仍然影响深远,在家庭内部女性仍然被视为传统的依从角色。对于年轻母亲而言,进入劳动市场与照顾子女既是权力也是义务;而回归家庭抚育不仅源于她们有不进入劳动市场的选择权,也有文化传统的要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文化传统与社会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年轻母亲的劳动力闲置与亲职教养实践。
四、结语
就J村的经验来看,家庭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功能目标转变共同构成了母职回归家庭抚育的社会基础,而在这一基础上,家庭经济的集体供养、家庭教养与情感满足、代际合作以及社会舆论支持等多重机制的作用发挥,构建起了母职回归家庭抚育的物质、情感、关系和文化支持体系。
长期以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空间分割与最大化利用构成了家庭发展话语与“功能性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在家庭形态、家庭结构转变与家庭目标升级的复合作用下,家庭劳动力的“最优化”安排呈现出了新的内容。家庭抚育中的母职回归即是农村家庭积极回应新时代家庭发展“质”的需要的结果。当下,子代往往承载了家庭的厚重价值寄托,而家庭抚育则承担了重要的价值实现功能。在新时代孩童教养目标及要求提升的背景下,相较于同代照料与隔代抚养,亲职教养更加精细化、科学化,并且相较于老年人,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夫妇在学习辅导、家校沟通以及成长管教上更具有优势和发言权,农村的年轻父母由此也逐渐成为家庭儿童抚育的主导力量。部分农民家庭中的年轻媳妇不再打工,回归家庭专门照顾、教育、培养孩童。尽管从家庭劳动力利用上看,年轻女性劳动力受到闲置,但实际上,这种家庭分工是当下教育模式转型与家庭抚育精细化的要求,同时也是“全工化”趋势下家庭劳动力策略化安排的结果。
当然,母职回归并非是家庭抚育模式中的简单角色转变,包括家庭劳动力、代际关系、家庭成员角色、家庭权力等在内的要素,在家庭抚育实践中展演出了丰富的内容。在农民家庭由基本生活维持向现代化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农村家庭抚育模式经历了一系列变迁过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母亲的角色在家庭抚育事务上经历的复杂转变,从观察研究区域来看,近几十年来,她们经历着从离开家庭到退居幕后再到回归家庭的持续角色转换。越来越多农村的年轻母亲在家庭成员的合作、支持下,从幕后走到前台、从权力依从走向权力主导,成为孩童精细培养教育最主要的责任主体,而从中也可以看到,家庭抚育的支配权,也由最初的父权主导,逐渐发展到子代主导,并且家庭抚育内容、方式的决策权也逐渐转移到年轻一代,且进一步聚集到年轻母亲手中,这不仅直接作用于实现家庭儿童抚育的新目标,也为女性自身生命实践与家庭再生产带来了新体验和新秩序。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杨柳.沙岗村儿童抚育方式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3]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的成年[M].周晓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尤吾兵.黑格尔家庭伦理观的生成及其现代价值[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9-26.
[5]邓锁.从家庭补偿到社会照顾: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路径分析[J].社会建设,2016(2):28-36.
[6]李向梅,万国威.育儿责任、性别角色与福利提供: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展望[J].中国行政管理,2019(4):138-144.
[7]程福财.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J].青年研究,2012(1):50-56.
[8]畅红琴,艾平,范汀芳.我国农村地区儿童早期照料与教育的供给及选择[J].学前教育研究,2017(3):3-13.
[9]佟新,杭苏红.学龄前儿童抚育模式的转型与工作着的母亲[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1):74-79.
[10]陶园园.儿童照顾视角下女性就业权利保障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7.
[11]张亮.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4.
[12]杨雪燕,井文,王洒洒,等.中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实践模式评估[J].人口学刊,2019(1):5-19.
[13]韦素梅.上海市托育供需现状调查及对早教中心职能的再思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
[14]时扬.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15]张航空.儿童照料的延续和嬗变与我国0-3岁儿童照料服务体系的建立[J].学前教育研究,2016(9):14-22.
[16]王兆鑫.“台前幕后”:农村家庭儿童抚育过程中祖辈、父辈的职能分工和代际关系[J].社会建设,2020(2):54-65.
[17]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6):148-171.
[18]孔海娥.转型期农村抚育模式与家庭结构的变迁——以湖北省浠水县柳树铺村为例[J].江汉论坛,2011(8):136-139.
[19]杜娟.叠加的三角家庭结构模型:抚育模式的变迁与策略性选择[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
[20]郑杨,张艳君.独立与依赖:“隔代抚育”中代际关系的平衡与失衡[J].贵州社会科学,2021(6):75-84.
[21]吕浩静.青年父母的亲职抚育行为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9.
[22]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4-60.
[23]苏运勋.隔代陪读:农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与家庭秩序[J].北京社会科学,2019(9):66-75.
[24]冯小.陪读:农村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基于晋西北小寨乡“进城陪读”现象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12):60-66.
[25]贺雪峰.南北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王勤美)杨 洋 杨 波,张 娅 郭 芸,王勤美,蒲应秋
Women’s Maternal Role Returning: The Rural Family Nurturing Pattern Change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Experience Survey Based on J Village in East Hubei Province
QIU Ti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Wuhan,Hubei,China,430074)
Abstract:
Family nurturing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family and a significant way of shaping local social culture.Based on surveys conducted in rural areas of East Hubei,it was found that local farming families have developed various family nurturing models including same-generation care,intergenerational upbringing,and parental nurturing.With the “all-full-time worker” household management,the decreasing size of family structures,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families due to urbanization,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mothers have started to stay at home full-time to care for their children.The underutiliz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of many young women in the job market is a strategic outcome for families to achieve development goals and address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The study reveals that collective care,emotional fulfillment,role transformation,and public support constitute the mechanisms that lead to rural migrant mothers returning to family nurturing.The return of mothers not only alleviates the challenges of intergenerational upbringing in rural families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ition in educational models for family nurturing subject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stability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family nurturing models;maternal return;urbanization;family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