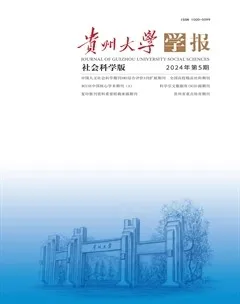网络“恶搞”行为的刑法规制边界
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与新媒介的融合发展,网络“恶搞”行为呈现泛化与异化趋势。网络“恶搞”由反文化向亚文化演进,其被赋予了表达与传播的功能并逐渐从个体向大众流变。网络“恶搞”的中性化、传播化、大众化使刑法对网络“恶搞”行为的介入与规制面临着现实困境。从法益类型化的视角来看,网络“恶搞”行为涉及的犯罪可以分为侵害国家法益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犯罪与侵害个人法益犯罪。在刑法介入网络“恶搞”行为时,其行为涉及的内容应为刑法所禁止的内容;在主观层面,行为人应当具有实际恶意与不法目的;在客观层面,网络“恶搞”行为须具有法益侵害的危害结果;在法律后果方面,以“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为代表的保安处分应当谨慎适用。
关键词:网络“恶搞”;刑法边界;法益;类型化;表达传播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4)05-0083-13
一、问题的提出
“恶搞”作为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社会现象,一直有着深厚的生长土壤。“恶搞”并非网络时代的产物。从先秦时期的“烽火戏诸侯”,到当今我国部分地区对新人乃至新人父母、伴郎伴娘进行戏弄的“婚闹”习俗,以及域外《堂吉诃德》对于骑士文学的诙谐讽刺和日本动漫的“KUSO”文化,都带有一定的“恶搞”色彩。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新媒介相互融合,“恶搞”行为在空间、方式、性质不断转换并日益泛化与异化的同时,也使网络“恶搞”行为罪与非罪的边界渐趋模糊,导致涉罪网络“恶搞”行为更易发生。面对愈加泛化与异化的网络“恶搞”,除了广电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先后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等部门规章、规范文件对其进行限制,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在刑事立法方面,2015年、2017年、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先后增加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侮辱国歌罪”以及“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等涉及网络“恶搞”的罪名,针对网络“恶搞”行为的立法逐渐呈现出犯罪化的倾向。在刑事司法方面,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诽谤等刑事案件解释》),对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辱骂、恐吓他人等行为的入罪量刑标准做了细化与明确;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惩治网暴指导意见》为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律适用提供指引,表明司法部门对网络“恶搞”行为实行严厉打击的趋势。
实践层面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对网络“恶搞”行为规制双向趋严的现状,在体现了刑法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也映射了我国“安全刑法”的形成之路。在“安全刑法”的安全、秩序价值与自由刑法的权利、自由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刑法法益论在实质上面临被逐渐蚕食风险的背景下[1],网络空间如何合理划定言论自由、行为自由、表达自由等与刑事犯罪的边界这个传统话题,无疑因网络“恶搞”这一新网络样态而引发的新问题拓展了新的讨论空间。但是,区别于当前对于网络环境下诸多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先行”,网络“恶搞”作为一个在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乃至政治学语境下讨论颇多的研究对象,其在立法与司法层面的“备受关注”却未引起理论层面法学学者尤其是刑法学学者的足够重视。具体而言,网络时代“恶搞”行为的泛化与异化为何带来了刑法的规制难题?刑法语境下如何对不同的网络“恶搞”进行界定与区分?刑法对网络“恶搞”的介入边界又在何处?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本文将作尝试性探讨与回应。
二、规制困境:网络时代“恶搞”行为的泛化与异化
区别于“婚闹”“无厘头表演”等传统的“恶搞”行为,网络“恶搞”并非简单的“网络+恶搞”或“恶搞上网”而是“恶搞的网络化”,即在网络空间通过网络手段对人和事物的夸张、剪接以及戏谑等。由于将网络“恶搞”行为纳入法学尤其是刑法学的评价范畴进行考量时,主要审察的是“恶搞”行为在网络时代的潜在危害性。随着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交互性、开放性等特征使恶搞行为在网络场域下逐渐中性化、传播化、大众化,网络时代恶搞的泛化与异化产生了网络“恶搞”行为的危害评价难题,从而让刑法对网络“恶搞”行为的介入与规制面临着现实的困境。
(一)反文化到亚文化的演进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互联网的出现和赋能实际上使恶搞经历了从反文化到亚文化的转换。作为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经典概念,“反文化”被视为是亚文化的极端状态以及“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笔下的“误入歧途的文化”和“文化的退化”,其自身“无序”“增熵”的非理性、非逻辑与主流文化具有较强的对抗性与割裂性[2]。就网络“恶搞”而言,无论是经典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被恶搞为网络短片《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参赛记》,还是早期主流媒体“网上恶搞是荣辱失范的‘败德行为’”要“刹住恶搞之风”的评价[3],其最初进入大众视野时自身也常常笼罩着反文化的色彩。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恶搞”逐渐向大众化与多样化演变,其越轨性、对立性也趋于减弱。当前更多的网络“恶搞”行为被视为属于亚文化的范畴,甚至部分网络“恶搞”行为还为主流文化所认可并接纳。官方对于网络“恶搞”除了拥有固有的“管控”态度之外,部分网络“恶搞”还会为其“借鉴”甚至“收编”[4]。正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虽源于对电影《无极》的恶搞与改编,但其下载量和影响度却远高于《无极》,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超越原著的艺术性、思想性;《暴走大事件》等网络脱口秀节目以嬉笑怒骂、戏谑恶搞的方式播报与点评现实世界的热点事件,实现对公共议题的关切与批判;《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更是发文向自发对“台独”分子进行恶搞的青年进行褒扬,称“这些自发组织的以90后为主的一群人充满阳光和自信的表现。”[5]当前的网络“恶搞”作为一种网络时代的文化症候虽在大多情况下仍难以与主流文化完全兼容,并体现出一定的反权威、反经典色彩,但普遍更加中性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和解,呈现出显著的亚文化色彩。
“刑事可罚性的条件自然必须是以刑法的目的为导向。”[6]如前所述,刑法之所以要介入网络“恶搞”,在于网络“恶搞”行为具有的潜在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作为反文化的网络“恶搞”与“大规模共同体”之间存在的核心价值冲突[7]。随着网络“恶搞”反文化属性逐渐被亚文化属性所替代,其破坏性在普遍意义上也被削弱,随之刑法也毋庸置疑地面临着介入网络“恶搞”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具体而言,从文化视角来看,当网络“恶搞”自身的文化属性发生变易并带来网络“恶搞”的外部社会认知发生转向,网络“恶搞”的爆炸式增长、多样化演进以及实质性分化将使对其进行反文化或亚文化评价的边界愈加模糊。网络“恶搞”作为一种文化样态,其自身潜藏的认知合法性评价判断将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背书。与此同时,诸如“自黑”“正话反说”“低级红、高级黑”等网络“恶搞”方式虽表面缓解了戏讥、讽刺乃至逆反、抗争等表达与秩序、权威、安全的紧张关系,但其实质内涵却无疑可能会更加激进。鉴于刑法作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其精确性是保障人权、避免罪刑擅断的有力武器。因此,当把网络“恶搞”放置到刑法语境中进行审察时,刑法如何回应不同类型网络“恶搞”行为背后的内生性价值模糊,区分不同网络“恶搞”的“恶”究竟是刑法意义上的“恶意”“恶劣”还是如“恶补”“恶战”等词语对事物的夸张表述,进而合理厘定网络“恶搞”行为带来的“风险”究竟是刑法场域中的法益侵害风险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中性风险,就显然成为了一系列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表达与传播功能的赋予
正如费尔巴哈所言:“犯罪是一个刑法中规定的违法或者说由刑法加以威慑的与他人权利相违背的行为”[8]。从行为论来看,对于行为的考察就是要从事实中选取值得纳入刑法评价范围的内容,亦即,将刑法上有意义的行为作为犯罪论的判断对象。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与网络“恶搞”行为相比,在非网络环境下恶搞行为的刑法认定显然相对简单。正如对于婚闹恶搞行为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罪、侮辱罪的认定,由于物理空间的限制,这种非网络环境下的恶搞行为溢出效应表现更弱、衍生后果相对清晰,是否违背刑律的判断往往仅需要聚焦于该外在行为本身即可。但是,随着恶搞的网络化,恶搞在作为“目的”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成为“手段”。“纯粹的自我娱乐”型网络“恶搞”行为,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方面都被急速稀释。在传播学看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其效果不在思维或概念层面,而更多地体现在意义关系与感知方式维度,“技术所向披靡,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感知的方式”[9]。因此,一方面,恶搞的网络化开始使网络“恶搞”行为更多地成为一种表达方式,其行为本身的戏谑、搞笑功能被消解。大量公众不再“为恶搞而恶搞”,而是开始更多地将网络“恶搞”作为发泄情绪、批判思考、表达立场的手段。在网络空间“恶搞”行为被普遍赋予表达功能的情况下,网络“恶搞”这一行为被附加了更多元、更复杂的外在价值。简言之,网络“恶搞”就更容易被“夹带私货”。当其与民族、性别、政治事件等社会敏感议题相连接时,就十分容易陷入触犯如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罪名的风险。另一方面,尽管表达的目的并非都是传播,但是正如学者尼克·库尔德利所言“媒介文化是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世界的运行主要是通过或依靠媒介的。”[10]这是因为:第一,传播仍是绝大多数主体进行表达的目的;第二,表达与传播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传播是表达的主要归宿。在网络“恶搞”行为中,由于互联网的交互性、即时性,网络“恶搞”的传播速度更快、覆盖更广,其方向、尺度、范围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回到刑法中来看,在刑事制度中,由于“传播”又具有独特的法律含义,无论是网络空间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还是“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被认为是诽谤罪的“情节严重”,以及《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要求在认定网络犯罪行为的情节和后果时,应当重点审查“账号数量、信息被点击次数、浏览次数、被转发次数等能够反映犯罪行为对网络空间秩序产生影响的内容。”刑法不仅深入地介入到了网络传播秩序的治理,“传播”对于刑法语境下的定罪与量刑都具有直接影响和现实意义。因此总的来说,伴随着网络“恶搞”表达、传播功能的普遍赋予,其带来的刑事风险也愈发的多元、弥散和不确定。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内网络“恶搞”可能与言论型犯罪、传播型犯罪等犯罪的连接,在拓宽了刑法规制网络“恶搞”的空间的同时,也将带来刑法在创作自由与内容审查、言论自由与言论管控、传播自由与信息监管等对立价值之间的权衡难题。
(三)个体到大众的流变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人类的“参与式平等”,作为一种“解放式媒介”,互联网还成为了自我传播的工具,成就了更多的自我表达并加强了个人主义的趋势。于恶搞行为而言,互联网无疑为其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从影视明星成龙的“duang”到素人“武术大师”马保国,再到抖音等自媒体社交平台的“流鼻涕”“猪头”滤镜特效可以使用户进行“自我恶搞”。互联网的出现模糊了恶搞行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在网络环境中个体既是网络“恶搞”的消费者,也往往是网络“恶搞”的生产者。匿名性的参与、低门槛的技术、多样化的表达、高速率的传播正在使网络“恶搞”的“生产型消费”成为奥尔森笔下的“集体行动”与巴赫金笔下的“第二生活”。
然而,互联网的赋权与赋能在使网络“恶搞”大众化、草根化的同时,技术权力向“恶搞权力”的普遍性转换使本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大众更容易出现以网络“恶搞”之名行网络暴力、网络伤害之实的失范行为。一方面,与物理空间恶搞行为的范围相对可控不同,网络“恶搞”的大众化使其在单个网络事件中在参与人数、持续时间等方面都难以控制。一场“全民恶搞”可能覆盖全国甚至跨越国界并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这是任何传统的恶搞行为都不可比拟的。另一方面,网络“恶搞”的大众化使恶搞行为更具煽动性与欺凌性,许多被恶搞的对象往往以个体面对庞大社会群体,遭受“道德审判”“精神欺凌”与“多数人的暴政”。就这两个方面而言,长期以来网络上对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恶搞以及在某些比赛过后网民对部分球员的集中攻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恰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言,“群体是匿名的,因此是免责的。对个体产生约束力的责任感在这里完全缺席。”[11]在这种网络“恶搞”大众化的现状下,集体非理性的群氓效应就体现的彰明较著,每个人在可以成为网络“恶搞”发起主体的同时也可能成为网络“恶搞”的对象;网络“恶搞”的方式既可以是“单对单”也可以是“单对多”“多对单”,甚至是“多对多”;网络“恶搞”的指向既可能是文学艺术作品,也可能是影视明星、政治人物、英雄烈士乃至普通民众;网络“恶搞”其性质既可以是无伤大雅、相对温和的调侃、嘲弄,也可能是低俗、色情、暴力。因此,随着网络“恶搞”这种从个体到大众的流变,个体自由作为当下人类信息社会中体系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大众化的网络“恶搞”将进一步放大其与以个体权利、个体自由保护为价值内核的刑法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与矛盾。进言之,面对网络“恶搞”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及其与主流价值观的“暧昧”关系,以及技术赋权导致网络参与门槛降低而使网络“恶搞”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自由”与“权利”,刑法作为最后的、最严厉的制裁手段显然力有未逮,不宜以一种普遍性、前置化的方式进行干预。在网络“恶搞”行为的规制中,作为应对真正严重危害行为的刑法,应当是最后一道防线。在此理念下,如何在刑法制度下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恶搞”行为进行界定与区分,就是兼顾刑法谦抑与有效规制的必要之举。
三、刑法界定:网络“恶搞”的类型化区分
网络时代,恶搞的泛化与异化使网络“恶搞”成为一种“集体性狂欢”,这天然地使参与者产生“法不责众”的博弈心理[12]。加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刑法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对网络“恶搞”行为的协同规制就面临着挑战与抉择。在官方对网络“恶搞”实施“管控”“借鉴”“收编”三种治理模式中,即使部分网络“恶搞”行为属于“管控”的内容,但也并不当然就会落入刑法规制或刑法管控的范畴。因此,在保障公民自由与人权、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基本立场下,应当通过法教义学的类型化、抽象化、体系化思维,厘清刑法所禁止的网络“恶搞”行为以及为何禁止,以此发挥刑法在网络秩序治理中的有效功用。
从本质上来看,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法益既是犯罪行为实质不法的内涵所在,也是行为之所以被定义为犯罪且需要受到处罚的实质理由。具体而言,法益既是刑法规制尺度的价值衡量标准,也是某一行为之所以受到刑罚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涉及网络“恶搞”行为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均趋严厉,而网络化的“恶搞”行为又日渐泛化与异化的情况下,应当“遵循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这一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逻辑”[13],在法益的指引下通过侵害法益的类型化区分明确不同涉罪网络“恶搞”行为的实质,指导刑法对网络“恶搞”行为的准确适用。
(一)侵害国家法益的网络“恶搞”行为
在刑法中,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主要为刑法分则第1章所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在该章的罪名中,涉及网络“恶搞”行为的主要是第103条第2款规定的煽动分裂国家罪,以及第105条第2款规定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这两个罪名可以看出,煽动分裂国家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之所以受到刑法规制,除了法益层面两者都会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造成威胁,两者的共同点还在于其“煽动性”,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文中所阐述的“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正如上文所言,网络“恶搞”行为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其煽动性和传播性,尤其是在大规模的网络“恶搞”行为中,事件本身的事实真相、是非曲直将成为“房间里的大象”而被群体的非理性湮没。对网络“恶搞”行为而言,在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社会事件中的反动恶搞言行就可能落入上述两罪的规制范畴。当前,虽然司法实务中侵害国家法益的网络“恶搞”犯罪并不多见,但如“修例风波”等政治事件中,香港媒体平台及域外媒体平台出现的大量涉嫌煽动分裂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性恶搞,以及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出台并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明确D6F1/a/vbFDP1KwhnInIsnUn93VYbg7yC5ryUjwJ5dE=驻港国安公署可以对特定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进行直接管辖,《香港国安法》可以超越制定者或实施者的管辖范围而对有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管辖[14]。显然,对于侵害国家法益的网络“恶搞”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不仅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更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刑事立法上系以不法构成要件所要保护的法益为准,而将保护相同或相类似法益的不法构成要件,同列在一个罪章之中”[15],侵害国家法益的涉罪网络“恶搞”行为在刑法条文上集中体现在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例如,刑法第249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虽然在刑法的内部结构安排上被放置在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部分,而由于当前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已经与国家安全、国家稳定、国家利益紧密勾连,在实践中该行为也更多是表现为侵害国家法益[16]。因而,俄罗斯等域外国家就将此罪作为破坏国家政权与安全类犯罪[17]。结合该罪的煽动属性,正如“李治东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案”中终审法院所认为的被告人李治东利用网络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诋毁、恶搞,实际上就是宪法所禁止的制造国家分裂、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刑终411号刑事裁定书。。因此,通过网络“恶搞”实施的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行为在侵害国家法益时也会落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二)侵害社会法益的网络“恶搞”行为
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主要指的是破坏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等行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空间成为法律意义上尤其是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场所”的情况下,网络“恶搞”行为无疑与超越个人利益、指向不特定多数人的社会法益有着更深度的关联。加之普通公众一般与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联系较弱,而社会法益较个人法益又相对抽象,因此,网络“恶搞”行为容易触犯侵害社会法益类犯罪的罪名。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侵害社会法益的网络“恶搞”行为可以分为:
第一,破坏政治秩序的网络“恶搞”行为。在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类型下,破坏政治秩序的犯罪行为虽然与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普遍具有密切联系,然而,由于此类犯罪的法益侵害更加具象且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在刑法分则中立法者将其安排在了侵害社会法益类犯罪的章节。对网络“恶搞”行为而言,触犯此类罪名十分常见。其罪名主要有:(1)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利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视频图片实施的恶搞行为,就很有可能触犯该罪名。例如,在“多某某宣扬极端主义案”“郑钱宣扬恐怖主义案”中,两被告人由于想“恶搞一下别人”、出于“恶搞的心态”而在网络空间传播了恐怖视频进而构罪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人民法院(2016)新4023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9刑初26号刑事判决书。。(2)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国旗国徽国歌作为国家符号,其政治性与象征性以及作为符号本身的社会事实属性,都使其容易被作为行为对象而恶搞、攻击[18]。在实践中,此类案件也屡见不鲜。(3)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英雄烈士的名誉与荣誉在故去之后已经上升为了社会公共利益[19],网络空间对英雄烈士的无底线恶搞,将严重冲击社会情感与核心价值观,乃至损害社会层面的政治认同与政治秩序,这类网络“恶搞”行为必然导致刑法介入。正如2021年引起社会公愤的“蜡笔小球案”就是例证。
第二,破坏经济秩序的网络“恶搞”行为。经济秩序作为社会法益的一种,刑法对其保护集中在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对破坏经济秩序的网络“恶搞”行为而言,最可能触犯第221条所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从法条可以看出,该罪的核心行为方式在于“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由于网络“恶搞”的夸张性、非理性、传播性,极易成为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通过商业评价树立形象、建立商誉,而虚假、不正当、诽谤性的网络“恶搞”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企业利益,还会破坏整个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进而触犯刑律。如在“施某损害商业信誉案”中,被告人施某出于提高个人微信公众号关注度与点击率的目的,通过拼凑图片文字恶搞称“市面上的农夫山泉饮用水90%以上都是假水”而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并受到了刑事处罚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刑终12号刑事裁定书。。
第三,破坏社会秩序的网络“恶搞”行为。在刑法中,广义的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等,而狭义的社会秩序又与政治秩序等存在内生性差异,侧重于国民的社会性市民生活,在刑法分则中主要体现在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尤其是该章第1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的相关规定。于网络“恶搞”行为而言:其一,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以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王景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中,被告人就是为了恶搞其朋友伪造并传播了疫情通报图片,扰乱了社会秩序,构成编造虚假信息罪参见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县)人民法院(2020)陕0502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书。。其二,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由于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特征以及网络寻衅滋事罪与编造虚假信息罪等罪名可能存在的竞合关系,实务中大量的言论型、传播型失范行为被以寻衅滋事罪论处[20]。其中,因网络“恶搞”行为构成此罪的亦是不胜枚举,尤其是在恶搞的对象为刑法没有专门罪名涉及的如敏感人物、敏感事件等。其三,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当前的网络“恶搞”行为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图片拼接、视频剪辑,诸如依托深度伪造技术的“一键换脸”“一键脱衣”等恶搞应用程序的出现,使现实中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的“换脸”淫秽视频[21]。技术的进步使网络“恶搞”行为的门槛不断降低,网络“恶搞”的手段不断丰富升级的同时,也使低俗色情的网络“恶搞”行为本就存在的传播淫秽物品风险表现得更加显著。
(三)侵害个人法益的网络“恶搞”行为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刑法仅保护具有重大意义的个人法益,个人法益的保护也是刑法之所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个人法益主要是指生命、健康、自由等为刑法所保护的个人生活利益,在刑法分则中集中体现为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侵犯民主权利犯罪,以及侵犯财产犯罪等。在这些犯罪中,网络“恶搞”行为所涉及的主要是侵犯人格权的犯罪,即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与诽谤罪。早在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就强调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惩治网暴指导意见》也明确了“在信息网络上制造、散布谣言,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的诽谤罪罪状,以及“在信息网络上采取肆意谩骂、恶毒攻击、披露隐私等方式,公然侮辱他人”的侮辱罪罪状,并详细阐释了网络暴力中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自媒体”的网络时代,正如当下引发社会公愤的“网课爆破”,网络空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新型传播格局使任何一名社会公众都有可能被恶搞。同时,由于网络“改变了人们所面对的利益与责任的配比”[22],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借助网络“恶搞”行为的侮辱与诽谤更加“方便”、频繁,网络中的个体在更容易遭受集体的“私刑”的同时,侵权责任人也更容易逃逸。这也恰恰印证了贝卡里亚所言:“舆论的强横就成了从他人那里获取和躲避法律所管不着的利益和损害的唯一工具。”[23]在现实生活中,如“郎某某等诽谤案”的被告人出于寻求刺激、博取关注的恶搞目的,捏造并散布“取快递女子出轨快递小哥”,在网络中引发了大量的针对被害人的淫秽、低俗评论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市)人民法院(2021)浙0110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书。;在“谭某侮辱、诽谤案”中,被告人谭某发布了系列恶搞漫画及恶搞文章,侮辱“江歌案”被害人江歌及其母亲江秋莲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刑终672号刑事裁定书。。从这些涉及网络“恶搞”的侮辱、诽谤犯罪的案例中,不难发现上述行为在普遍严重侵害当事人个体的人格、尊严、名誉的同时,也会对整个网络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介入限度:网络“恶搞”行为的可罚性基准与限制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技术性”扩大了网络犯罪的侵害范围。从刑法角度来看,网络“恶搞”可能涉及侵害国家法益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犯罪与侵害个人法益犯罪。但由于在类型化的视角下上述的实定基准较为抽象并具有较强的形式性,可能引起公诉程序的恣意启动,且我国“单轨制”的案件过滤机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应受到追诉的案件退出刑事诉讼的可能[24]。因此就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中指出的,“法治是互联网治理的基本方式”,要“运用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推动互联网发展治理”。基于刑法“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二元评价模式,未来应当通过对网络“恶搞”刑事可罚性基准的厘定与限制,明晰刑法介入网络“恶搞”行为的限度与边界,以防止“国家对网络空间的过度干预”[25],实现法治观念与法治思维指引下的网络“恶搞”行为刑法治理。
(一)恶搞内容的限制:为刑法所禁止的内容
行为是犯罪成立的基础,没有行为也就无所谓犯罪。构成犯罪的网络“恶搞”亦以行为为要素,即如上文所梳理的这种行为集中地体现为网络“恶搞”的表达与传播。但在既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表达”“传播”这些行为方式,而忽略了网络“恶搞”构罪的组成要素即网络“恶搞”的本质内容。作为网络“恶搞”的实质内涵,恶搞内容是刑法对于网络“恶搞”进行评价的核心参照[26]。因此,网络“恶搞”行为是否涉及犯罪的判定离不开恶搞内容本身的判断,刑法介入网络“恶搞”的边界设定首先就是要在内容上划清具有罪质指向的网络“恶搞”内容与正常言论内容、表达内容、传播内容的界限。在网络“恶搞”的内容中,对于刑法所未禁止而宪法等法律还会给予保护的内容自然不必赘述。在此需要重点讨论的是,宪法等法律未予以保护而刑法也未禁止的内容。这类内容由于处于刑法规制辐射的外部边缘与模糊地带而又与刑法所禁止的内容存在可能的交叉,因此,网络“恶搞”对于此类内容的涉及极易在刑法扩张中被有罪化处理。
具体来看,从网络“恶搞”所涉及的各项罪名可以看出,在我国的刑法制度中,无论是诸如煽动分裂国家、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等发布、表达即构成犯罪的内容,还是虚假信息、虚假恐怖信息等需要一定的传播才成立犯罪的内容,以及刑法第287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毒品、枪支、淫秽、诈骗等信息的禁止,刑法对特定的违法内容进行了规制。但是,除了前述的为刑法所明确规制的违法信息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属于违法而刑法未介入的内容。例如,实践中出现的通过网络“恶搞”的方式发布招嫖信息的案例,对于此类案件,如果招嫖内容背后不存在实际的卖淫活动,则根据案件的危害性等实际情况判断是否构成侮辱罪、诽谤罪、诈骗罪等罪名;如果恶搞的招嫖内容背后确实存在卖淫活动,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由于卖淫活动本身就只是一种违法行为,因此,为筹备、实施卖淫而实施的招嫖行为就不应当纳入网络“恶搞”行为刑法规制的范畴。概言之,对具有一般违法性的内容,由于刑法并未明确地规定对其的禁止与介入,对于其恶搞的发布与传播是否应为刑法所规制就应当根据罪刑法定的立场,结合内容的实质进行谨慎认定。诸如关于赌博、传销等内容的恶搞,皆属于此类。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寻衅滋事罪的兜底作用,当前大量涉及犯罪的网络“恶搞”行为都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尤其是当网络“恶搞”行为涉及的内容不属于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到的任意一项,且又无法被刑法第291条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的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所覆盖时。在司法实务中,这类寻衅滋事罪案件中当事人发布传播的就包括歪曲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形象”“企业单位形象”等内容[27]。暂不考虑在危害结果层面上述个案网络“恶搞”行为是否达到了刑法及《诽谤等刑事案件解释》等规定对网络空间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实质要求,仅就内容角度而言,上述的部分恶搞内容是否属于刑法所禁止和规制的内容也是值得商榷的。
(二)主观意图的限制:实际恶意与不法目的
前文所述,从词义学的角度来看,虽然“恶搞”一词的“恶”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负面性的伦理道德评价,但在网络“恶搞”日趋泛化与异化的当下,网络“恶搞”的“恶”已经不能仅仅从“恶意”“恶劣”等角度进行理解,其还蕴含着夸张性表达的内在含义。根据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入罪评价时,主观与客观的要件需同时兼备;而在出罪评价时,两者的任一否定均可排除行为的犯罪性。从这一角度出发,鉴于网络“恶搞”的中性化、传播化、大众化使网络“恶搞”产生的主观逻辑起点日趋复杂,在主观方面刑法对网络“恶搞”行为的介入也有相当的限缩余地。
实际恶意作为美国法上的一个经典概念,最初是指行为人在行为时明知发布的内容为虚假或可能为虚假而将其发布。随着其适用从民事领域向刑事领域的扩张,其内涵也从发布内容的虚假演化为不法,进而被认为是判断网络谣言、网络寻衅滋事等犯罪主观不法性的有效标准[28]。鉴于网络“恶搞”行为的表达性与传播性,以及刑法语境下恶意的判断不仅具有入罪功能更具有出罪功能——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任何犯罪都是有恶意的,但只有特别恶劣的犯罪动机才能实质影响主观罪过的可谴责性,明显属于国民容忍限度范围内的恶意行为应当被排除于犯罪之外。通过实际恶意的判断也可以确定在涉罪网络“恶搞”中行为人是否具有不法目的,进而依托实际恶意与不法目的的连接使看似符合构成要件、但不具有实际恶意与不法目的的行为出罪。即当网络“恶搞”中行为人的实际恶意由犯罪动机演化为不法目的时,其实际恶意就成为了主观构成要件要素[29]。因此,在网络“恶搞”中,只有行为人能够认识到其网络“恶搞”行为会产生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利益等结果,且无正当原因而希望、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时,才可能在实际恶意与不法目的的基础上构成相关犯罪。举例而言,在“张强(化名)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中,张强因为使用“本·拉登”头像在微信群聊天而引发了群友的调侃:“看,大人物来了”,其顺势回复了一句“跟我加入ISIS”。而后所有群内成员也均未对其进行任何回应,并继续闲聊其他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据此认为张强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判处其有期徒刑9个月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刑初45号刑事判决书。。就本案而言,可以看出在主观方面张强的恶搞言论没有实际恶意,此句话只是一种生活性的玩笑,张强并不具有违反法规范的主观意图与敌视法秩序的实质恶意;并且此恶搞言论也没有不法目的,从张强的职业、背景、过去表现以及此恶搞言论的发布场景等实际情况可以轻易地判断出,张强不仅不具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不法目的,更不具有宣扬背后的怂恿、鼓动他人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退一步来讲,即使认为张强此句言论具有“宣扬性”或“煽动性”,但这也并不当然的、默认的等于张强在主观上具有“宣扬”或“煽动”的意图。总的来说,在网络“恶搞”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判断中,主观方面判断的缺位极有可能导致严格责任倾向下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对网络“恶搞”行为是否涉及犯罪的主观方面判断,要借助经验法则结合行为人所言、所知、所为等因素综合判断行为人的实际恶意与不法目的[30]。而不能仅仅根据行为人网络“恶搞”的内容以及其发布、传播的行为就倒推出其具有实际恶意与不法目的,进而进行客观归罪。
(三)危害结果的限制:法益侵害性的再强调
从本文第二部分的梳理可以看出,根据传统的法益主体三分法分类,网络“恶搞”行为涉及的犯罪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由于网络“恶搞”行为涉及犯罪罪名的广泛性,本文无意就单个罪名的法益侵害问题进行详尽论述,而是希望通过典型个案的剖析,阐解并强调法益侵害性对判断网络“恶搞”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意义这一共通性问题,以此从危害结果的限制角度,明晰刑法介入网络“恶搞”行为的边界。
对于犯罪是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这一基础概念,在理论层面毋庸置疑已经无需赘述。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规范的抵牾、个案的判断以及互联网的动态性、时效性所带来的刑法适用的不稳定等原因,部分关于网络“恶搞”行为的刑事裁判却忽视了刑法“谦抑性的法益保护原则”,对法益的判断不合刑法目的的泛化,进而造成了对危害结果判断的泛化以及刑罚的扩张。如在“罗岱青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罗岱青先后在境外社交平台发布恶搞国家形象的“不雅拼装图片信息”40余条。法院认为罗岱青“起哄闹事、引发围观,破坏社会管理秩序”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刑初1087号刑事判决书。。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法益应当是“公共秩序”,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侵犯的法益是“公共场所秩序”。就本案而言,就算暂不考虑学界对于网络空间是否构成刑法上“公共场所”的质疑[31],但刑法上危害结果的判断应当是质和量的统一,即入罪评价时行为应同时具备罪质和罪量,而正当化行为、轻微行为对罪质或罪量的任一否定就可以出罪。本案中:一是被告人罗岱青所发布的恶搞、 诋毁内容仅40余条,40余条的内容是否会对“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秩序”这一法益造成实质损害?二是本案中的恶搞行为发生在境外网络平台,并非说在境外平台的相关行为就不应受到法律、特别是刑法的规制和规范,而是鉴于现实上我国境内外网络的区隔性,罗岱青在境外平台的40余条发布行为又是否能够达到刑法规定的构成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危害后果?因为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在“高振强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高振强在境外网络共计发布或转发信息17 051条,其中80%都是与罗岱青案类似的不良信息、有害信息,并且受到了不同数量点阅和转发。该案中法院认为高振强构成寻衅滋事罪,但是高振强也是被判处了与罗岱青相同的6个月有期徒刑参见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304刑初323号刑事判决书。。而更典型的案例仍是上文所谈及的仍以“张强(化名)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为例,在本案中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作为抽象危险犯虽然以对法益的提前保护为设立目的,但是其构成也要求这种抽象危险具有转化为实害的可能。亦即,“只有当行为的抽象危险现实化为实害,行为人基本上不可能控制危险的现实化,才能将该危险规定为犯罪”[32]。结合案件的生活性场景、张强的农民工身份等因素可以清晰看出,张强的恶搞言论并不具有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也不具有产生危害结果的现实可能。简言之,其行为只是在表面具有刑事违法性,而没有实质上的法益侵害性,其恶搞言论显然不应当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
“保护法益的抽象化,必然导致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缺乏实质的限制,从而使构成要件丧失应有的机能。”[33]犯罪的实质是法益侵害性,在具体的涉罪网络“恶搞”案件中,要综合审察案件的具体情节判断恶搞行为法益侵害的危险性,而绝非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就一定构成犯罪。刑法上的法益是实质性的、限定性的,而绝非虚无缥缈、无限泛化的普通利益。刑法介入网络“恶搞”行为对法益进行保护时,必须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具体来看:一方面,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价值在网络“恶搞”行为全民化的时代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对国家机关的恶搞与批评在没有直接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时,就不应当认为侵害了国家法益进而构成犯罪[34];涉及“公共秩序”的网络“恶搞”,应当参照刑法第298条对“公共秩序”的规定,将公共秩序限缩为公众现实活动秩序[35];对企业的网络“恶搞”行为,在没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危害结果时,哪怕可能“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也应该交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法律予以规制,而不能草率认定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针对个人的侮辱式恶搞、诽谤式恶搞,也应当优先通过《民法典》对名誉权的保护乃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对于诽谤侮辱的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应对,其只有“情节严重”、在刑法视域下具备法益侵害性时才应入罪。
(四)法律后果的限制:保安处分的谨慎适用
就涉罪网络“恶搞”行为而言,由于其涉及的刑法分则中的罪名较多,不同罪名之间的刑罚差距也较为悬殊。因此,对刑法介入网络“恶搞”行为的法律后果限度的讨论将不考虑刑罚问题,主要围绕保安处分措施的适用来展开。
以保安处分为切入点来探讨刑法规制涉罪网络“恶搞”行为的法律后果限度,一方面源于在我国《刑法》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论的主张下,保安处分于刑罚不具有依附性,对网络“恶搞”行为涉及的各种罪名具有共通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践层面刑法对网络“恶搞”行为的规制中,以“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为代表的保安处分的适用存在的过度化问题。由于仅仅依靠刑罚难以完成预防犯罪的刑法任务[36],因此,刑法在规定了刑罚的同时,基于特殊预防的立场还规定了保安处分措施。鉴于保安处分存在一定的“法外性”特征——其与刑罚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对犯罪人已然的行为做出的处罚措施不同,保安处分不以有责为前提而主要着眼于犯罪人的危险性。为避免其滥用对人权的侵害,其适用:一方面要保证必要性,即必须采取保安处分措施才能防范行为人可能的危险行为时方可适用;另一方面要具有相当性,就是说保安处分的采取应当与行为人先前行为的危害程度、社会保安的现时需要、行为人未来的危险性相称。然而,审视当前的网络“恶搞”犯罪案件,作为保安处分措施的“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却存在着普遍适用的倾向。特别是在大量网络“恶搞”案件中,法院都对被告人的手机进行了没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无疑是网络“恶搞”行为的重要工具,甚至是网络“恶搞”犯罪的工具。但与此同时,其更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生活工具。从刑法第64条来看,需要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是与“违禁品”具有相当性的财物,即对具有生活用途的物品而言,应当是被专门、长期或多次用于犯罪时才可没收[37]。具体到网络“恶搞”犯罪行为来看,在考虑对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设备进行没收时,除了查证该设备是否被用于网络“恶搞”犯罪,更需要考量的是对于该设备的没收是否能达到消灭行为人再次犯罪条件的保安处分预防效果与显著意义。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网络“恶搞”犯罪行为中,当行为人长期或专门地将手机等设备用于网络“恶搞”犯罪时,此设备毋庸置疑应当没收。但是,如果行为人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偶尔使用该设备进行网络“恶搞”并构成了犯罪,缺乏专门利用该设备进行网络“恶搞”犯罪的意思的情况下,则不应对其设备进行没收。
五、结语
随着网络时代恶搞行为的泛化和异化,网络“恶搞”行为已然成为了网络公民个体失范与网络空间治理失序的重要原因。由于部分网络“恶搞”行为具有对个人、社会或者国家法益的侵害危险,决定了刑法参与网络“恶搞”治理的必要性。但是,刑法的最后性表明,刑法并非网络“恶搞”行为治理的最优手段,动用刑法进行网络“恶搞”行为治理需要使整个社会承担较高的治理成本,并掩盖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刑法对网络“恶搞”行为的介入应当坚持罪刑法定与刑法谦抑,避免在事本主义下使刑法沦为“在先的管理法”[38] 。进言之,刑法对于网络“恶搞”行为规制的主要思路应当是:通过类型化区分,以恶搞内容、主观意图、危害结果、法律后果等基准要素限缩犯罪圈,清晰厘定刑法规制与前置法规制的边界,实现民事侵权、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的阶梯递进措置,进言之,网络“恶搞”的内容应当是刑法所禁止的内容;行为人主观上应具备实质恶意与不法目的;危害结果层面该行为必须具有实质的法益侵害性,避免保护法益的抽象化处理;在法律后果方面手机等网络终端设备具有很大的生活用途,应当谨慎适用“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保安处分措施。以此确保网络“恶搞”行为规制中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功能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刘艳红.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安全刑法抑或自由刑法[J].政法论坛,2023(2):60-72.
[2]李丽.扰动文化的逆流:对反文化现象的哲学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
[3]蔺玉红.刹住“恶搞”之风 发展先进文化[N].光明日报,2006-08-11(003).
[4]曾一果.符号的戏讥:网络恶搞的社会表达和文化治理[J].南京社会科学,2018(12):106-115.
[5]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帝吧出征FB,友邦有话要说[EB/OL].(2016-01-22)[2024-04-17].https://mp.weixin.qq.com/s/gzC800gyesaUb63D9YwsGQ.
[6]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33.
[7]J.弥尔顿·英格,黄瑞玲.反文化与亚文化[J].国外理论动态,2013(10):36-43.
[8]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34.
[9]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M].刘芳,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9:68.
[10]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67.
[1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陈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20.
[12]王立峰,潘博.“法不责众”的博弈心理与法治对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3):55-64+173-174.
[13]刘双阳.数据法益的类型化及其刑法保护体系建构[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6):37-52.
[14]顾敏康,王振华.香港国安法的域外效力研究——从香港国安法第38条展开[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34-142.
[15]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12.
[16]王秀梅.依法打击“东突”势力 切实维护国家稳定——兼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完善[J].法学评论,2011(6):109-116.
[17]吴占英.中俄刑法典对煽动族群仇恨、歧视性质的行为规制之比较[J].湖北社会科学,2012(10):168-170.
[18]高巍.国家符号的刑法保护[J].中国法学,2022(1):182-202.
[19]刘艳红.法秩序统一原理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对象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5):110-123.
[20]贾健.网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件的罪名适用研究——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区分为视角[J].理论月刊,2021(1):146-153.
[21]王禄生.论“深度伪造”智能技术的一体化规制[J].东方法学,2019(6):58-68.
[22]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M].李旭,沈伟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97.
[23]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78.
[24]王禄生.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分析——基于案件过滤的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14(10):148-154.
[25]刘艳红.互联网治理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基于场所、产品、媒介的网络空间三维度的展开[J].理论视野,2016(9):41-44.
[26]刘艳红.理念、逻辑与路径:网络暴力法治化治理研究[J].江淮论坛,2022(6):21-30+2.
[27]张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J].法律适用,2022(7):79-88.
[28]姜涛.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从宪法的视角[J].中国法学,2021(3):208-228.
[29]张勇.恶意犯罪的类型阐释[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6):3-19.
[30]刘宪权.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刑法规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J].法学家,2016(6):105-119+178-179.
[31]冀洋.“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的刑法分析[J].中国法律评论,2023(3):99-111.
[32]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2017(7):88-108+205-206.
[3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397.
[34]刘艳红.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134-152+204-205.
[35]欧阳本祺.疫情期间刑法对谣言的合理界定[J].人民检察,2020(07):5-9.
[36]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04.
[37]张明楷.论刑法中的没收[J].法学家,2012(3):55-70+177.
[38]刘艳红.刑法的根基与信仰[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2):150-170.
(责任编辑:蒲应秋)杨 洋 杨 波,张 娅 郭 芸,王勤美,蒲应秋
The Criminal Law Boundary of Online “Spoofing” Behavior
SUN Yu
(Law School,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China,211189)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new media,online “spoofing” behavior is showing a trend of gener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Evolving from counterculture to subculture,online “spoofing” has been endowed with functions of expression and dissemination,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individual to mass dissemination.The neutralization,dissemination,and popularization of it pose real challenges to the intervention and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interest typology,crimes related to online “spoofing”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ose that infringe upon national legal interests,social legal interests,and individual legal interests.When criminal law intervenes in online “spoofing” behavior,the content of the behavior should be prohibited by criminal law;at the subjective level,the perpetrator should have actual malice and unlawful intent;at the objective level,online “spoofing” behavior must result in harm to legal interests;in terms of legal consequences,security measures such as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perpetrator’s property used for the crime” should be cautiously applied.
Key words:
online “spoofing”;criminal law boundary;legal interests;typology;expression disse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