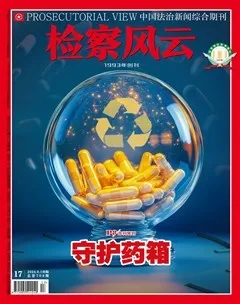传统中国法律激励的历史镜鉴
法的作用是法理学中的一项基础命题。一般认为,规范作用是法的主要作用之一,它具体又可以分为指引、评价、教育等多种作用类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法律惩戒是人们感知最深的规范作用,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激励,则容易受到忽视。其实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法律激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丰沛的智慧源泉和历史镜鉴。
社会治理与法律激励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意识到了法律激励对富国强兵的重要意义,商鞅变法是这一时期最成功的范例。奖励耕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它运用法律激励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和秦军的战斗力。在社会治理层面,法律激励的作用同样巨大。比如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侠义精神备受推崇,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大亮点。实际上这一法律文化的形成,与长期以来的法律激励密切相关。
以《唐律疏议》为例,其用较多的篇幅来对见义勇为等行为进行释义,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在《唐律疏议》中,专设“捕亡律”篇来规范抓捕罪犯等事宜。见义勇为的行为一般发生在暴力犯罪案件中,抓捕是这类案件的核心环节,故而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主要分布在此篇中。在“捕亡律”的开篇,唐朝立法者首先明确国家执法机关的法律责任,要求其在执行抓捕任务时,做到尽职尽责。该篇“将吏捕罪人逗留不行”条规定:“诸罪人逃亡,将吏已受使追捕,而不行及逗留,谓故方便之者。虽行,与亡者相遇,人仗足敌,不斗而退者,各减罪人罪一等;斗而退者,减二等。即人仗不敌,不斗而退者,减三等;斗而退者,不坐。”简而言之,执法人员不积极抓捕,会依情节轻重受到各种处罚。
权责相应是《唐律疏议》高超立法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立法者对执法人员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为他们尽责执法免去后顾之忧。在上一条款之后,便是“罪人持杖拒捕”条,该条规定“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及走逐而杀,若迫窘而自杀者,皆勿论”。当然,立法者也考虑到了过度执法的问题,对此也有详细规定。在明确了执法人员的责任后,紧接着就是有关见义勇为的规定。“道路行人不助捕罪人”条规定:“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在该条的“疏议”中,立法者特别对“势不得助”“之类”等法律术语进行了立法解释。“‘势不得助’谓隔川谷、垣篱、堑栅之类,不可踰越过者及驰驿之类。称‘之类’者,官有急事,及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亦各无罪。”由此可见,法律对道路行人见义勇为的要求并不严苛,体现出法律的人性之美。
以上是国家执法人员在场情况下的见义勇为。考虑到此类案件一般情况紧急,案发时通常没有执法人员在场,这是见义勇为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场域,立法者对此作了详细规制。“被殴击奸盗捕法”条规定:“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虽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也就是说,有殴打人致折伤、强盗、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时,即便是没有亲属血缘关系的旁人,也应立即捕捉,将嫌犯送交官府。抓捕过程中的权责问题,参照上条国家执法人员的规定进行。
与此同时,法律还对邻里之间的见义勇为作了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此外,诸如发生火灾等危险情形,唐律也要求公众要及时报告和救援,善尽帮扶义务。《唐律疏议》“见火起不告救”条规定:“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谓从本失罪减。其守卫宫殿、仓库及掌囚者,皆不得离所守救火,违者杖一百。”
律和令是唐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律侧重负面惩罚,令注重正面劝导。唐代立法者善用法律激励,在《唐令》中规定了要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经济方面的嘉奖。《唐令·捕亡令》规定:“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信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这一规定逻辑清晰,思路缜密,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将法律激励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到了明清时期,对见义勇为等行为的法律激励得到进一步巩固。《大明令》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大清律例》规定:“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对于因见义勇为而受伤者,法律也给予妥善照顾,规定“受伤者移送兵部,验明等第,照另户及家仆军伤例,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正是在上述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激励下,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见义勇为故事,使见义勇为逐渐成为一种精神与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
科技发展与法律激励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中华科技文化独树一帜,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宋朝为例,陈寅恪先生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为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一部《梦溪笔谈》,堪称中国古代科技的百科全书。宋朝在物理、化学、天文、工程、数学、农学等科技领域成就非凡。在这些辉煌的科技成就背后,离不开法律激励的强大推动。
为了鼓励科技发展,宋朝统治者出台了大量奖励科技的法律政策,奖励方式丰富多元,奖励对象包罗万千。对贡献巨大者,奖励不但及于自身,还能惠及子孙后代。在奖励方式方面,既有精神奖励,包括降诏褒奖、树碑立传、赐姓、赐名、赐诗、赐文,也有各种丰富的物质奖励。比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京西提点刑狱官、知河阳高绅组织治理黄河水患,“以弃石累之,计省工巨万,而又坚固”,得到了朝廷的降旨褒奖。同样是在宋真宗时期,东京汴梁通往江南的运河要经过5个堤堰,结果“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疲于牵挽,官司舰舟由此速坏”。天禧三年(1019)朝廷派人开通扬州古河,自此“漕船无阻,公私大称其便”,朝廷下旨对工程人员进行褒奖。江淮发运使贾宗觉得这种奖励力度不够,上书宋真宗请求皇帝钦赐御制文褒奖,得到了皇帝的准许。
宋朝在天文历法方面颇有建树,最高统治者对此也极为重视。河南洛阳人王处讷(915—982)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周世宗时期,旧历出现差错,皇帝命王处讷制定新历。王处讷尚未完成,枢密使王朴率先完成了《钦天历》献给朝廷,受到众人好评。唯有王处讷看出了这部历法存在的问题,他私下告诉王朴道,“此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并且指出了其中的问题,王朴听罢深以为然。宋朝建立后,朝廷发现了《钦天历》存在谬误,下诏王处讷别造新历。三年之后,王处讷完成了六卷新历,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为之作序,命名为《应天历》,此举可见这位马上皇帝对天文历法事业的重视。由于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杰出贡献,王处讷的官职不断升迁,最终官拜司天监,成为全国天文历法方面的最高主管。
在军事方面,宋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军事科技的发展,投入巨大的资源鼓励军事技术革新,用来弥补自身骑兵不足的缺憾。在这一背景下,火器、弓箭等克制骑兵的远程武器得到了长足发展。宋太祖开宝年间,兵部令史冯继升等发明了火箭法,试验取得了成功,赵匡胤下诏赐予衣物、束帛。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制造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装备,也得到了重金奖赏。诸如此类的奖励还有许多,不胜枚举。
总体而言,法的激励功能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和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驱动力。但是从客观角度评价,古人运用法律激励,可谓有得有失。在社会治理方面比较成功,其立法智慧可以为今天相关领域的立法提供重要参考。然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尽管古人也运用了法律的激励功能,但这些法律大多采用诏令的形式,而非进入法典之中,缺乏体系化和稳定性,未能使法律对科技发展的激励发挥至最大效用,值得后人深思。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